博文
论客家话书面表达2:客家话书面用字问题及误区
|
论客家话书面表达2:客家话书面用字问题及误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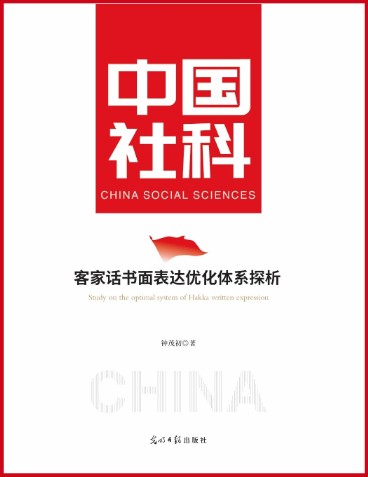
转摘自《客家话书面表达优化体系探析》,钟茂初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24年版
客家话书面表达的用字问题,是关乎客家话书面表达体系及其简洁化实用化的核心问题。只有解决了书面表达用字简洁化实用化的既有障碍,才能为客家话书面表达体系的完善与优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客家话书面表达“用字”,不能简单等同于“考本字”。强求“历史真实”的“考本字”,难以整体性地实现客家话书面表达。应以“逻辑真实”解决客家话用字问题,为客家话书面文字表达体系的构建与优化奠定基础。
客家话书面表达的核心问题是“用字”问题。因为,客家话口语是非常完备的语言系统,但要对其语音作出语义准确的文字表达,存在相当大的难度。长期以来,客家话学界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求解客家话“本字”。本书作者认为,客家话书面表达“用字”问题,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客家话“考本字”问题。因为,客家话书面表达“用字”问题,根本目的是形成客家话书面表达的文字系统,以便于客家话以书面文字方式传承与传播;而客家话“考本字”,则是针对客家话口语词语的读音追本溯源地探讨其“原本用字”。换言之,“用字”问题追求的是“逻辑真实”,只要其语义、读音符合汉语言特点和客家话语言特色,无论其是否是“历史真实”,都可以作为客家话书面表达的用字;而“考本字”,更多地追求“历史真实”。但由于客家话并没有多少历史文献资料可供考证,最终还是依靠逻辑推理去得出。所以,本书作者认为,过于强调“历史真实”,过于强求“考本字”,是难以解决客家话书面表达问题的。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采用“逻辑真实”的方式来实现客家话的书面表达,形成客家话的书面表达体系。
在语言学领域,“逻辑真实”“历史真实”问题,不知是否有学者直接提出过。但这一问题却是广泛存在的。例如,采用现代汉语的标点符号对古文进行标点断句,采用简化汉字来书写印刷古文,显然不是“历史真实”,而只是“逻辑真实”!再如,采用汉语拼音方案对汉字进行标音,显然也不是“历史真实”,而只是“逻辑真实”!所以,客家话书面表达特别是用字方面,采用“力求逻辑真实、不强求历史真实”原则,并不是什么离经叛道的做法。
本书作者强烈主张客家话用字“力求逻辑真实、不强求历史真实”。对于这一主张,许多客家话研究者可能不赞成,尤其是“不强求历史真实”!本书作者为什么坚持这一主张呢?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一主张的合理性。现代汉语中的“祖父(爷爷)”一词,不少客家话地区的发音都是“Gōng Da”,写作“公爹”大体不错。但在现代汉语和北方方言普及的语言环境下,很难将“祖父”与“公爹”联系起来,即使是客家话为母语的现代读者也很难做到。可见,将“祖父”写作“公爹”或许是“历史真实”,如果我们的客家话书面表达强求这样的“历史真实”,不仅无助于客家话的传承与传播,反而徒增混乱!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也能很好地阐释这一主张的合理性。现代汉语中的“没有”一词,客家话中读作“Máo”,基本上都写作“冇”。事实上,“冇”是一个后造字,用在客家话书面表达中显然不是“历史真实”,但由于该字已经传承了一段时期,且为大多数客家话使用者接受,而且也被收入了现代汉语之中,所以,客家话书面文字表达中少量接受“冇”之类的后造字,也是“力求逻辑真实、不强求历史真实”主张的体现。
要认识到,类似的客家话词语并非仅此几例,而是存在一批。所以,“力求逻辑真实、不强求历史真实”应当成为客家话书写中的一个基本准则。
二、既有客家话书面表达“用字”及“本字”研究中存在的若干误区。
客家话书面文字表达的既有研究(主要是“考本字”,如各种客家话字典辞典中收录的“本字”),出现了以下几种倾向,从而使客家话书面文字表达走向缺乏逻辑的误区(既缺乏语言文字发展的历史逻辑,也缺乏一种语言自身内在的逻辑关联性)。这些误区,是客家话书面表达体系的完善与优化必须有效处置的关键性问题。
误区之一:不顾“本字”常用性的逻辑特点。
既有客家话文献中的大量“本字”,是现代汉语中并不常用的“字”,即使在唐宋时期历史文献中也并不是常见的“字”,即使客家字典辞典中引用的例句也往往是孤例。本书作者对这一研究倾向不敢苟同。因为,这样的“本字”不符合语言文字发展的逻辑。其一,客家话作为一种客家群体日常生活交流中的实用化语言,不可能流传许多繁难、生僻而不常用的字词。尤其是一些在唐宋时期就不常见的字词,为什么会在客家群体中流行起来并不断地流传下去呢?显然不合乎常理。其二,客家话与北方方言(包括现今的普通话)是同源流的语言文字,为什么许多繁难、生僻的字词,只在客家话中留存,而北方方言中则荡涤无存?从语言文字的发展逻辑上来分析,也说不通。从发展逻辑上来看,同源流的语言,在有一定区隔的相对孤立的环境下,某些字词的读音和语义可能出现不同的变化,但字词的常用性不大可能出现很大的差异。可类比的例子,同源流的汉语,在大陆与台湾两个地区相互隔离70多年的状况下,一些字词的读音和词义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留存的常用字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差异,最多只是常用程度的差异。更具说服力的例子是,日语汉字是隋唐时期流入日本而在日语中广泛使用的,但比较现代汉语与现代日语,经过一千多年的语言流变和各自发展,除少量日语自造字以外,两种语言中的常用汉字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别。由此可知,客家话与现代汉语的常用汉字不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别,只是用字的常用程度可能存在一些变化而已!既有文献资料中大量的繁难生僻字,必定是人为臆想导致的,既不是历史真实,更不是逻辑真实。
误区之二:不顾汉语言及汉字源流发展逻辑。
例如,客家话中的人称代词,既有客家话文献中,第一人称写作“𠊎”,第三人称写作“佢”或“渠”。选用这些“本字”,表面上看,符合汉字表义表音的形声字特征,但恰恰忘记了汉字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代词都是“假借字”,而不是“象形字”或“形声字”。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𠊎”、 “佢”等字是后造汉字,而不可能是客家话人称代词的“本字”。同理,几乎所有的虚词,既有客家话文献中都仅仅根据相近的读音而选择近音字。合乎语言逻辑的思路应当是,既然都是假借字,在现代汉语已经确定了其规范的假借字并流传有年,何不在客家话书面文字表达体系中,主要虚词采用同样的假借字,赋予其客家话读音即可。
误区之三:考本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整体性综合考量。
在客家话本字考据中,往往都是单独地对某个字词进行考虑,而缺乏对关联字词一并考量的过程。如,客家话中,作为否定的常用词“Ngu”,一般客家话文献中都写作“唔”。其实,只要关联性地考虑,客家话中读“Ngu”音的字,如“五”、“吴”等,就很容易确定客家话否定词“Ngu”的本字应为“无”或“毋”。写作“唔”,毫无道理,毫无必要,语义上没有任何关联性,语音上也没有更接近于“Ngu”的读音。再如,有学者论证表“儿子”的“Lài Zi”的本字为“裔子”,独立来看或许有一定道理,但结合表“男性”的“Lài Zi Ngín”来看,则完全站不住脚。本书作者认为,客家话表“儿子”的“Lài Zi”、表“女儿”的“Mòi Zi”或源于“令郎”、“令嫒”之用语,本字当为“郎”、“嫒”(分别为“男”、“女”的雅称),音变转为“Lài”、“Mòi”。
误区之四:缺乏对词义情境的逻辑考量。
有方言学者认为,“确定本字的关键是方言词和本字在语音上对应,在词义上相同或相近”。这一主张,在客家话“考本字”的研究中也被广泛引用。本书作者认为,这一原则对于其他方言是否适合,不敢妄自评判。但对于客家话而言,完全是本末倒置的思维方法。客家话字词,通常受周边方言以及各时期官方语言的影响,所以,语音往往会不断变化,有些字词的读音在同一方言小区域内都可能存在多种读法。相反,核心词义反倒是较为稳定的。只要是长期流传下来的字词,其词义基本不变。因为,一旦受到了其他语言的影响,就会出现新的词语,而不是通过原有字词的词义变化来适应。因此,本书作者主张:确定客家话本字的关键是词义精准(精准地体现核心词义和词义情境),语音和声调上存在流变合理性即可。
例如,表“对老人小孩关心照顾”的词语,其读音为“Zhāo Fū”。如果把语音对应作为首要原则,必然会选择写作“招呼”,词义上存在较大的偏差。反之,如果将词义相符作为首要原则,则可以选择写作“照拂”或“照护”,虽然音调上有所差异,但两个选择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再如,表“宰杀”的客家话词语读音为“Chí”,客家话文献一般都写作“治”。本书作者认为,该词的核心要义在于表“宰杀动物并处理其皮毛”,“治”无法表达这一内涵。语义读音相符的“褫”,是更为合乎逻辑的选择。
误区之五:刻意复古的思维倾向。
某些“本字”考据,为了“有理有据”,刻意从古代字典类书籍中去寻找字义、字音相近的古代汉字。殊不知,客家话是特定历史时期(上限是五胡乱华衣冠南渡时期,下限是靖康之难时期的南渡)中原地区的日常用语。之前时代的用语(特别是书面用语),与客家话用语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古代字典类书籍中近音近义用字,不足为凭。最具证据价值的只有“隋唐及其前后历史时期”的记载性文献。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古字作为客家话本字是正确的。但是,这些用语并不是客家话的固有用语,而是客家话受周围南方方言影响而纳入的用语。这些南方方言是更早时期从中原地区流传下来的,这些南方方言中的本字,可能与古代字典类书籍中近音近义用字存在渊源关系。但与客家话并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客家话字词的“本字”,应当有其发展脉络,应当与中古时期的汉语字词有源流关系,而不应是凭空出现的一个生僻字。各种客家字典辞典中所举例句、所举早期汉语字典辞典的收录、所举前人的考据,如果缺乏清晰的源流逻辑,那么就不足为凭。为什么古代文献中会出现客家话“本字”的个别例句,其实当时的使用者也未必清楚某个字词的“本字”,而以“趋雅避俗”的方式选择了某个“本字”。
相当一部分的复古字,乍一看颇有道理,使得相关文献作者不作深究而人云亦云。实际上,经不起逻辑推敲。例如,客家话表“铁制利器因久用未磨变钝”之义,亦表“铁锈锈迹”的词语为“Lū”。多数客家话文献写作“黸”。但深究一下,此字仅有黑色之义,与客家话语境完全不符。
客家话“考本字”过程中,可适当追求“古意”。但是,“古意”绝非体现在繁难字、化石字方面,而是体现在:用字为常用字,现代读者能够理解其意,却不常用。例如,表“谜语”的客家话用字为“令”,用字为简单的常用字,其词义现代读者能够体会到,但现代汉语口语中一般不用“令”来表“谜语”。
客家话研究中“考本字”的目的,一是便于研习者更精准地理解方言字词的含义和读音;二是便于研习者理解客家话字词的源流变化;三是从客家话留存的古汉语因素中认识现代汉语字词的源流变化;四是便于记录或创作真正意义上的可读的客家话文本,使客家话得以以可读文本流传下去。
大量使用生僻字,基本上属于自娱自乐,完全失去了传播价值。例如,客家话表“用刀划割”为“Lá”,明明有现代汉语常用汉字“剌”,某些客家话文献却非要煞有介事地“考证”并使用“𠠝”,对于客家话的有效传播而言有什么意义?
误区之六:大量使用“后造字”,陷入臆造误区。
既有客家话文献中,某些“本字”的选定,类似于古物仿造中的臆造品(貌似有一定的古意,却不符合时代特征,生硬地把某些古意特征附着在器物之上)。例如,客家话中,作为对女性长辈亲属称谓有“ōi”与“Mēi”两个读音,一般客家字典辞典把该字写为“娭”与“㜷”。其实,古代汉语中“母”本来就有“ōi”与“Mēi”两个读音,否则以“母”为表音构件的形声字“海”、“每”、“梅”等的读音从何而来?更何况作为客家话中高频常用字,怎么可能没有其本字而需要后造字来表达呢?以“娭”与“㜷”这样的后造字或复古字来表达,毫无逻辑、毫无价值,反倒人为地割裂了语言文字的历史逻辑。
本书作者主张,客家话中除了极少数已经被现代汉语接受的“后造字”之外,其他后造字、臆造字都不宜保留。
误区之七:过于强调读音、音调流变的所谓“规则”,忽视客家话字音存在“讹变”现象。
对于字词读音的变化,不必“食古不化”地引用有关音韵的古籍,也不必“刻舟求剑”式探究其流变过程。客家话由于长时间不作书写用语使用,母语者都是口口相传。说者和学习者都不知道“本字”,只知道大致的读音。在流传过程中,很容易把一个词语的读音“讹变”为某个常见事物的读音。如同英语初学者用汉字读音来标注英语读音,初学者标注读音往往会选择语音相近的日常事物来标注,如将“thank you”标注为“三块肉”、将“good morning”标注为“鼓捣猫呢”,这样才便于记忆、也便于交流流传。但这样标注的读音,肯定是不准确的,也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同样的道理,客家话之中,必定有为数不少词语的读音发生了类似的“讹变”。如果非要从已经“讹变”的读音中去探寻其本字,无异于缘木求鱼。例如,客家话中“矮凳”的读音为“aa Má Dèn”,实际上“矮”字的读音讹变为了更为常用的“鸭”字读音,而“鸭”又进一步“讹变”为客家话日常事物“鸭嫲”,久而久之,“矮凳”讹变成了“鸭嫲凳”。我们探寻客家话的本字,应当还原“矮凳”,如果还原为“鸭嫲凳”就失去了探寻本字的意义。再如,客家话表“太阳或阳光”的词语读音为“Ngiè Téu”,写作“热头”,表“月光”的词语读音也为“Ngiè Téu”,写作“月头”。但从语言的整体性来考虑,“日光”与“月光”为同一读音,是不符合语言准确表达逻辑的。合理推测,“Ngiè Téu”(热头)是由“Ngii Téu”(日头)讹变而来。又如,客家话表“外孙”词语的读音为“Ngòi Seāng”,写作“外生”。从语言整体性来考虑,“外生”与“外甥”同音,不符合语言准确表达的逻辑性。可以合理推测,客家话中的正确用词应为“外孙”(Ngòi Sēn),但在流传过程中,讹变为“外生”。所以,对于此类词语,应在客家话书面文字表达体系中适当加以纠正。
同理,对于音调的变化,也不必“讲死理”地引用相关古籍、探求其流变。音调的无规则变化,很多情形是由于客家话口语词汇在口口相传过程中“讹变”为日常熟悉事物而造成的。这一现象,相对于汉语书面文字传承中的“雅化”现象,可称之为客家话口语传承中的“俗化”现象。例如,“酒酿”(Ziǔ Ngiàng)讹变为“酒娘”(Ziǔ Ngiāng);再如,“长揖”(Chāng Ya)讹变为“唱谒”(Chàng Ya)。如此之类的音调变化,有什么规律可言?何必对其如逢大敌、不敢越雷池一步呢!
我们应当追求的是语义正确,而不是形式上的“精准”。客家话词语读音,不可避免地存在流传传播过程中的讹变。应当认真地判别,并通过适当方式予以纠正,尽可能避免走向无法还原的地步。
误区之八:有闻必录,不顾词语的适用范围,不作逻辑分类地选择字词。客家风俗文化器物用语,与客家话用语,混杂在一起,人为增加了客家话语言的繁复程度。
客家话词语应区分:正式场合的常用词语、非正式场合的俗语、俚语、口语;长期传承变化不大的词汇、新近所造词汇;客家话各方言区的通用词汇、小方言区词汇;与语言有关的词汇、与语言关系不大的日用品词汇。
客家风俗文化用语,本质上并不是客家话作为一门语言的特有用词,不应纳入语言范畴。例如,客家话词典中,多数会列入“金罂”一词。其实,这个词语,并不是客家话语言范畴的特殊词语,而只是客家族群迁葬风俗中的一个用语。再如,客家话词典中,多数会列入“饭甑”一词。其实,这个词语,并不是客家话语言范畴的特殊词语,而只是客家族群常用煮饭方式的一个器具用语。相关词语,在有关客家风俗文化的文献中记载即可,加入到客家话语言文献中,没有必要,徒增烦杂。应当明确:客家话书面文字表达语言体系,是用客家话记载描述世间一切现象的语言,并不是单纯用于记载客家族群风俗文化的语言。客家话书面文字表达体系中收录的词语应主要包括:正式场合的常用词语、长期传承变化不大的词汇、客家话各方言区的通用词汇、与客家话语言直接有关的词汇。而与现代汉语表达相同的词语、与现代汉语表达略有不同但易于理解的词语、客家话中非常用和非典型的词语、客家话小方言区的非通用词语、仅表征客家族群风俗文化、生活环境、日常器具的词语,则不予列入。
引文格式:钟茂初.客家话书面表达优化体系探析[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24.
https://item.jd.com/14362433.html
https://product.dangdang.com/29830577.html
https://wap.sciencenet.cn/blog-1251036-1471765.html
上一篇:论客家话书面表达1:客家话传承传播存在的问题
下一篇:论客家话书面表达3:客家话书面用字的基本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