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论客家话书面表达1:客家话传承传播存在的问题
|
论客家话书面表达1:客家话传承传播存在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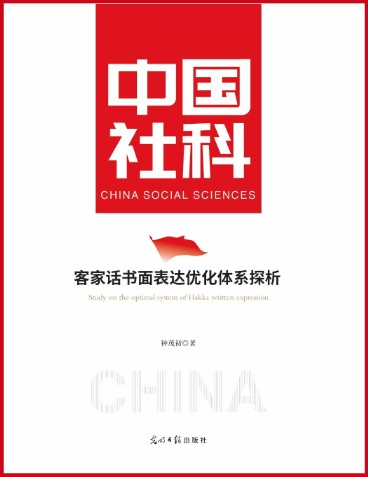
转摘自《客家话书面表达优化体系探析》,钟茂初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24年版
客家语(英译为Hakka),是汉语七大方言之一,是汉族客家民系的共同语言,是联结全国各地乃至全球华人客家民系认同的主要载体。全国大陆地区客家话总人口超过5000万,约占汉族人口的4%。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华人中也有大量的客家话人口。客家话中较多地保留了中古时期的词语,保留了中古汉语音韵,也保留了中原地区的许多常用词语及其发音特征。客家话较好地传承了汉语言文化。当前阶段,客家话被认为是衰落较快的语言之一,亟待有效保护。
一、“客家话是中古时期汉语活化石”,这一定位未必准确!应放下包袱,着力推动客家话的书面文字表达,着力推动客家话书面表达体系的完善与优化!
“客家话是中古时期汉语活化石”,这一判断似乎成为了客家话群体和学界的定论,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客家话书面表达中的思想包袱和思维定势。似乎只有尽可能多地在客家话词语中附会上古汉字,客家话就更准确、更完美。
客家话,流传至今,依然是近亿人口的常用语言甚至是日常交流语言,决不是“化石语言”!所以,客家话用字不可能、也不应留存过多的“化石汉字”。即,客家话字词,绝大多数是中古时期汉语中的常用字词,不应有太多的生僻字、繁难字。客家话与北方方言、现代汉语有共同的源流,北方方言、现代汉语中没有留存的繁难字词,多数也不会在客家方言中留存。
“客家话是中古时期汉语活化石”,单纯从客家话词语与中古时期词语的对比来看,有一定合理性。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作为同源流的现代汉语(普通话)、北方方言,难道就不是“中古汉语活化石”?逻辑上根本说不通!最合理的判断是:现代汉语(普通话)、客家话、北方方言等,其中都存留了大量的中古汉语字词。只不过各自存留的字词,有着不同的“选择”。但存留比例,大致相当。在这一基本判断下,可以得出两个关联判断:其一,留存的字词必须是中古时期(可以隋唐及其前后作为基准时期)的常用字词,绝不会是当时的非常用字词,绝非更早期的繁难生僻字词;其二,留存的字词中,客家话与现代汉语(普通话)、北方方言,是对偶性地留存的,即,对于相近语义的表达,各自“选择”了一个近义的字词。
要认识到,当前客家话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更好地传承和传播,而不是背负“中古时期汉语活化石”包袱,去扮演语言“活化石”的角色。客家话群体和学界应意识到,在现代汉语语言环境下,根本不可能以“客家话”一己之力去“还原”中古时期汉语言的本色。当下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以书面文字表达方式记录客家话面貌,尽可能减缓这一方言退化甚至消亡的步伐。因为,只有书面文字表达才能更加稳固地记录和传承。然而,“1883年,开始客家方言以汉字记载的历史, 早期的客家方言书写显得不成熟,中期有明显改善,但前后期几乎没有衔接。……客家方言书写无法统一标准,经过130多年的发展,客家方言书写还处于一个混乱的局面。”
着力完善客家话书面表达体系,并形成简洁化实用化的体系,是当前客家话传承与传播的急迫任务。
二、站在现代汉语言的角度,客家话不是一门独立的语言,而是一门汉语方言。客家话的传承传播,不仅不应强化与现代汉语的差异,更应着力降低其差异度,以降低客家话书面文字表达的难度!用字与读音的简洁化实用化是客家话书面表达体系的核心要求!
本书作者认为,为了更好地传承和传播客家话,必须促使客家话与现代汉语的差异度“降维”、学习客家话的门槛“降维”!
站在现代汉语语言的角度,客家话学界和使用群体也应客观地承认,客家话不能算作是一门独立的语言,而是一门传承有序的汉语方言。因此,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作为用字、读音的校核基准,是理所当然的。
既有的客家话研究,有意无意地强调客家话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差异性(特别是在用字、读音方面的差异性),人为地割裂客家话与现代汉语的联系,使得现代汉语语言环境下的人群学习研究客家话存在较大的障碍和高门槛。
站在语言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客家话与现代汉语必然存在密切的关联性。比较现代汉语(普通话)、北方方言、客家话、其他方言,打个不很恰当的比喻。北方方言是普通话的“亲兄弟”或“堂兄弟”,各方面都很类似,只是局部有所不同;客家话则是普通话“出五服未远的家族兄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各方面都存在有据可考的渊源;而吴方言、闽方言、粤方言等,与普通话大体是“同宗关系”,源头相同,但其后走向了差异化发展道路。
用字方面。就常用字而言,客家话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差异程度,并不很大。排除那些与客家群体生活区域地理环境、客家群体特定文化习俗、客家话特定表达的语言情态等特殊用字,仅考虑一般通用语言表达程度,如果以1500个汉字作为各自的“常用字表”,那么,大体推测:在客家话“常用字表”中而未出现在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中的字,不会超过3%,也就是说不会超过四五十个。之所以,人们印象中,客家话用字与现代汉语用字的差异度很高,其成因主要是:一是,大量“挖掘”化石汉字。即使是中古时期也不常用的繁难生僻汉字,也被“挖掘”作为客家话“本字”,且牵强附会地作出所谓的“考据”;二是,既有客家话文献中大量使用后造字、臆造字。这些后造字,既不是客家话的“本字”,也不符合汉字表义表音的造字原则。其“作用”大抵相当于:初学外语时,标注汉字借以提示读音,仅此而已。显然,大量后造字对于客家话书面表达的作用毫无价值、徒增混乱;三是,既有客家话文献,对于客家话词语无差别地有闻必录,不分主次轻重,对于一些客家话语言环境中都不常用的词语也罗列出来,从而形成了大量的化石词语及化石字、后造字、只表音不表义的借用字;四是,既有客家话文献,客家话与客家文化不作区分,许多仅仅反映客家人文风俗的词语也罗列为客家话词语(其实这只是文化风俗的区别,并非语言上的区别),从而使得客家话核心词语淹没在大量非核心词语之中。
本书作者再次强调,客家话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和更有效地传播。为此,客家话书面表达中,必须尽可能地降低其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差异程度。客家话与现代汉语的差异度高,学习客家话的门槛高,很大程度上是客家话学界人为割裂与现代汉语的联系而造成的。一是对于高频常用字词(特别是超高频字词)的选择,人为地割裂与现代汉语的关联性;二是对于标音系统的选择,人为地割裂与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关联性。
客家话,是流传有序的汉语言留存,客家话“本字”,绝大多数是从中古时期汉语中传承下来的,不应有大量的后造字(指《说文解字》之后所造之字),更不应当有太多的“臆造字”。如果大量采用生僻字、后造字、臆造字、无关字来书写,就会使得现代汉语读者误以为,客家话与现代汉语的差异度极大;实际上也无法使现代汉语读者简单地读懂客家话文本。这种客家话的书面表达方式,既不符合客家话的本来面貌,也向客家话的潜在学习群体传达了错误信息。
读音方面。现代汉语(普通话),虽然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但其读音与客家话的读音也是同源的,必然有许多字的读音是相同或相近的,读音之差异也是有据可循的。因此,以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读音来校核,也是合乎逻辑的。标音方面,如果以国际音标或其他标音系统,或自行设计标音系统,都会大大提高学习客家话的门槛和难度,使得有意愿学习和了解客家话的读者望而却步。大大制约客家话传承和传播的群体范围,对于客家话传承和传播起到的不是促进作用反而是阻碍作用。
本书作者提出两个主张以解决客家话书面表达的基础问题:一是对于超高频字词的选择,特别是虚词用字的选择,应尽可能选择现代汉语所采用的字词,同时赋予其客家话读音;二是标音系统应选择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其基础,在汉语拼音方案声母、韵母的基础上,根据客家话读音的特点少量增加声母和韵母。在汉语拼音四声声调基础上,鉴于客家话大量存在入声字,保留入声作为第五声调。其他声调不再保留,将之归并到相近的声调中。
如果能够从上述两个方面进行调整,那么,客家话与现代汉语的差异度,学习客家话的门槛,将降低80%以上,实现“降维”目标。这就是本书作者提出的“客家话书面表达优化体系”(客家话书面表达体系简洁化实用化)的核心内涵!
三、客家话基本属于日常口语。应着力将丰富的客家话口语体系,转化为完备的书面文字表达语言体系!客家话长期不作为书面语言,其口口相传过程中用字和读音方面存在大量讹变,既要合理留存,也要适当纠正。
客家话是文白相杂的语言,词语中的主干字来源于古汉语文言词语的留存,但为适应口语表达,在主干字上添加了不同时代口语化语素。导致客家话词语文白相杂、雅俗相杂、古今相杂。某些字词,在不同情态下、不同程度、不同感受,口语都能够区分开来,以语音语调的稍微差别加以分别表征。而在书面表达时,只能写成同一个字。无疑会对客家话的精准性有所损益。总之,客家话基本上归属于日常口语化的语言。
为了持续传承和有效传播客家话,只得两害相权取其轻。必须明确客家话书面表达的目的是:力图形成一套能够完备表征客家话文字表达(同时也有利于书面文字的口头表达)的语言体系。基本目的是能够创作出可写、可读、可说、可流传的客家话文本,进而可通过客家话文本准确记录留存至今的客家话语言、客家历史、客家社会。并不是要通过繁琐的考据去复原客家话的历史原貌,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要认识到,任何语言,口语表达,总是要远比书面文字表达丰富。所以,不要指望能够将客家话的口语用词能够穷尽地以书面文字方式书写出来。客家话的传承传播读物,只要能够将常用语句、一般情形下和一般情态下的常用字词句,完整自然地表达出来即可。对于特殊情形下、特定情态下的用语,只能寄希望于客家话母语使用者,通过视频音频记录。完全准确地将之书面化文字记录下来是难以企及的目标。
另一方面,客家话学界似乎有这样一个“思维定势”:认为,凡是客家话用词用字和读音的不同,都是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差异造成的。本书作者认为,古汉语字词音的留存与变化,只是形成客家话与现代汉语差异的一个成因,决不可忽视另外一个重要成因——客家话字词音的“讹变”。因为,客家话长期不作为书写用语,其口口相传过程中,用词用字和读音方面不可避免存在大量没有什么逻辑路径的讹变。说者和学习者都不知道精准的“本字”,只知道大致的读音。在传承过程中,很容易把一个词语的读音“讹变”为某个常见事物的读音,进而又反过来引致其字词的“讹变”(相关例子,参见本节后文)。这是导致用字和读音与现代汉语存在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传承过程造成的“讹变”,我们应当认真判别。对于一部分用词用字及其读音,可以语言的“约定俗成”准则予以保留;而对于一部分用词用字及其读音,则应通过适当方式予以纠正,尽可能避免走向无法还原的地步。
四、站在客家话传承传播主体的角度来看,客家话使用群体存在显著的断层,客家话快速走向濒危状态;客家话不存,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客家人群体、客家历史文化,也就很难存续。客家话的书面文字表达,客家话书面表达体系及其简洁化实用化,对于客家话以及客家文化的持续传承,存在急迫性。
由于历史原因,客家人迁徙落脚之地基本上是当时南方偏僻未开发的深山区,且不固定不集中,流散四处,客家话也就成为方言中唯一不以地域命名的语言。时至今日,随着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深入推广和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客家话这一古朴语言的命运堪忧,使用人口流失严重。其一,以客家话为第一语言的人口基本上都是山区村民,且为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他们保留传统语言文化,已经缺乏了先民那样的自主性,更谈不上在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其二,由于客语区分散,客家话语言力量分散,其语言势力正逐步递减甚至消亡,客家话逐步被“客普话”(客家味的普通话)所取代,“00后”客家人群能够说地道客家话的比例少之又少。其三,各地城镇化建设打破了山区原本的宁静,作为乡土语言的客家话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村民人口(特别是学龄儿童)涌向城镇,客家群体再次分散,客家话作为第一语言的人群大幅度且持续地压缩。其四,尽管在语言学术界,有一批专家学者进行客家话语言调查研究,但其影响范围极为有限。由此可见,当下,一门颇能代表汉语传统特色的方言语种——客家话,已然面临传承延续危机。一旦消亡,则万劫不复,到那时任何抢救举措都无济于事。因此,国家文化部门应未雨绸缪地推动有效保护措施,同时,最重要的是尽快解决客家话书面文字表达问题。因为,书面文字是记录和保存客家话语言以及客家族群人文历史最为稳固可靠的途径。
五、站在客家话习学群体的角度来看,诸多客家话字典词典,未能为客家话习学群体提供有效学习的公共品。这一问题,严重影响着客家话的传承与传播,亟待有效解决。客家话书面文字表达的标准化、简洁化、实用化,应成为客家话公共文献提供者的基本准则。
自从1883 年外国传教士于开始以书面方式翻译客家话圣经,开始了客家话书面表达历史。此后各个时期编纂出版了为数不少的客家话字典词典,但是迄今为止诸多的客家话字典词典毫无规则标准可言,客家话书面表达仍然处于一个混乱状态。仅以两部同以“梅县客家话”为基础的工具书为例,《客家话方言标准音词典》与《梅县方言词典》,其词语、用字、表音、释义等方面,毫无一致性。如此一来,对于客家话习学群体而言,根本起不到有效的工具书作用,徒增混乱。这一现象并非个例,而是普遍状态。相当部分的客家话词语,各个作者都有自己的用字,既不是一以贯之地采用“词义相符”原则,也不是一以贯之地采用“读音相符”原则,而是随心所欲。一个客家话词汇竟然有三种以上的写法!这是何其混乱无序的状态!对客家话习学群体而言,何所适从?如果,一部客家话字典词典,不能为客家话习学群体提供有效学习的公共品,那么,其对客家话的传承和传播就不具有工具书的价值。
客家话书面表达体系的标准化问题,亟待有效解决。客家话字典词典,必须为客家话习学群体提供有效学习的公共品,而不应是自娱自乐的个性化产品。客家话书面文字表达的标准化、简洁化、实用化,应成为客家话公共文献提供者的基本准则。
六、要用科学研究一般性准则——“奥卡姆剃刀原理”,来指导客家话书面表达体系的构建与优化。
客家话书面文字表达,客家话书面表达体系的构建,无疑是一项基础性的科学研究。科学研究的一般准则,也完全适用这一研究领域。
既有客家话研究,多数是语言学领域的学者完成的,他们对于客家话的传承传播做出重要贡献,但他们也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例如,客家话研究现状普遍情形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论是客家话“本字”研究、还是客家话读音研究,都缺乏整体逻辑性的考量。因此,必须从逻辑性、整体性、创新性的角度,对客家话既有研究现状提出改进方向。科学研究中的“奥卡姆剃刀原理”,作为科学研究中的一般性准则,非常有必要引入到客家话研究之中,“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即“简单有效原理”)的准则,在客家话书面表达的“用字”选择和“标音”选择中是有其切实的重要意义,即:如果对于同一现象有两种或多种不同的选择,我们应该采用简单或可证伪的那一种。由此,本书作者提出构建“客家话书面表达体系”并朝着简洁化实用化努力的目标,并在后文提出客家话表达体系“用字”基本准则、客家话类汉语拼音标音系统、客家话字词读音的选用原则,都是对这一科学研究原理在客家话研究中的体现。
引文格式:钟茂初.客家话书面表达优化体系探析[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24.
https://item.jd.com/14362433.html
https://product.dangdang.com/29830577.html
https://wap.sciencenet.cn/blog-1251036-1471420.html
上一篇:要以DeepSeek式创新来探寻传统节日晚会的突破口
下一篇:论客家话书面表达2:客家话书面用字问题及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