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吴敏:《深耕广植 探美求真——吕启祥先生访谈录》【《曹雪芹研究》2025.1】
||
吴敏:《深耕广植 探美求真——吕启祥先生访谈录》【《曹雪芹研究》2025.1】
黄安年推荐 黄安年的博客/2025年6月28日发布 第36811篇
【按:这里发布的是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已获硕士学位研究生吴敏同学,在攻读学位期间所撰写的《深耕广植 探美求真——吕启祥先生访谈录》,刊于《曹雪芹研究》2025年第1期第138-148页,导师俞晓红。感谢位灵芝女史惠寄。】
****************************
深耕广植 探美求真
——吕启祥先生访谈录
【访谈题记】 吕启祥,女,1936年生于上海,原籍浙江余姚。195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20世纪60年代曾参加全国统编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编写;70年代中期起,参加《红楼梦》新校本的校注工作,并参与《红楼梦大辞典》初版的编写。1985年被评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有《红楼梦开卷录》《红楼梦会心录》《红楼梦寻味录》,自选集《红楼梦寻:吕启祥论红楼梦》《红楼梦校读文存》,回忆文集《一份缘》。与友人合作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所著的大量红学论文、评论,参与的重大红学基础工程,都在学术界产生了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2023年9月22日和2024年8月26日,笔者先后两次对吕启祥先生作了较为深入的学术访谈。先生常在三言两语间答疑解惑,在文字开阖处给人以启迪心灵的力量。笔者不仅学到读书的方法、为学的路径,也被先生治红背后的为人品格深深吸引。先生的红学成果远非一篇访谈录可以涵括,笔者唯有如实记录访谈文字,以作为青年学子求教并获益于红学前辈的见证。
一 以师友因缘为助,徜徉“红楼”之中
吴敏:吕先生好!您曾说与《红楼梦》“结缘”是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您跨入红学领域的机缘是什么呢?
吕启祥:吴敏你好!与红学结缘,对我来说确实有偶然性,也是时势造成的。1954年中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东海南中学教化学和代数。三年后考入北师大中文系,1961年毕业后留在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任教,此后数年间参与的也都是与鲁迅研究相关的工作。1969年,我所在的中宣部被全员下放到贺兰山下的“五七干校”长达四年之久。当我翻开许久未读的《红楼梦》,在那文化沙漠中真是如获甘霖,如逢知己。也因自己颇有了人生阅历,切己的人生感受同书中那沉浮变幻真假难辨的人生意蕴不期而然地相通了,读下去有无穷兴味、诸多感悟。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被借调到《红楼梦》校注组,在前辈学人的带动下,正式涉足红学领域,常在会心感悟中自得其乐,在感动处发力开掘。这大约是种因结缘之始吧。
吴敏:您早年在现代文学领域耕耘时,从事的是与鲁迅相关的研究,后来专门发表过有关鲁迅红学研究的文章。这种学术准备对您后期的红学道路,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或者说鲁迅的红学研究,至今对我们仍有哪些启示?
吕启祥:相较于具体观点,我认为鲁迅先生研究红学的路径,可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一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来掌握一部作品最本质的特点。多年来的《红楼梦》评论,不是阶级分析法用得太多,而是乱用一气或者不得其法,糟蹋了这部作品,也败坏了方法本身。二是严格遵循和创造性运用艺术创作典型化法则,强调《红楼梦》创造了典型而并非作者的自传,反对将小说人物等同于小说的“模特儿”(生活原型)。三是始终保持客观的“赏鉴”的态度,反对把文学作品当作道德说教或生活图解。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考订作者、研究时代等史实是完全必要的,但这种研究绝不能包括或代替对作品本身的研究。其实不仅在红学研究领域,任何时候,鲁迅作品对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而言,都是极其宝贵、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读鲁迅,品读其治红方法和路径,有固本培根之效。
吴敏:在进入红学领域前,还有哪些经历为您的红学之路打下了学术基础?
吕启祥:在北师大受教的点点滴滴,一直使我受益。1957年我初入北师大,分量最重、课时数最多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由郭预衡先生执教。在郭先生处,我获得了富于启发性的文学史教育,领略了一种“史家”风度。他讲课,重方法、重分析,在当时革命批判的大环境中,使我们这些学生的艺术感受力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呵护,在后来的红学研究中,这份艺术感受力得以继续保全和发展。其实郭先生从未教过我如何写作,但他简约干净、颇具鲁风的语言风格,自然引起了我的效仿。20世纪60年代初,我加入了全国文科统编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得见唐弢、王瑶、刘绶松、杨占升等一众前辈专家的学养和风范。主编唐弢先生像所有胸襟博大的前辈一样,没有嫌弃青年的稚嫩,曾给予我“过程比结论重要”的箴言,教给我“治学先治史”的基本方法。另外,关于文字功夫,弢师总是强调写文章笔下要讲究一点。以后每每提笔,便会不自觉想到“文字要干净,辞采宜讲求”的忠告。
吴敏:能谈谈您与一众红学前辈友人的学术交往,以及从中获得的启迪和帮助吗?
吕启祥:我涉足红学领域,是从参与《红楼梦》校注这一集体项目开始的。启功先生在《红楼梦》的注释问题上给了我很多指导和帮助,他有关于《红楼梦》注释的专门文章。为了《红楼梦》校注的事,我那时隔些日子便会到启先生家中求教。先生很平易,从不故作艰深,答疑解难,就如聊天话家常,随时随地给我指点。所以在《红楼梦》注释问题上,我始终把启功先生的注和他关于注的主张记在心上。比如注不要太繁,应该繁简得宜,注不宜艰深,要让读者懂得等等。
还有李希凡先生,他于我更像是一位亲和的长辈。先生仁厚,爱才举才,深知我不愿汲汲于名利的心迹。他曾给初版《红楼梦大辞典》的修订负责人专致一信,陈明修订目的在学术,特别提出:“启祥同志就不要担任什么名义了,她还是编委。”这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他还充分评价我所参与的红学基础工作为“前海红学”。这是对基础研究、对各学科奠基工程的重视,是对群策群力朴实学风的肯定。另外,希凡先生始终维护红学的正常生态,抵制各种歪风邪气。他对一切戏说、揭秘、解构及新老索隐说“不”,一直重申《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审美品性和不朽价值。对小说作者的种种新说也不以为然,始终维护曹雪芹的著作权等等。我曾在2016年“李希凡与当代红学”学术座谈会上,郑重提出:希凡先生是新时期红学航船的“压舱石”,虽居幕后,然而不可或缺。
我要感谢冯其庸先生。他非常包容我的学术兴趣,从来不限制我、要求我,任由我运用自己认可的学术方法和语言风格。他从来没有给我出过题目或划定畛域。对于我的研究,先生不仅能够包容,而且能够理解,尤为可贵的是他往往有一种深度的理解以至内心的共鸣。二十一世纪初期,“秦学”走红、揭秘盛行,很多人从各个角度批驳刘心武。人们通常觉得秦可卿这个人物塑造得挺失败的,好多地方都很概念化。我也想过这个问题,难道除去探佚、还原、索隐、猜谜,秦可卿这个人物形象本身真就无话可说了吗?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作品本身,回到秦可卿这个人物形象本身。于是有了《秦可卿形象的诗意空间——兼说守护〈红楼梦〉的文学家园》这篇文章,随后发表在2006年的《红楼梦学刊》上。冯先生看了这篇文章之后,立刻给我打了个越洋电话(我那时候去美探亲,人不在国内),并赠诗一首:“红楼奥义隐千寻,妙笔搜求意更深。地下欲问曹梦阮,平生可许是知音。”冯先生说他翻开这篇文章后,不知不觉地就看下去了。
关于秦可卿这一艺术形象,端木蕻良先生曾有十分精到的见解。在《说不完的红楼梦》一书“可卿之谜”一节里,他明确提出从作品的艺术效果和作家的思想境界来看,曹雪芹的改写大有深意在。我在自己的文章里,主张依凭作家改塑的实际描写,将秦可卿作为情的化身、美的象征,对端木老的观点有过发挥,我想这也是符合端木老心愿、符合他相关论说和创见的。
另外,蔡义江、胡文彬、刘敬圻等师友,也给了我诸多的帮助。
吴敏:您觉得,学术研究和个体人生之间,有什么关联相通或相互促进之处吗?
吕启祥:世间的沧海桑田、人事的升沉荣辱,原本既可近看也可远观,小说里的一枝一叶、一颦一笑,同大千世界社会万象连通着,人生世上固然要执着,当下更应寻求超越。我中年时代,在贫瘠的生活和窒闷的空气里触摸到了《红楼梦》的血脉气息,切己的人生感受和作品的意蕴不期而然地相通了。于是,在改革开放的春天来临之时,面对《红楼梦》和周遭的学术环境,我由衷地感叹“形象的丰满和批评的贫困”。后又尝试探求林黛玉形象的文化蕴含和造型特色,勾勒史湘云的不羁之态和魏晋风度,寻绎王熙凤的魔力和魅力,开拓秦可卿形象的诗意空间等等。新世纪前后,着力寻求《红楼梦》的深层意蕴,蠡测它的超验之美和人性深度。
前辈学者吴宓开过一门“《红楼梦》与人生”的课,想来必定丰富多彩。每个人的人生都不相同,那课程也就生生不已了。我青年时代崇尚阳刚之美,中年以后才渐渐读懂红楼。在完成红研所一些集体项目的同时,我将自己对作品的研读所得陆续成文,大体按时段编入几本论文集中,开卷、寻味,时时于会心处自得其乐。现在想来,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尽相同,个体在求索《红楼梦》艺术真谛和人生真味的路上,也永远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二 以实证研究为底,校勘注释文本
吴敏:您1983年写的《〈红楼梦〉新校本校读记》(《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3辑)一文,提出了“新校本无论从艺术直觉出发还是从理性分析着眼,都是优于原通行本的”观点。请问您撰写此文的初衷和契机是什么?
吕启祥:当时的校注组中,把新校本和原通行本直接加以比较对读这件事,还没有人来做。因为版本研究的专家,都去研究那些早期的抄本了;而一般的读者,恐怕虽有此心而无暇。事实上,将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新校本和已经流行的原通行本直接进行对校,是一件有意义、值得做的事情,可以作为赏鉴和批评的一种参考,也为评论和研究提供一种方便。做这个工作是为读者想。你想想,已经有了一个流行数百万册的普及本,为什么还要另做一个本子?我自己读起来也是,程乙本已经很流畅了,为什么还要去校另一个本子?所以为读者想,我就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就下了一些笨功夫——把两个版本的前八十回逐一校读,对照出了好几百例重要的差异,辑成了近7万字的《〈红楼梦〉新校本和原通行本正文重要差异四百例》(见《红楼梦开卷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并在这个基础上写成了《〈红楼梦〉新校本校读记》。需要说明的是此文并非严格意义的版本研究,不涉及本子的源流演变;而只是从现状出发,从文学的角度着眼,诸如语言文字、叙述描写、人物形象、思想意义等方面,综合考察它们的异同长短。在我做的实证性研究里,现在看来比较有用的,要包括这篇文章。
吴敏:在您看来,相较于原通行本,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新校本有何优长之处?
吕启祥:通体看去,两个本子在语言上的差异是文白之别和南北之差。较之原通行本,新校本始终保持着合乎一部古典白话小说典雅凝重的语言风貌。另外,新校本南风盛,原通行本北俗多。比照之下,新校本的用语是准确的。从细微之处的用语来说,新校本往往于一字之差间,表达得更加准确、合理,富于表现力。从大段文字的差异来说,新校本在不少地方比原通行本多出了若干文字,有时竟达整段整页之多。总的看来,这些部分并非闲言赘语、节外生枝,而总是这样那样地丰富了人物和情节。
在艺术形象的改动和变异上,新校本的某些艺术形象发生了较大的变异,甚至连思想倾向都有所不同了。众所周知的便是,尤三姐在两个本子中已然是两个不同的艺术形象了。针对这一改动和差异,人们在多数情况下的认识还是一致的,即新校本的有关形象,不论其艺术水平还是思想意义,都是优于原通行本的。这也是两种本子差别中最引人注目和常引起讨论的问题。另外,就书中那些直接关涉现实、讥评时事的词句和段落而言,新校本要更鲜明锋利一些。还有一些表述作者创作思想的文字,也比原通行本来得丰富和精彩。许多论者常常引用,作为研究曹雪芹美学思想的一种依据。从根本上看,新校本的优点基本上也是脂评本的优点。脂评石头记的乾隆抄本,由于较少受到后人的删削篡改,较多地保存了曹雪芹原著的面貌。据以整理的新校本也因此比较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这可以说是新校本种种优点之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一条。
总的来说,新校本无论从艺术直觉出发还是从理性分析着眼,都是优于原通行本的,这已经被广大读者所接受,被几十年来的事实所证明。
吴敏:关于本子,您还为北师大校注本写过一篇上万字的书评,发表于新校本盛行、脂本广受重视之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否可以反映出您在《红楼梦》版本问题上的一些态度?
吕启祥:是的,这篇文章题目是《填空补阙 厚积薄发——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红楼梦〉校注本》(《红楼梦学刊》1989年第3辑),写于1989年3月。我认为北师大本的发行,在《红楼梦》版本史上自有其价值。它以程甲本为底本,尽量保持其原貌,普通读者据此也可以对程甲本取得一定的发言权,对其与早期脂本和程乙本之间的异文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
曾经有人批评我说,什么都是脂本好,什么都是新校本好,难道通行本子就不好吗?事物总是相对而言的。就新校本来说,它的缺陷、不足、错讹、失误,可以挑出许多许多来,仍需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使之更加完善,更加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客观来说,原通行本也有它的若干长处,它较为通俗顺畅,有的地方文字较为简洁干净,人名有意识地加以统一,生僻字和异体字也改掉了,个别语言表达也有优于新校本的地方,这都利于阅读和普及。但这两个校注本的差别,从根本上来说是脂评本和程乙本的差别。校注工作是基础,需要尽可能地选择可靠的、接近曹雪芹原貌的底本来进行。我其实在版本问题上没有偏见,我重视但不迷信脂本。我在脂本流行、很受重视的时候,并没有一味说脂本有多好。程本系统也有好的本子,以之为底本的北师大本便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我在重视脂本的同时,也把程甲本当作一种重要的本子。因而这篇书评在当时还是比较有影响的。
吴敏:除了校注工作,您还曾和友人合作主编过《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这部资料书早已成为《红楼梦》研究者手头的必备之作。请问这项工作的难处何在?
吕启祥:由于长期的积累,我们搜索和汇集了大体自1911到1949年间,发表在全国各种报纸杂志上的红学论评500余篇。本书的大量资料,从收集、复印、放大,到整理分类、校阅厘订,无不渗透着辛劳和汗水。此书的前言,长达两万多字,题目叫《本世纪上半叶红学论评三百篇述略——〈红楼梦稀见资料汇要〉前言》(《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4辑),便是我在这项扎实的实证工作的基础上写就的。这篇前言是下了功夫的,是在看了这期间所有的红学文章包括长文短论之后,加以分类归纳写成的。很多报刊文章,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林东海先生跑到柏林寺报刊馆去照相,然后复印出来的——非常不清楚。那时候照相技术也很落后,我们把135毫米的缩微胶卷放大,看起资料来很费劲。这篇前言写得很辛苦,很不容易。《红楼梦学刊》编《不惑之获:〈红楼梦学刊〉40年精选文集》时,大家都说把这篇文章收进去,后来我自己反对,拿掉了。因为它太长了,收了它后,别的文章就进不去了。
吴敏:在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中,您是如何看待“实证研究”与“文学阐释”两者关系的?
吕启祥:我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就两种类型。一类是实证性的,涉及新校本的校勘和注释,以及红学基础资料的整理总结;一类是对《红楼梦》本身的文本阐释,也即你所说的实证性研究和阐释性研究。我认为二者之间,校勘注释以及作者时代等是基本功,是基础,否则所论难免成为沙上建塔,根基不牢。比如薛宝钗的形象,在原通行本里,好多处不是描写宝钗的文字,被安到宝钗头上了;有些关于宝钗自身幽默个性的文字,又被去掉了。我记得庚辰本第四十九回里,薛宝钗打趣菱、湘二人没昼没夜谈诗,说“呆香菱之心苦,疯湘云之话多”,可见宝钗也能诙谐,不只一味说教;另外像贾政,后期有一整段名利大灰、不再以功名强求贾宝玉的文字,这些在现在的程高本里都没有了。还有一些细节,比如刘姥姥听到的“打箩柜筛面”声儿,现在程高本中是“打箩筛面”,像这样的一字之差,所带来的是准确和不准确的区别。所以我觉得可靠的本子是最重要的,如果根据一个不可靠的本子,那么很多人物就走样了,所谓的分析也就虚浮无根。但实证研究大体上属于史学范围,我的学术兴趣在文学,在这方面用力较多。
三 以审美阐释为功,守望精神家园
吴敏:阐释类您用力较多的,要数《红楼梦》人物了。为什么您会选择薛宝钗这个人物,作为阐发《红楼梦》人物世界的起点呢?
吕启祥:这篇文章叫《形象的丰满和批评的贫困——关于薛宝钗这一典型形象及其评论》(《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八辑)。薛宝钗的艺术形象是丰富复杂的,但当时关于《红楼梦》艺术批评的文章还很少,因而从数量上说是很贫困的;另外从过往对薛宝钗的评论来看,也是简单贫乏。然而这个题目适用于《红楼梦》中的任何一个人物,讲薛宝钗可以,讲刘姥姥也可以。因此我希望通过薛宝钗这一代表性人物,提出“形象的丰满和批评的贫困”这一普遍性问题,来期待艺术批评的繁荣。《红楼梦》中的人物,总体来说形象都很丰满,但当时的批评普遍比较贫困。那么今天的批评是不是贫困的呢?我认为依然是贫困的。现在我们很多的批评还没有到点到位。没有一个人敢说,我的艺术批评就和《红楼梦》的人物形象相称了,我们的研究只能不断靠近《红楼梦》的形象世界,而不能穷尽它。所以面对《红楼梦》形象世界的丰满,批评永远是贫困的。我认为是这样。
吴敏:您曾在《文史知识》等刊物上发表了“红楼”人物的系列短评,但有些人物,比如史湘云、王熙凤等,除短评之外另有长文,这些关于同一人物的长文和短评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吕启祥:这就要说到一些人物的写作契机了。湘云我有一长一短两篇文章,长文题为《湘云之美与魏晋风度及其它——兼谈文学批评的方法》(《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2辑),写于1985年。后来把它压缩成短文,发表在《文史知识》上了。那时候《文史知识》正策划一个关于文学人物的专栏,编辑马欣来邀请我去开栏,写第一篇文章,并且指定写史湘云。我就把湘云的长文浓缩成千余字、题为《豪兴·隽才·厄运——谈史湘云》(《文史知识》1985年第8期)的短文。以后,我陆续在“文学人物画廊”这个栏目里,发表了关于宝钗、宝琴、晴雯、平儿、刘姥姥等人物的文章,其中有些文章是现写的,有些是根据已有长文压缩而成的。关于王熙凤,我也写过几篇文章,有一篇叫《“凤辣子”辣味辨——关于凤姐性格的文化反思》,发表在《古典文学知识》(1989年第1期)上。这篇文章虽然短,也还是比较重要的。北京大学让刘梦溪先生来主编一本《红楼梦十五讲》的教材,我把有关王熙凤的文章整合起来,写成了由他命题的《王熙凤的魔力与魅力》,搁到那个教材里面去了。还有《花的精魂 诗的化身——林黛玉形象的文化蕴含和造型特色》(《红楼梦学刊》1987年第3辑),对林黛玉形象的“愁”,由表及里、由今至古作了一些分析和梳理,因而这篇文章还是比较有影响的。
吴敏:这些“红楼”人物的专论已足以构成一个系列,但您却就此停笔,以后少有专门论人物的文章了。这是为什么呢?
吕启祥:我读书常常“不求甚解”,只要会心感悟就自得其乐,在感动处发力开掘,如此而已,不求大而全。冯其庸先生曾建议过我,把每个人物都论到,来个“人物论”。也经常有友人问我,为什么不把所写之文整合成一个“系统”。我想,举一可以反三,何必求全呢?
这些《红楼梦》里的人物,我总的一个意思,首先是着眼看她们总体的审美价值,比如说凤辣子的“辣”,史湘云的“豪”。薛宝钗总体上是“冷”嘛,我曾概括过她外貌上的冷艳——薛宝钗是很漂亮的一个人;性格上的冷静——她遇事不像薛蟠那么毛毛躁躁;有的时候就变得有点冷酷了,简直到了不动声色的地步。林黛玉很难概括,我用了“花的精魂,诗的化身”,她身上有一种仙气儿——“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嘛!除了在审美价值上对人物进行总体把握,我认为一定要注意到每个人物的复杂性。人物本身一定会有一种内在的矛盾,比如薛宝钗——冷和热、情和理、远和近,这些相生相持的内在矛盾,会使她在各种情势底下有不同的表现。我写每个人物,都希望追求这种独特性和复杂性的统一。我也不是说一定讲人物的艺术性,艺术性和思想性是分不开的。我所用力的,是从人物入手,对人物形象的审美品格进行开拓。希望这样能够回答“形象的丰满和批评的贫困”这个问题。
吴敏:您还将“艺术意象”引入《红楼梦》的形象分析,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鉴赏视角,呼吁研究者守护《红楼梦》的文学家园。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吕启祥:优秀的作品创造艺术典型。但对《红楼梦》这本书,我认为不仅要用传统的艺术典型论,还应该引入艺术意象来解释。比如秦可卿这个人物,她在《红楼梦》里头很特殊。曹雪芹把“托梦”等重大情节、重要关节托付在秦可卿身上,已经不光是在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塑造人物了。这些情节的意义和分量已经远远超过和压倒了那些叙述性文字,让秦可卿成了情的意象的化身。其实不只是可卿,像宝钗、黛玉这种人物,在现实生活里是没有的、不可能的、找不到的。这些人物明显带有了作者意象化的塑造倾向。要说最最生活化、最最符合典型论的人物应该是王熙凤。
并且,我认为研究要遵循对文学作品的直观感受。关于秦可卿的大出丧,我曾经写过一篇《悲喜相映 庄谐互出——谈〈红楼梦〉的喜剧因素》,发在《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3辑上。我当时认为辈分低年纪小的秦可卿与风光异常的大出丧之间,暗含一种不协调不相称的喜剧因素。后来想想,这和我艺术感受不符。因为对可卿出丧这件事情本身,我没有什么喜剧感受,相反,我觉得它是正大的。秦可卿是《红楼梦》十二钗里面第一个死亡的人。一个美的象征、一个情的化身毁灭了,这对贾宝玉来说是很大的刺激,所以他一下子吐血。很多人对此作了一种很不好的解读,我认为不是这样的——贾宝玉和秦可卿之间没有那种暧昧的关系。“秦学”之所以模糊以至失落了《红楼梦》的本来面目,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忽略了《红楼梦》是文学、是作家的审美创造这一要义。
吴敏:您认为《红楼梦》这部作品天然带有一种神秘感,并将《红楼梦》视为现代人的精神家园。可以请您谈谈对这一观点的看法吗?
吕启祥:我认为,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总会有一种神秘感——一定会有一种神秘感,也即一种内在的、和当代人心灵相通的东西。大千世界中的形形色色、人生的百味百态,几乎都可以在《红楼梦》中尝遍历尽。人生的悲欢离合、聚散起落、两难选择等等,书中很多切己的感受和当代人的情绪都是相通的。人们可以由此得到极大的精神慰藉,产生一种认同感和皈依感,获得心灵的满足和安宁。因而这部描写过去时代生活的作品,到现在仍被人们珍爱,被视作精神家园,原因恐怕在于能够启悟哲思安顿心灵,使人的精神有所慰藉,有所皈依,有所归属。曾有漂泊海外的学人满怀深情地诉说,《红楼梦》在身边,故乡和故国就在身边。《红楼梦》俨然已经成为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不论处于何种人生境地,都能给人启迪、安顿的力量。
作为精神家园的《红楼梦》,更高一层的意义在于使人的精神得到提升、超越以至更新,也就是从世俗的烦扰困惑中解脱出来,以一种更为从容洒脱的心态面对人生,面对自我。正如有的论者精到地指出:“色就是色,色不是空。”真实的大千世界的色色图景,相较于种种梦幻隐喻,更能唤起我们的人生经验。既为文化经典,自有其穿越时空的品质,人们更应该关注其恒久的、内在的、深层的东西,对经典抱有一份敬畏之心。所谓敬畏,并不意味着经典只能高高在上,不可触摸,而是说我们应当用一种严肃的真诚的态度对待这部经典之作,力求以真挚坦诚之心去同作品和作家对话,而不是导致疏离和隔膜。倘若不能达成这种穿越时空的沟通,不能展开双向的心灵对话,那么经典就没有生命力,这份神秘感也难以葆有了。
对《红楼梦》这份深层意蕴的追寻,是无穷尽、无止境的,这也是现在很多人说《红楼梦》的文章做不完的原因。但这始终是我的一种愿望。现在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很多很多,什么边边角角犄角旮旯都给挖掘到了。我想说的是,研究者笔下要留情,要留下《红楼梦》的那点神秘感。
吴敏:半个世纪以来,您见证了红学的发展,也一路推动着红学的发展。您是如何看待红学研究的热潮的?
吕启祥:放眼四顾,历史无情亦有情,泡沫泥沙终会淘汰,真知灼见终将留存。对于时下红学,我所希望的无外乎八个字:退热降温,返璞归真。我不希望红学那么热闹显眼;复归平静,回归到一部小说,才是其本色。文学不会消亡,对于《红楼梦》这样的文学经典的阅读和赏鉴也不可能被替代。《红楼梦》文学文本所创造的诗意空间,能够激发人的想象,丰富人的情感,启迪人的智慧,提升人的精神。对于健全的人生而言,审美等精神需要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植根于内心的促进人性全面发展的需要。这里只想就自身的感受和心愿说一句话,那就是:把《红楼梦》还给小说——也即回归它作为文学艺术的本位。它不是历史,不是哲学,更不是谜语,不是密码。《红楼梦》是文学,这是常识,是必须守住的一条底线,也是艺术的生命线。守护文学的家园,也就是守护生命的灵性,守护审美的创造。
吴敏:谢谢吕老师!今天的访谈涉及《红楼梦》的文本文化研究、校注等实证研究,还谈及了当代红学人物等等,让我收获满满,学生将长久受益!
吕启祥:也谢谢你的访谈。在耄耋之年和小于自己年龄六十多岁的年轻学生交谈,相信不论是对于求教的青年学子还是接受访问的学者,都是有益的。
结 语
作为红学历史的见证者,吕启祥先生身历当年红学之盛,也目睹如今红学研究向前发展。她用毕生精力和切实行动守护着红学的文学家园、精神家园,“在感动处发掘”,不断开拓《红楼梦》的审美品格和文化意蕴。不论是为学还是为人,真正做到了内外兼修、始终如一,处处显露学者的良知和勇气。此种为学功力和为人品格,值得后学长久回味,引为高标。
(本文经吕启祥先生审定)
(作者信息: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照片13张拍自《曹雪芹学刊》2005年第1期
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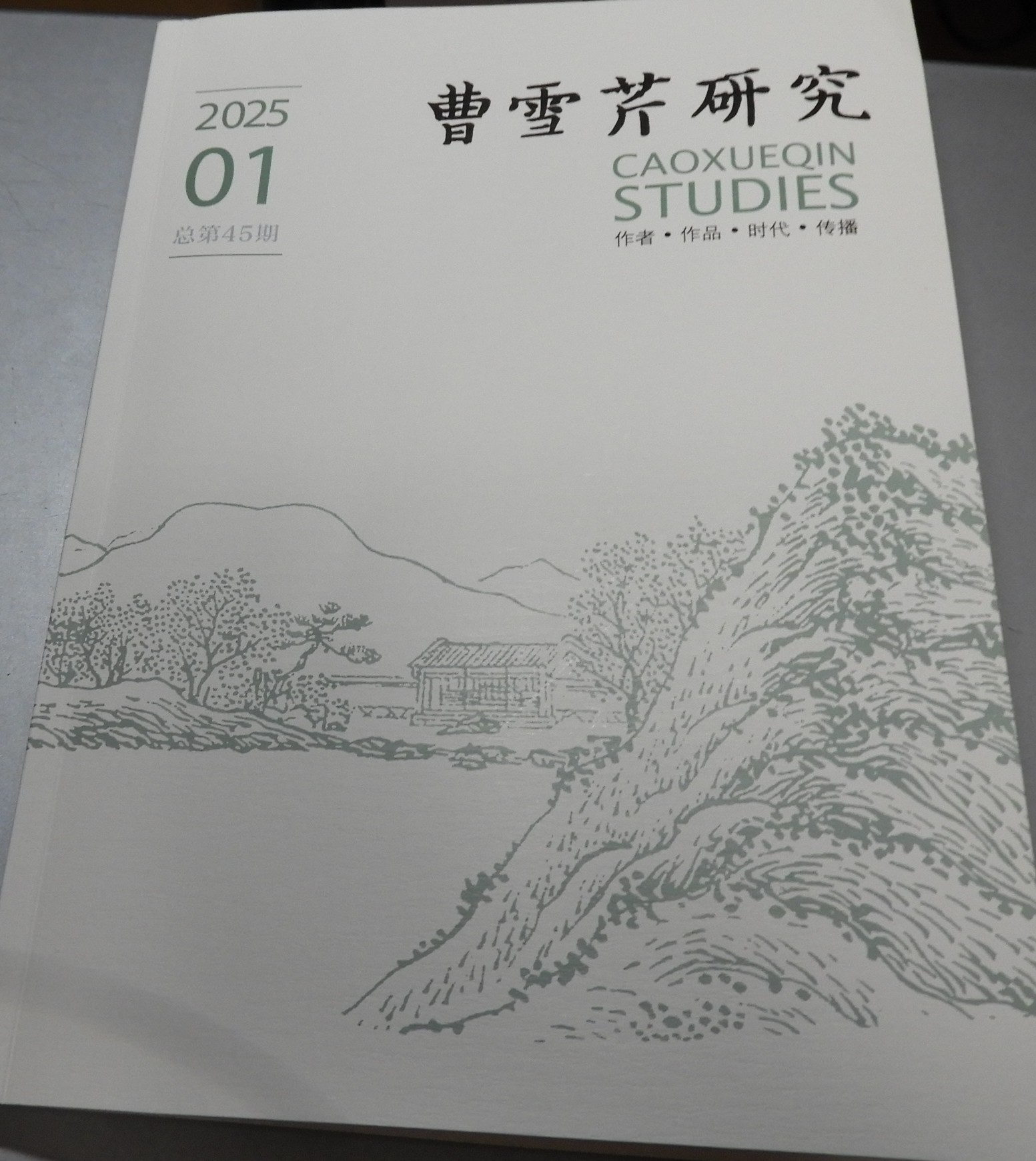
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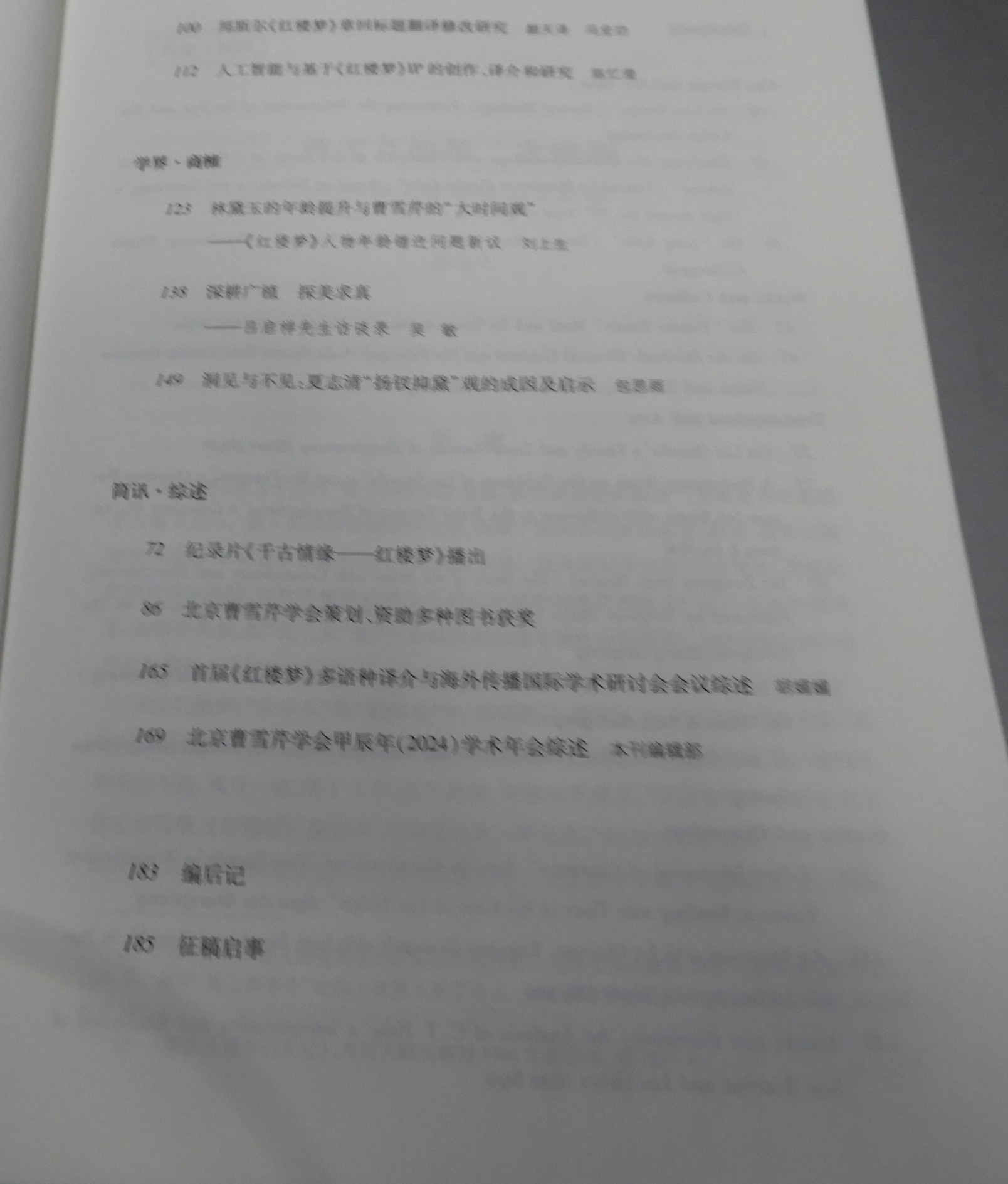
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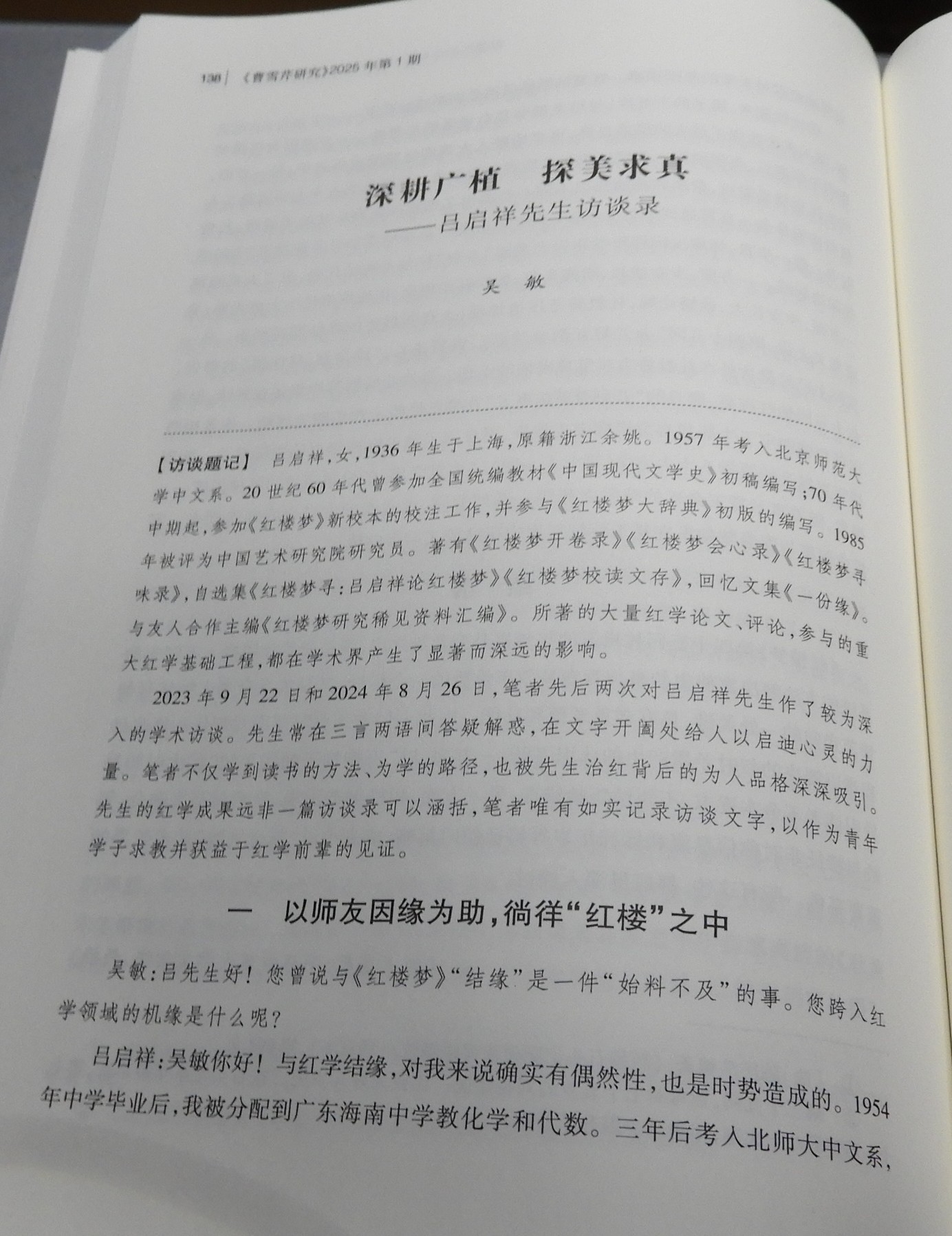
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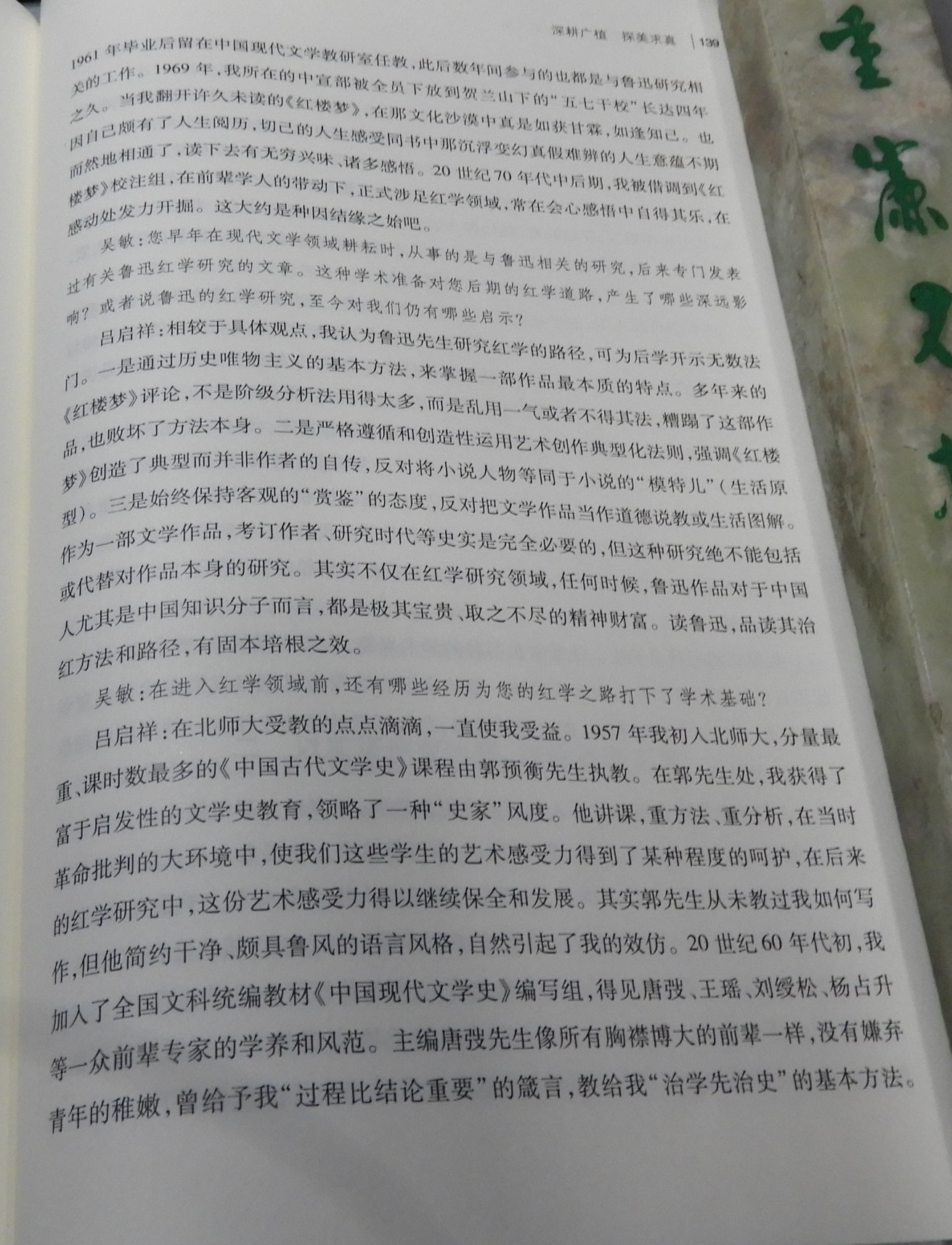
5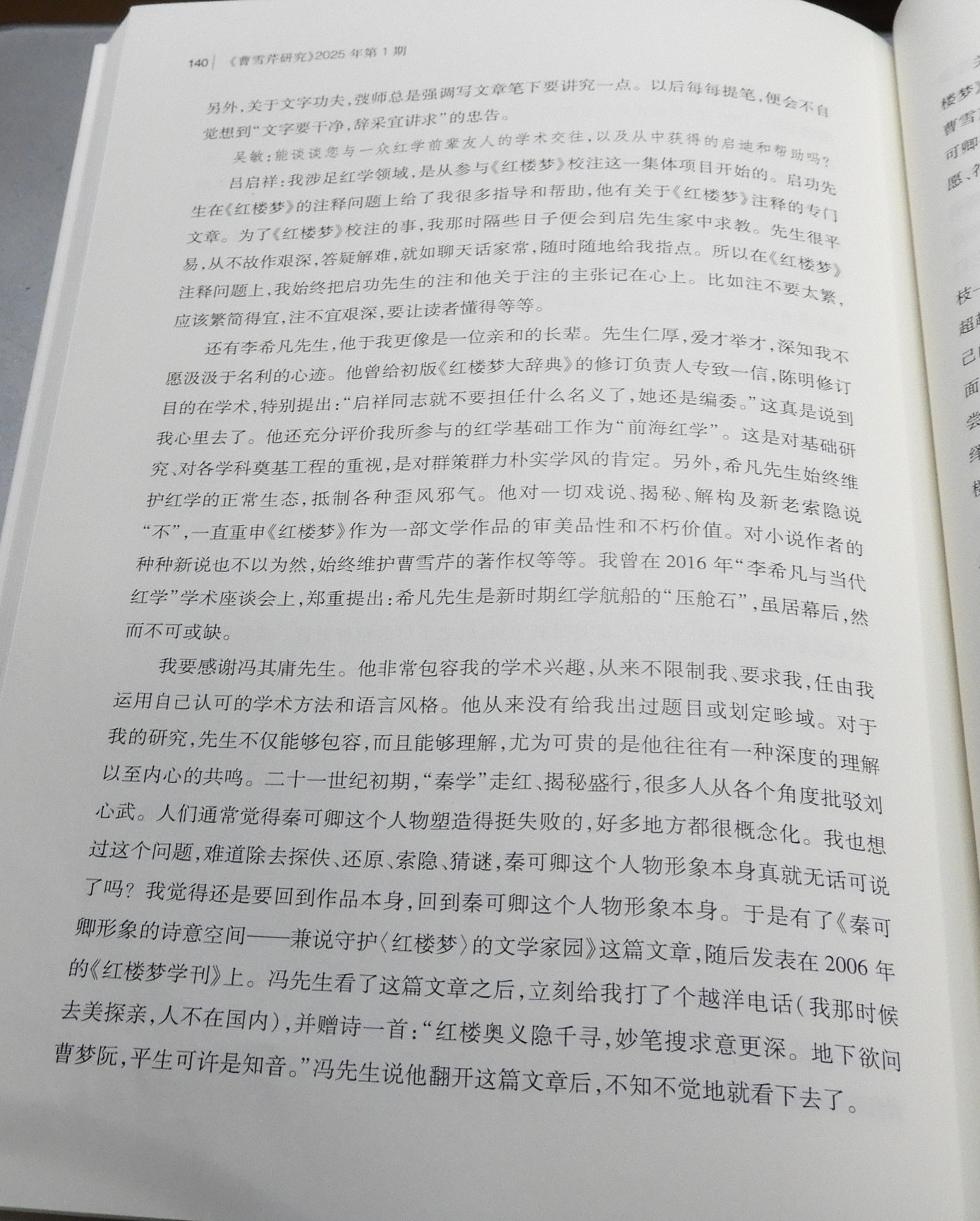
6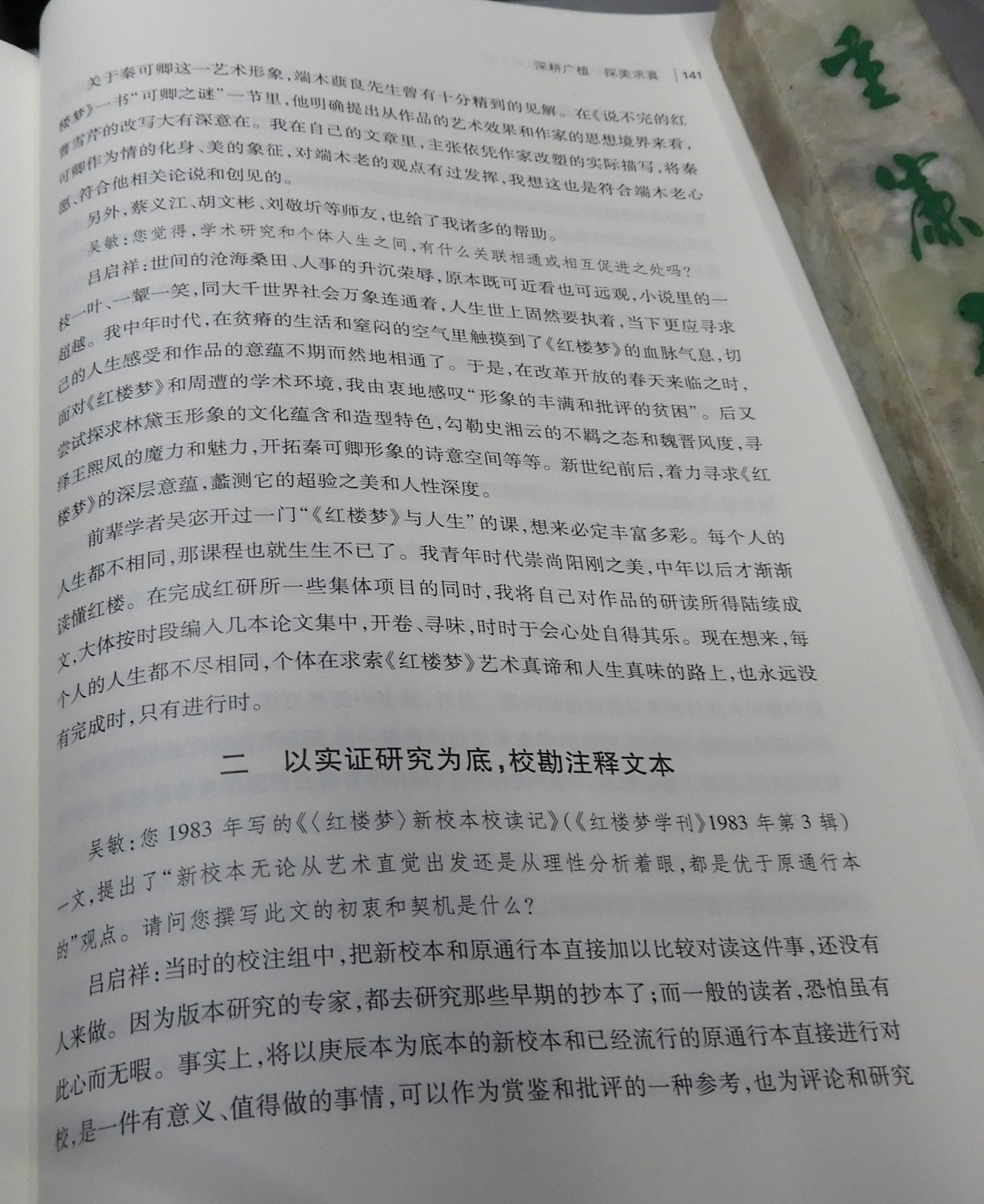
7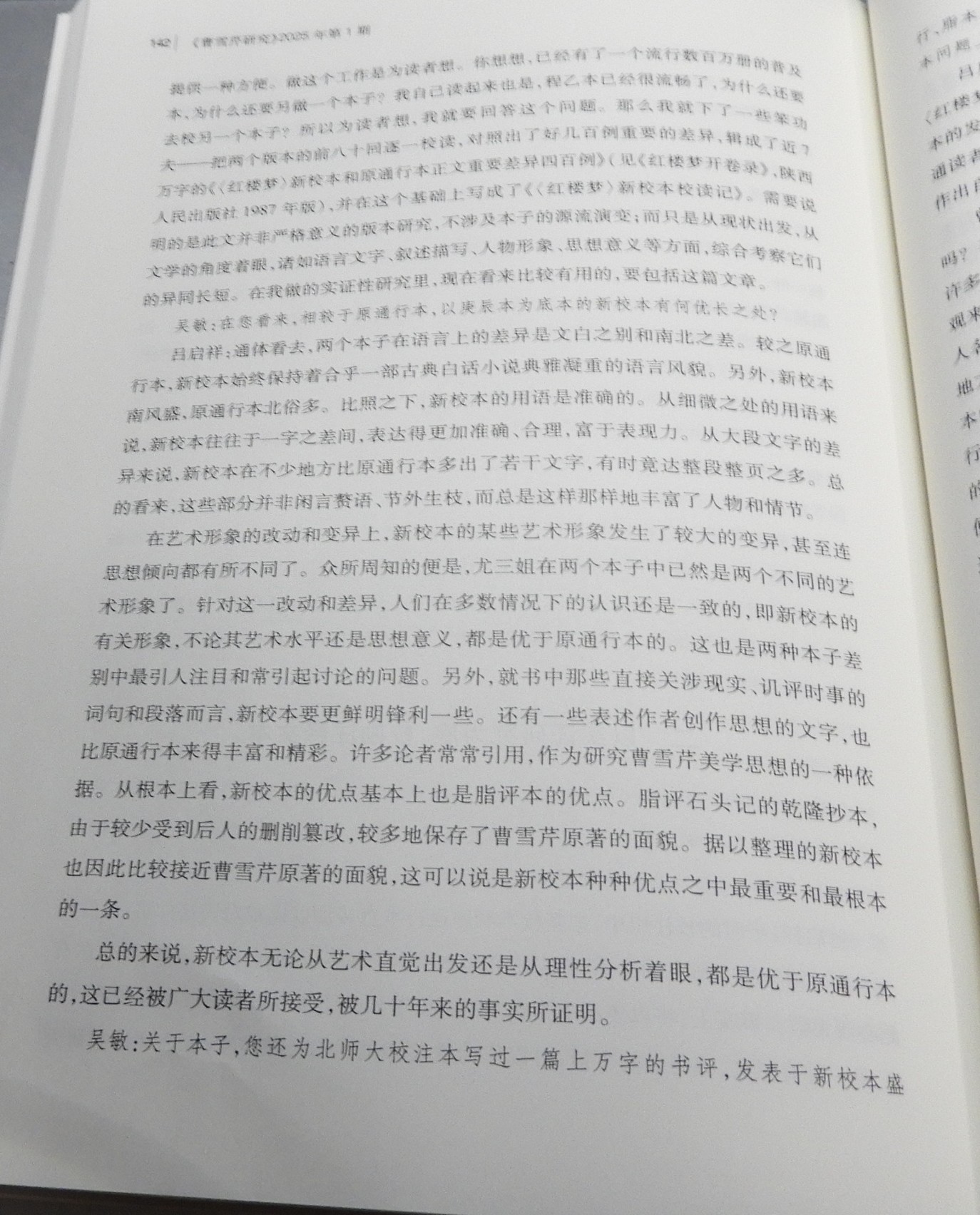
8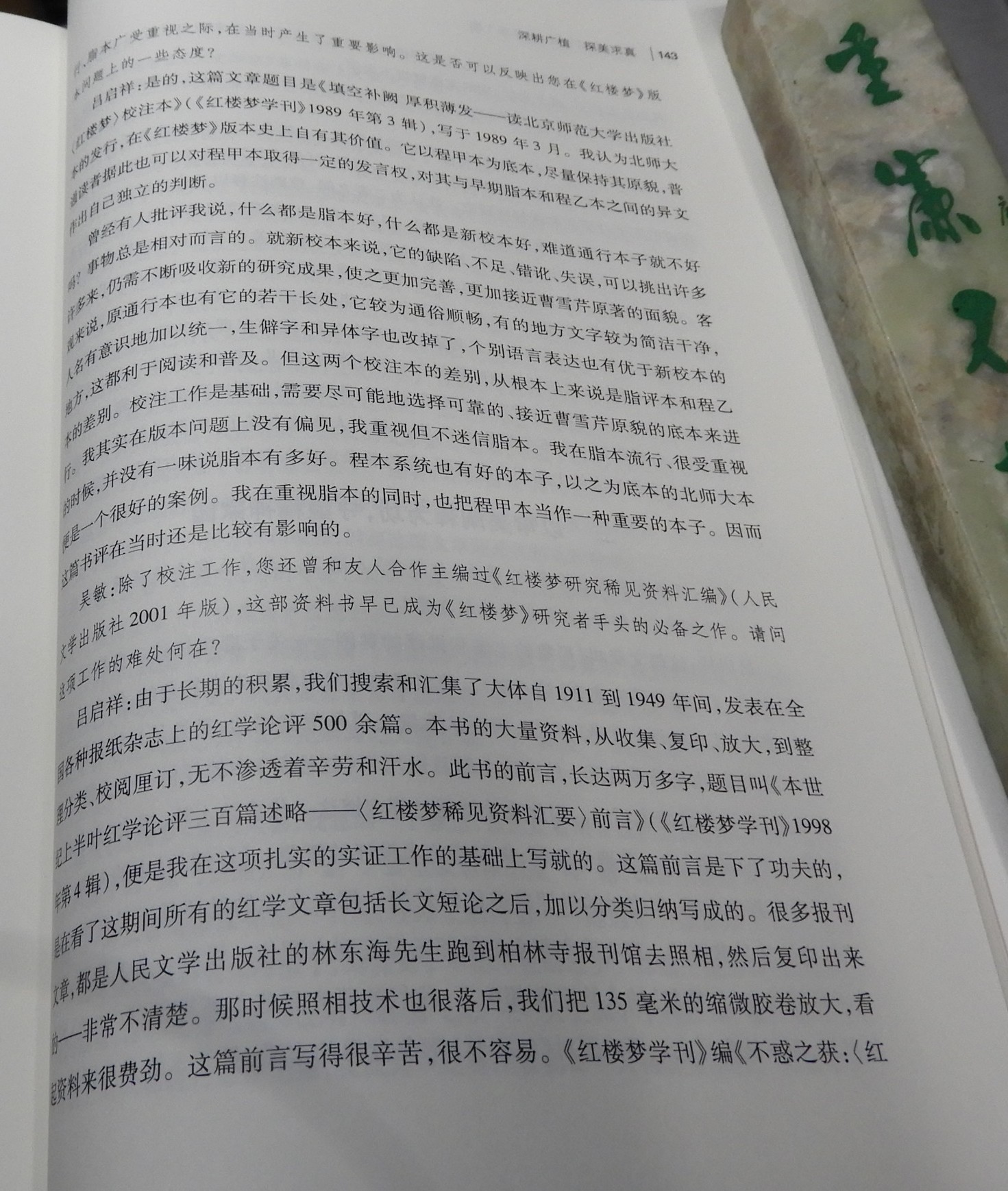
9
1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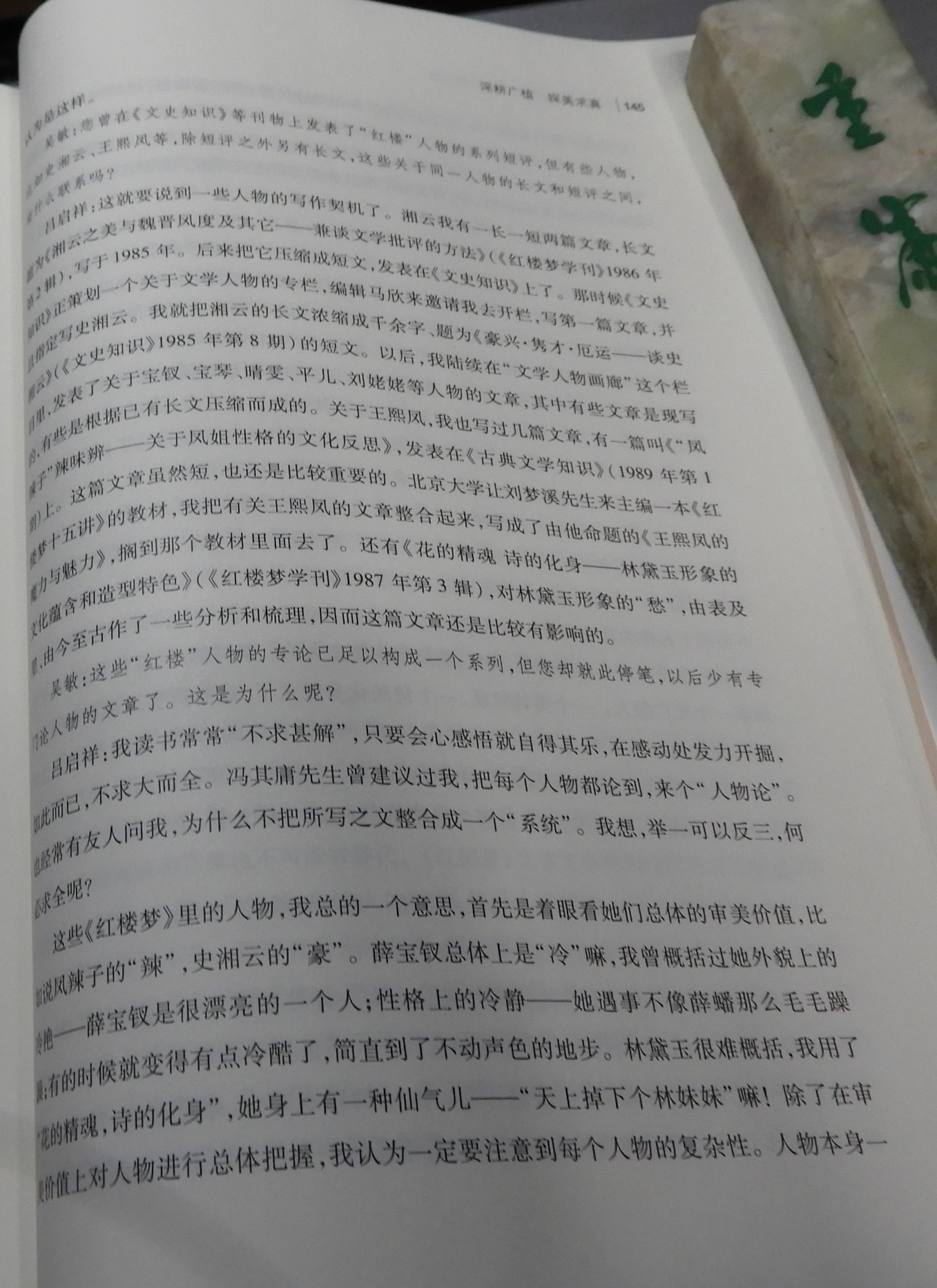
1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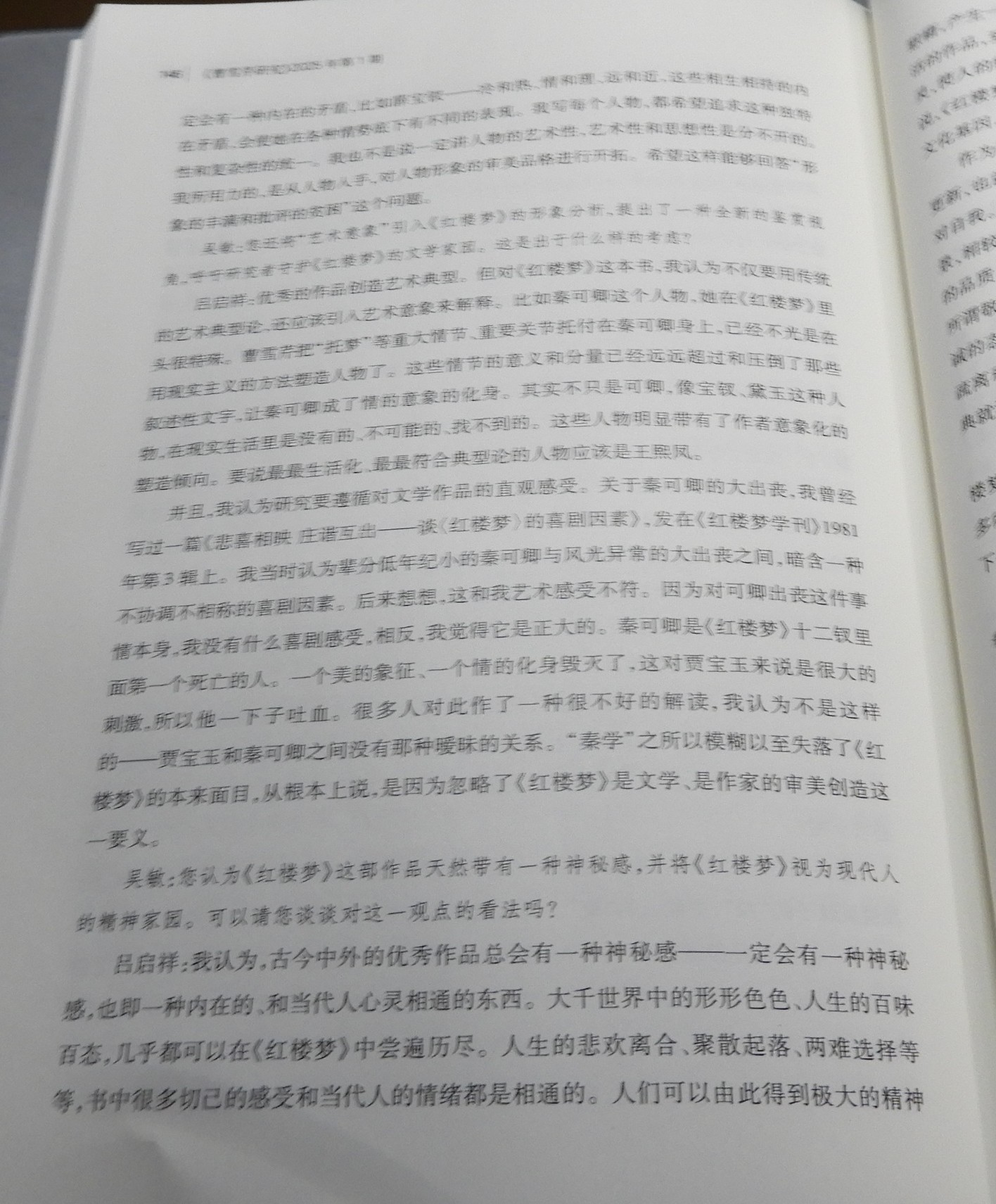
12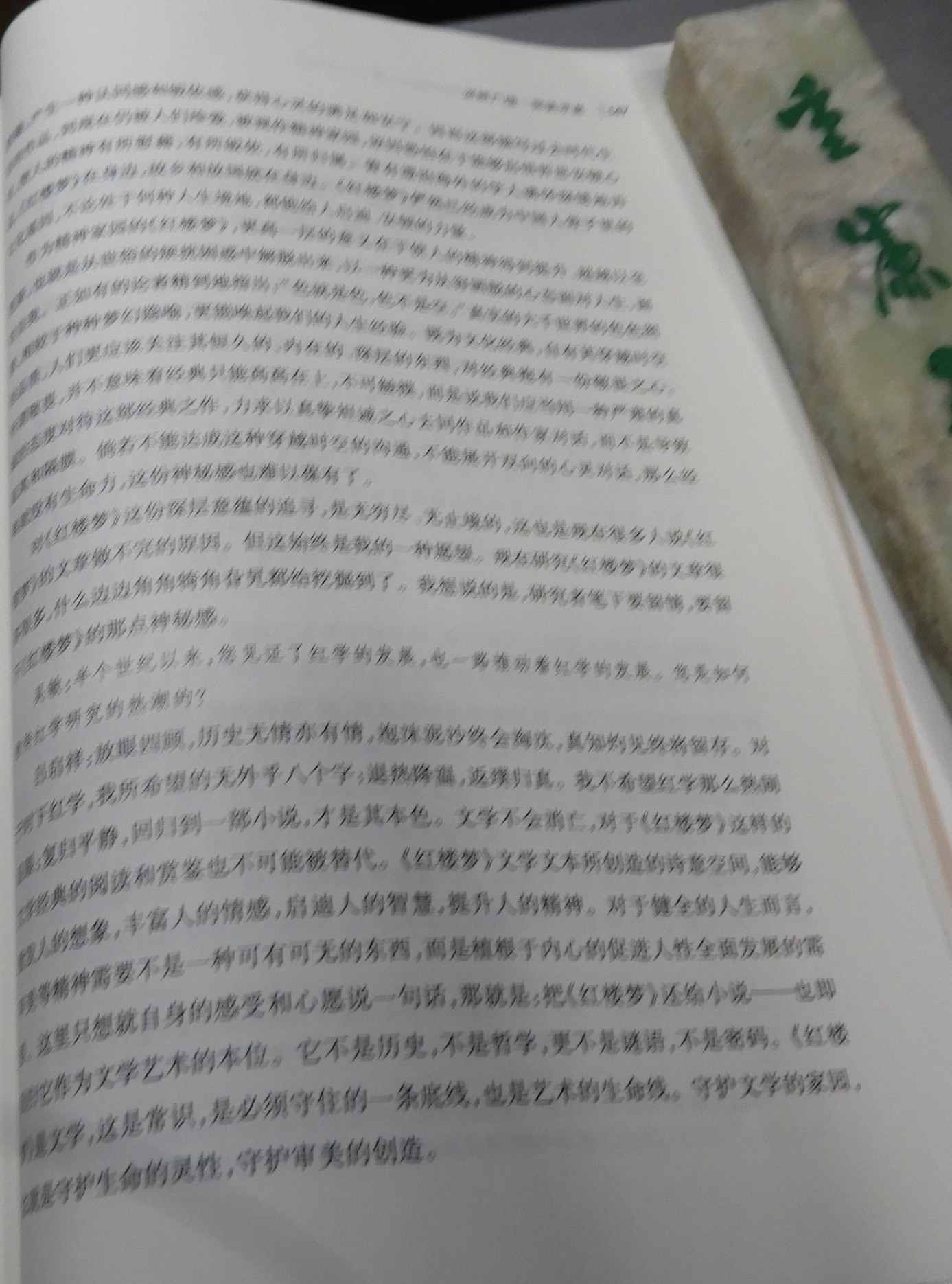
1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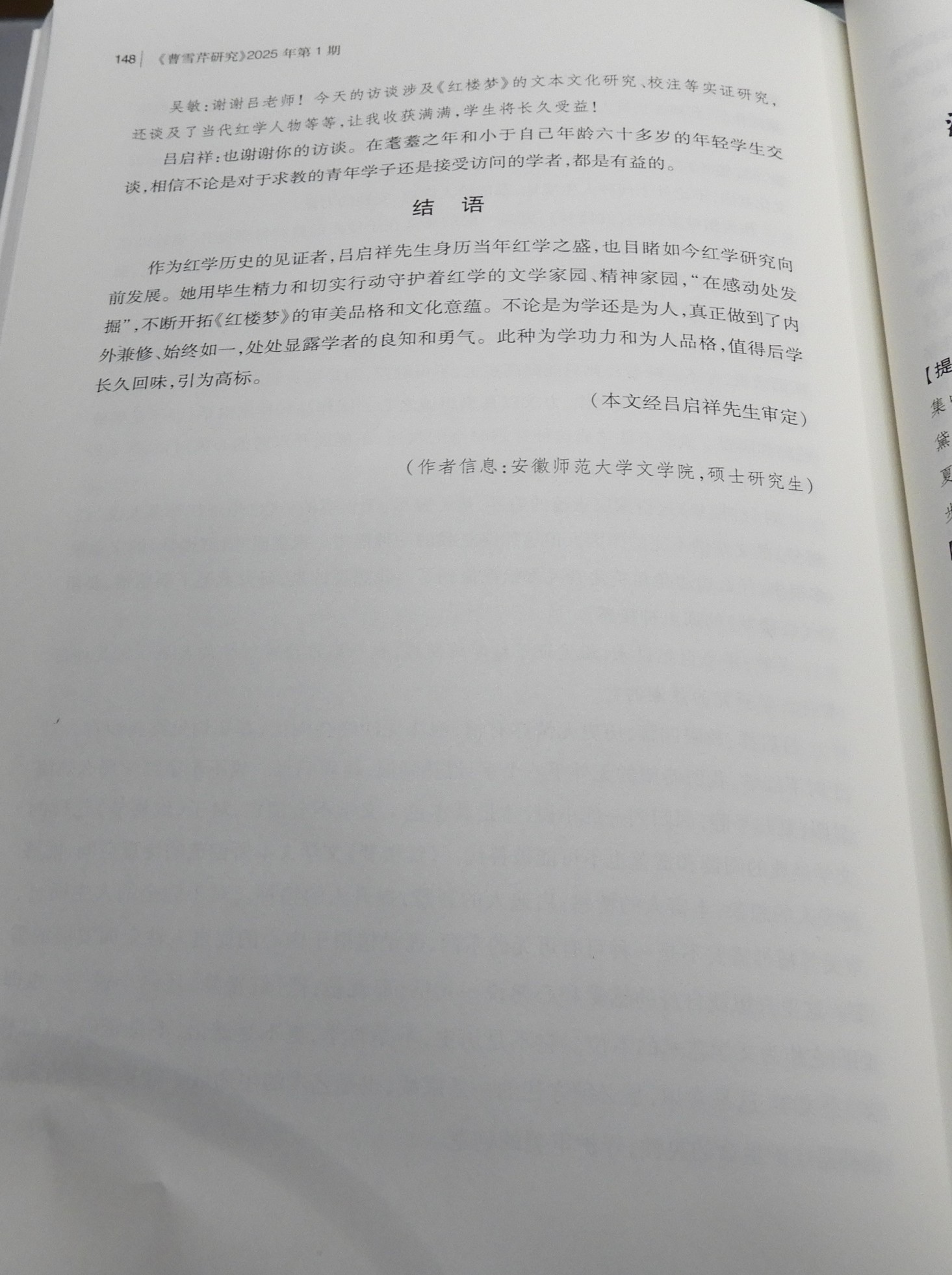
https://wap.sciencenet.cn/blog-415-1491535.html
上一篇:徐源:穷搜博览,务求其真——陈熙中教授访谈录【《曹雪芹研究》2025.2】
下一篇:《曹雪芹研究》2025年第2期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