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选
精选

「哦,你暑假去腾冲啊。那也挺好。其实云南夏天可去的地方可多了。下次来云南,如果是 7、8 月,来我昆明的小房子看看。就一个好处,环境。三面环山,天然的氧吧啊。打开门一看全是绿色,特别舒服。」
「王老师,您从北京到昆明,没坐飞机,开车去的?」
「对呀,开了 3 天呢。」
「您一个人开?」
王老师故意停顿了一下,睁圆眼睛盯着我:「当然了。车上除了我,就你师母,和我们家那条狗 —— 可她俩都不会开啊!」
我正在喝着手里这杯茶,乐得差点儿一口水喷到老爷子身上。
王老师也乐了起来,因为包袱抖响了,得意中。他说 9 月末是学校组织体检的时候,所以他那时候再开车回津。
这时候,一个女生走过来,提醒大家茶歇结束,可以回到各自分论坛了。
王老师谈兴正浓,没有要走的意思。我上半场点评结束,按说也没啥事儿,但是下半场的主题不错,我想听听,就跟王老师告了假。王老师根本不以为意,因为很快就有其他人过来跟他开聊了。
这是 2025 年 7 月 13 日,西安,陕西宾馆,情报学年会。这一年里,我至少第五次见着导师,光西安就两次了。反正 9 月末王老师回天津聚会是一定的,有啥事儿到时再聊呗。哦,对了,我还得准备几张孩子们的近照,因为师母每次都喜欢看。
当时只道是寻常……
9 月 7 日清晨,下电梯的时候,我睡眼惺忪打开微信,才得知王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不信。
明明 8 月末,我还看过王老师在广州会上和同门的合影;甚至 9 月 5 日晚上,王老师还在师门微信群里有说有笑呢……
我希望这只是个噩梦。而噩梦,总会醒来的。
可惜,这次的噩梦,没能醒来。
两天了,我总想为王老师写点儿啥。但是心乱如麻,根本下不了笔。
昨天晚上,我打开多年的日记,看了许久。找到几个片段,在悲痛中记录下来,聊以告慰导师王知津教授的在天之灵。
王老师的学术成就和生平贡献,有口皆碑,我就不必写了。写写我经历的一些小事儿吧。
署名我总觉得,王老师招我做博士,着实是个「亏本买卖」。
我从计算机专业跨考,对人文社科的研究范式和基础理论都不了解。整个儿博士一年级,我都在上课、补硕士课程,一篇论文都没写。而在这期间,我同学发表的 C 刊论文数量,都够毕业 3、4 回了。
我挺着急,但是王老师一直鼓励我:「树义,没事儿,先把基础打好。」
有一天上课,让展示翻译论文练习成果。我讲了半个小时,王老师两眼放光「你这英语不错啊!得给你找点儿活儿干。」
于是,王老师拿来了一本他的书稿,资料大多来源于外文,给我讲解了详细要求,让我修改。我改好后交给他,王老师读完很满意,又拿来了两本。不过给的期限较短,工作量太大我有点儿吃不消,找他要了两个硕士生过来和我一起干,王老师欣然应允。
书稿改完了,我就把这事儿忘了。2009 年 5 月的一天晚上上课,王老师拿来一个大信封,说是我的。
我打开一看,是《放眼看天下》3 本样书。封面上,我的位置居然是副主编!
我愣了,说这哪里合适。王老师说,你是主力嘛,应该的。
当晚,把书稿给爸妈看,给他俩开心坏了。
署学生的名字,王老师特别慷慨。但是轮到署他自己的名字,那就不一样了。
博一第二学期期末,王老师找我聊。说发表论文都有周期,你这一年基础打得差不多了,得抓紧啊。我于是跟他商量,拿他那门课的结课论文细致修改,作为小论文投出去。
获得导师首肯,我就开始改稿。写完以后,署上「王知津、王树义」的作者名称,给他发了过去。王老师很快电话打了回来。提了两个要求:
第一,论文篇幅太长,不符合大部分期刊的规定。拆分一下,控制总字数;
第二,把他的名字删去。他说作为导师,指导学生修改论文是应该的;但他对这篇论文创作没有实质性贡献,不可以署名,否则就是学术操守问题了。
我当时听得似懂非懂,但是只好照办。
每次给学术圈的朋友讲这段儿,他们总一脸坏笑问我「你这篇论文写得太差了吧?」
嗯,那篇论文,后来只调整了些格式和措辞,就发表在了《情报学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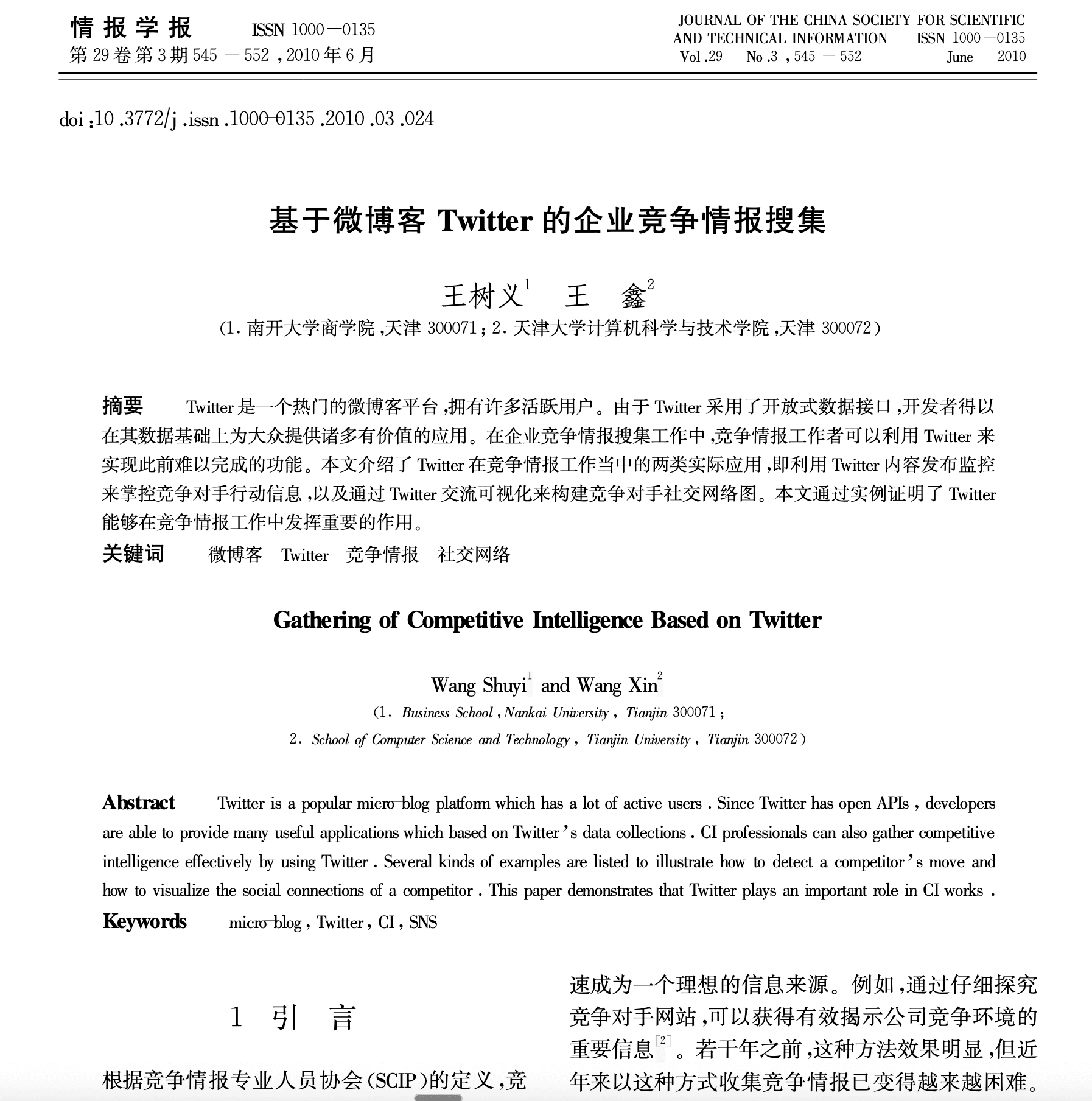
不过我还是不理解,什么样的合作,导师才可以署名呢?
毕业论文工作基本搞定的时候,王老师跟我商量,就着「情报误判心理学」主题合写一篇文章。我说没问题。这次,我才明白合作撰文是啥意思。
我俩就着资料,一起在王老师办公室里商量好整体规划。然后我开始动手,完成初稿后发给他。
发回给我的,是一张「大花脸」。从遣词造句,到标点符号,改得那叫一个精细。连参考文献的格式,都一一校对。
这篇论文 2011 年发表在《图书情报工作》期刊上。说来惭愧,那是我和导师正式署名合写的唯一一篇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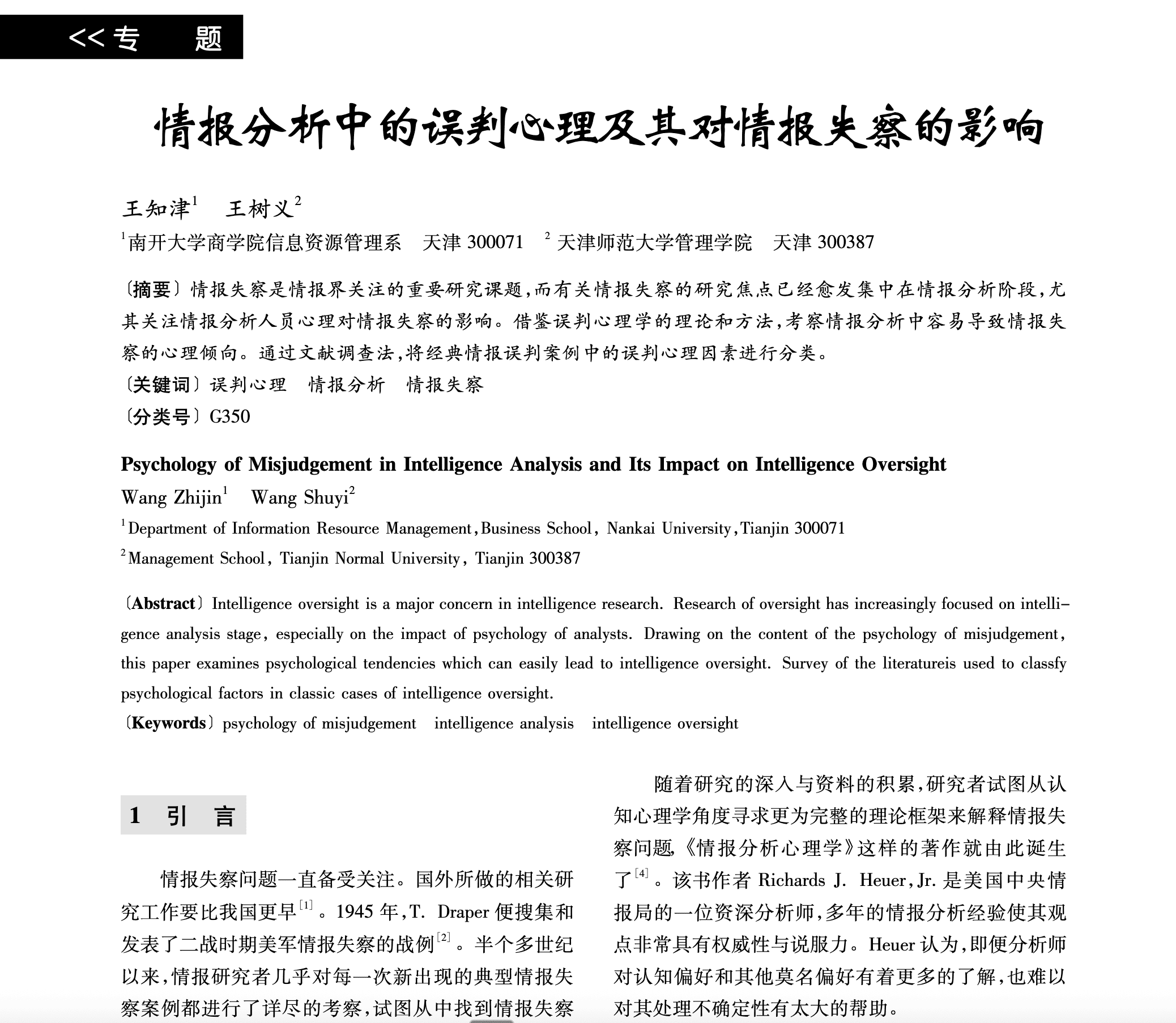
后来我才明白,王老师是希望我能通过这种训练,适应情报学领域的科研范式,以便能在走上工作岗位后继续钻研前进。润物细无声的教导,让我受益颇深。只可惜,我在读博期间驽钝,这样的训练机会太少了。
折腾要说王老师招个学计算机学生的好处,那可能就只剩下「能修电脑」了。
其实,现在这电脑比起兼容机时代,稳定性强很多。一般情况下,出现问题的几率很低。
但王老师的电脑,那真是时常「红色警报」。
因为老爷子太爱折腾了。
他几乎对于所有的新硬件都好奇。包括但不限于新的电脑、手机、打印机、扫描仪、导航仪、随身路由器…… 统统折腾个遍。
王老师不但好奇心重,胆子也大。驱动拿过来就装,各种「安全卫士」给出的建议直接接受……
结果呢?写了一晚上的稿件。一保存退出,崩了。再打开,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所以,我经常往他办公室和家里跑。
其实「学计算机的都会修电脑」绝对是个误解。我修理电脑系统级崩溃的方式,无它。一般就是先做重要数据备份,然后重装系统。几年下来,也算轻车熟路。
王老师用的电脑上安装了一大堆软件,拷贝备份操作很慢。我们俩就一边看着说明书,了解新硬件的正确安装方法,一边等着拷贝和系统重建慢慢完成。
这个过程,每次都至少半小时。也不能光大眼瞪小眼干坐着啊,于是我就跟导师聊天。
这一聊,我才明白一个文科二级教授,为什么对这些科技产品如此感兴趣 —— 如果不是文革,以王老师在哈尔滨的高中成绩,上哈军工或者哈工大是妥妥的。而他本来,就是按照工科生准备学业的。
因而,当他搞研究的时候,特别喜欢把新的技术和机制,引入进来。可要想了解这些新东西,就得有独特的信息渠道,外语更是必不可少。可王老师上中学的时候,东北学的是俄语。他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要学英语。就买了个收音机,把《新概念英语》的磁带复制进去,自己跟着学。愣是靠着这股劲儿,他可以直接查阅英文资料,掌握了许多独特信息,写起文章来才有新意。
移动互联网来了,王老师也快速应用。我们读博的时候,用飞书、QQ 群,后来有了微信,他立刻让我建了个群,往里面拉人。那时候早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有些同门师兄还没有微信。
当着我的面儿,王老师打电话过去:「你对新技术也太不敏感了,落后了啊。赶紧注册一个微信,然后加进群里!」
给王老师修电脑,还有个大麻烦 —— 修好了远远不算结束。
王老师专门准备了个笔记本。每一次修好后,他让我重新演示操作过程,他就用笔原原本本记录在这个小本上。我有时说您不用记,下次有问题我再过来。王老师不同意,说这个问题他自己搞明白,才算满意。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我于是提出我回头做个文档,截图说明操作流程,这样更方便。
王老师摇头「那样印象不深。好脑子不如烂笔头儿」。
而当他记录完成,实际操作后,发现一些顺畅,甚至比原先还要快捷时,总会开心地发出一声感叹 ——「妥了!」
别说是这些小物件儿了,就连开汽车,他也愿意尝试。
你很难想象,一个 62 岁的人,才开始去驾校学开车。但是王老师不管那套,岁数大怎么了,动手能力不比年轻人差。
驾校教练完全同意他的判断,还经常用王老师当作正面典型教训车上的几个年轻学员:「人家老爷子 60 多了,一次掌握动作要领。你们这都多长时间了?懂得害臊吗?」
拿下来驾照,王老师更是不闲着了。还没退休的时候,动静还不是太大。退休之后,特别是 70 岁往后,那可就是「大环线」开起来看了。
唯一阻挡了老爷子旅途进度的,是各种会议的发言邀请等学术活动。所以他的做法是车停下,同行的家人原地等候。他飞过去开会,会后赶紧飞回来继续往前开。
我问王老师,为什么这么喜欢开车?我自己一直觉得开车是个累活儿,能少开就少开。
王老师告诉我,如果不是当年读大学的推荐名额给了他,他早就是专业司机了。那年头儿上山下乡都是力气活儿,像开车这样的技术工种很罕见。他当时已经调到了车队。从洗车开始,一路苦干。眼看第一次有机会让他上车摸方向盘的时候,一纸录取通知,他去武汉报道了。从此他和开车技能失之交臂。
看来,年轻时候的梦想,压抑不住啊。
挂怀现在想想,我们都是被导师宠溺的孩子。
遇到困难时,导师和师母全力以赴伸出援手。师母时常笑着说:「你们现在都毕业了,太好了。还记得吗,那时候毕业论文写不出来,有的女生跑来先抱着我哭半个小时,然后才跟王老师开始讨论该怎么写。」
很多时候,为了不给学生增添压力,王老师不会当面催促,但是老人家自己心里也会很急。师母还经常劝导,说「跟学生说话的时候千万注意语气,别激化」。王老师总是创造一切条件,帮助学生找好选题思路,希望我们大伙儿的学业过程更顺利一些。
从 2009 级起,南开博士毕业的标准愈发严格。王老师也为了学生能在毕业前符合规定发表权威期刊操心不已。还记得关门弟子毕业的时候,师门聚会,王老师那真叫喜上眉梢啊。积攒了好几年的压力,瞬间从肩头卸掉,看得出那是发自心底的轻松和开心。
同门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王老师也总是慷慨解囊。同门回忆读博的时候拮据,有了参加学术会议的宝贵机会,但是在是连会费都交不起。王老师不但用科研经费支持他参加会议,还主动提出帮他垫付开支费用。
不光是学业,家庭、工作遇到的困难,我们也第一时间愿意跟王老师分享,希望导师能帮忙出出主意。王老师总是当成自己的事儿来办,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从来没有半分犹豫。
我们自己的选择,只要不违背原则,导师总会鼓励。我这些年写公众号,不务正业。但王老师每次总夸我的公众号写得很有意义,对读者有实际帮助,还不止一次鼓励我出书。他好几次当面帮我分析技术类书籍的半衰期,说如果不早点儿结集出书,后面技术发生变化,就浪费了。
2023 年,我的两本新书出版后,给王老师寄到了北京。老爷子那叫一个开心,一个劲儿赞叹「好!」还针对书籍封面设计等细节给我提出了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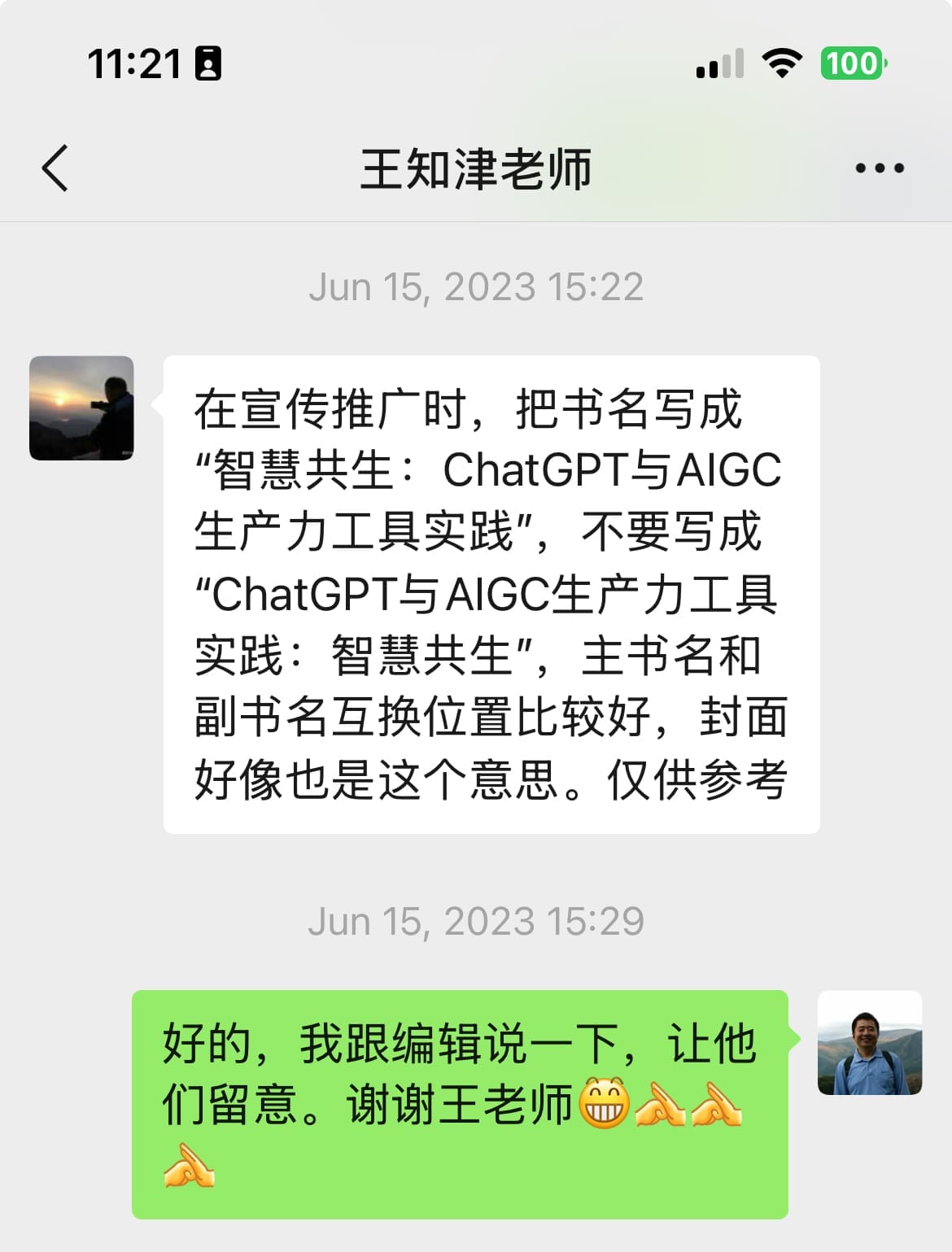
当然了,春天聚会的时候,趁着私下没人的功夫,王老师还是跟我说了句「树义,公众号写得好,科研也得再努把力啊」。
当然,对每一位同门,王老师都是一视同仁地支持。每有同门取得新的成绩,也都第一时间愿意分享给王老师。王老师于是就可以在师门群里广而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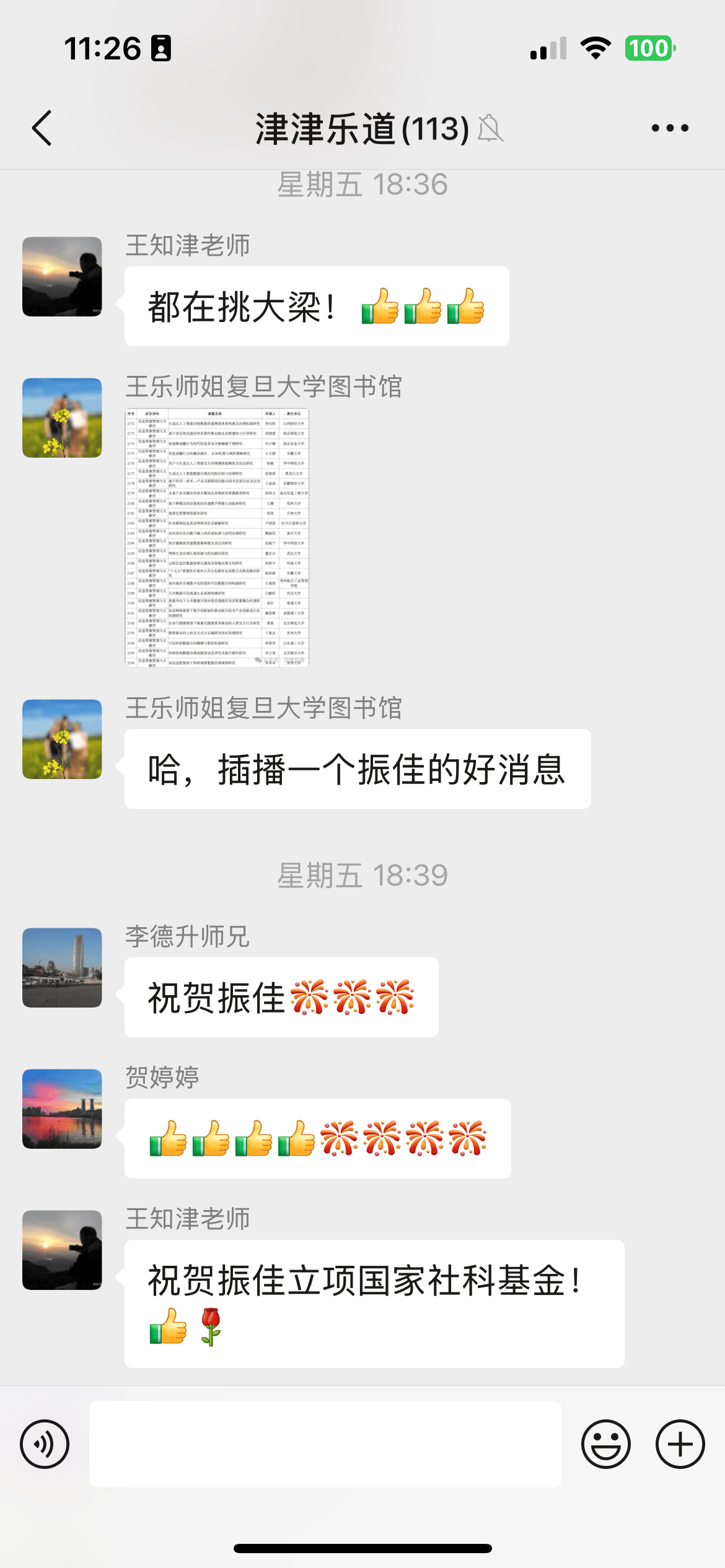
这是王老师留在师门群里的最后一则留言,也依然是在祝贺,祝贺同门樊振佳教授刚刚获批了今年的国家社科立项。
因为在津生活工作,我有更多的机会和王老师、师母、同门们一起聚会。外地的同门每次来津,尽管毕业多年,天南海北分隔,却总是和王老师、师母有说不完的话。这种场面,每次看到,都让人心里暖洋洋的。
伤逝2 天多过去,我的心绪依然是乱的。身体健康、精神矍铄的导师,离开我们太过突然了。有人开导,说老人家一生精彩,活出了人生厚实的宽度。又没有饱受疾病折磨的罪苦,安详地离世,不失为一种功德圆满。
话虽如此,我还是无法承受这种打击。我还想在师门聚会上跟您拉家常,想去您家附近的羊坊去涮肉,想看着您面带骄傲给我展示三面环山的昆明住所……
多次提笔,不知道怎么开始,也更不知道如何收尾。就先停在这里吧。
我追忆的这点儿细节,不到和导师接触获得的十分之一. 王老师是个热爱生活、和蔼可亲又幽默的人。我们经常合起伙来,诱导王老师讲段子,因为是真爱听。只给你把这些段子的精华部分串起来,篇幅大约都是这篇小文的好几倍。
可惜,这样风趣的段子,再也听不到了。
然而,王老师高尚的师德、严谨的治学、开阔的胸襟和对学生的深厚情感,将永远铭刻在我们这些弟子们的心中。如同一座灯塔,指引着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导师王知津教授千古!
学生王树义泣涕而作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王树义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wap.sciencenet.cn/blog-377709-1501119.html?mobile=1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