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选
精选
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被誉为“原子核物理之父”,不仅以划时代的科学发现载入史册,同时也以卓越的导师风范培育出一批顶尖科学家。在20世纪上半叶,卢瑟福从新西兰农场少年成长为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的领军人物。他领导的实验室因产出诸多诺贝尔奖得主而有“诺奖工厂”之称,其严谨又自由的科研文化在科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将从卢瑟福的个人成长历程、导师风格和实验室文化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并探讨若干广为流传的逸事与名言的来龙去脉。

卢瑟福于1871年出生在新西兰南岛尼尔森附近,一个苏格兰移民家庭中排行第四。父亲詹姆斯·卢瑟福是一位来自苏格兰的车轮工匠,母亲玛莎·汤普森是来自英格兰的教师,两人于19世纪中叶先后移居新西兰。卢瑟福自幼接受良好教育,16岁时考入纳尔逊学院就读。1889年他赢得了一项全国大学奖学金,进入新西兰大学所属的坎特伯雷学院学习。1893年卢瑟福以数学和物理双专业一等荣誉成绩取得硕士学位,次年又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在本科和硕士阶段,他已展现出非凡的研究才华。1894年,年仅23岁的卢瑟福凭借出色的学术表现赢得了著名的“1851年科学奖学金”,得以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师从发现电子的物理学家J.J.汤姆孙爵士。
初到剑桥时,卢瑟福面对的是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物理研究环境。卡文迪许实验室设备精良、人才济济,汤姆孙教授很快便赏识了这位来自殖民地的新星。卢瑟福在剑桥期间展现出卓越的实验创造力:他发明了一种用于检测电磁波的接收装置,可在相当远的距离上探测到高频无线信号。他还与汤姆孙合作研究了X射线照射气体后的离子行为、电场中离子迁移率以及光电效应等新奇现象。值得一提的是,1898年卢瑟福通过实验发现天然铀射线由两种不同射程的成分组成,并将其命名为α射线和β射线。这一发现揭示了天然放射线的复杂性,为放射性研究开辟了新方向。
1898年,卢瑟福抓住机遇远赴加拿大,就任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物理学麦克唐纳教授,开始独立领导实验室开展研究。麦吉尔大学的研究条件优越,卢瑟福在此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其中,与年轻化学家弗雷德里克·索迪(Frederick Soddy)合作最为引人注目。两人研究了钍的“放射性氡(emanation)”气体,成功分离出一种新惰性气体——即后来的氡(Radon)同位素,证明放射性元素在蜕变过程中会产生全新的物质。更重要的是,卢瑟福和索迪于1902年前后提出了**“元素蜕变”(衰变)理论**,认为放射性现象是原子层次的变化过程,而非传统化学反应。他们用大量实验证据证实了放射性元素会按照一定序列衰变生成其他元素,并测定了系列中各新元素的性质。这一理论首次揭示了原子的非永恒性,即原子可以自发地演变为另一种原子,这在当时是革命性的见解。凭借关于元素蜕变及放射性化学的这一开创性贡献,卢瑟福于190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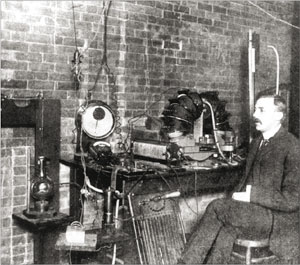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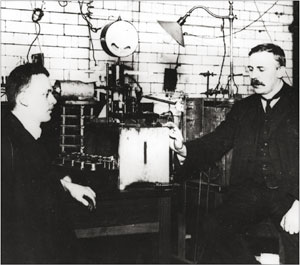
图1:1900年前后,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任教的年轻卢瑟福。在蒙特利尔期间,他完成了对铀、钍等放射性元素的划时代研究,发现放射性元素会发生“蜕变”而生成其他元素(原子核的嬗变)。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为他赢得了19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1907年,卢瑟福受邀回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担任朗沃西物理学教授,接替著名光谱学家阿瑟·舒斯特的职位。在曼彻斯特工作期间,卢瑟福延续了对放射性氡气和α射线性质的研究,并与汉斯·盖革(Hans Geiger)一起发明了一种计数单个α粒子的方法,被视为盖革计数器的雏形。卢瑟福在曼彻斯特取得的最大成就是提出了原子的核式结构模型:1910年前后,他指导学生盖革和欧内斯特·马斯登(Ernest Marsden)进行著名的α粒子散射金箔实验。他们发现少数高速α粒子会在薄金箔上发生大角度甚至后弹,这一反常结果令卢瑟福震惊不已。他据此于1911年大胆推论,原子的正电荷和几乎全部质量都高度集中在原子中心的一个微小区域,即原子核。这个原子结构模型彻底改变了汤姆孙“枣糕模型”中原子被视为均匀分布实心球的旧图景。1912年,来自丹麦的青年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加入曼彻斯特的卢瑟福团队,受卢瑟福提出的核式原子观启发,结合马克斯·普朗克的量子理论构建出玻尔原子模型。玻尔模型成功解释了氢原子光谱和原子稳定性等难题,尽管后来经历修改,其基本思路对现代原子物理仍有深远影响。
卢瑟福在曼彻斯特期间还培养和吸引了诸多才俊。亨利·莫兹利(Henry Moseley)在卢瑟福指导下用X射线轰击多种元素,1913年前后发现了原子序数与元素特性的对应关系,确立了以原子序数(核电荷)为基础的元素周期表。1917年至1919年,卢瑟福继续探索原子核的性质,他以天然α粒子轰击氮气,首次实现了人工核反应:氮核被打碎释放出快速质子。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实验将一种元素转变为另一种元素(氮变成氧的同位素),堪称“新炼金术”的诞生。卢瑟福将这种从氮原子核中打出的带正电粒子命名为“氢原子”(即质子),并预言自然界中可能还存在一种未带电的核粒子。这些研究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原子核物理领域的领军地位。
1919年,卢瑟福接任师恩J.J.汤姆孙,成为剑桥大学第4任卡文迪许教授,出掌当时世界上最具声望的物理研究重镇——卡文迪许实验室。此后一直到1937年逝世,卢瑟福都在剑桥领导该实验室,并担任包括皇家研究所自然哲学教授、皇家学会蒙德实验室主任等重要职位,为英国科学政策和科研体系出力甚多。在剑桥执掌帅印期间,卢瑟福依然活跃在科研第一线:他的学生詹姆斯·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于1932年在卢瑟福主持的实验室发现了中子,为原子核结构谱系添上关键一笔;同年约翰·考克罗夫特(John Cockcroft)和欧内斯特·沃尔顿(Ernest Walton)在卢瑟福倡导下建成高能粒子加速器,成功用质子裂变锂核,实现人类首次人工劈裂原子核。卢瑟福作为科学家的成长历程,从偏远殖民地的青少年到一系列重大实验发现的完成人,再到一所顶级实验室的领导者,可谓精彩纷呈。在此过程中,他积累的不仅是科学发现的声誉,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治学理念和育人方法。
导师风格:多样性人才的培养作为一名导师,卢瑟福以其旺盛的精力、敏锐的科学直觉和开放的胸襟,营造出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他尤其善于吸引不同学科背景和性格特质的青年才俊,使其各展所长。卢瑟福门下汇聚了当时世界各地的顶尖年轻科学家,例如:
保罗·狄拉克(Paul Dirac) – 英国剑桥出身的理论物理奇才,因沉默寡言著称。虽然狄拉克的研究以数学理论为主,但卢瑟福并未将他拒之门外。狄拉克常年在卢瑟福主导的剑桥物理圈中工作,并受到了实验室自由学术环境的滋养。卢瑟福甚至在私人层面给予这位年轻同行指导(例如劝说他接受诺贝尔奖的故事,详见后文),体现出对理论人才的关怀和支持。
詹姆斯·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 – 英国物理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剑桥师从卢瑟福完成博士学位。查德威克一直追随卢瑟福从曼彻斯特到剑桥,担任其副手,并最终在1932年发现中子(获得193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卢瑟福对查德威克寄予厚望,在整个20年代鼓励他寻找“中子”这一当时假想的粒子,并提供必要的实验支持。查德威克的成功证明了卢瑟福识才善任、长期栽培的眼光。
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 – 丹麦物理学家,量子理论先驱。玻尔于1912年来到卢瑟福在曼彻斯特的实验室开展研究,与卢瑟福共同探讨原子结构模型。卢瑟福作为实验家,乐于听取这位理论家的新思路,并提供实验结果供其验证。玻尔后来回忆道,卢瑟福待人真诚直率、精力充沛,讨论问题直截了当,对真理有一股执着的热情,这种作风深深影响了他的发展。玻尔的原子模型在卢瑟福实验发现的基础上取得成功,也让他于192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彼得·卡皮察(Peter Kapitza) – 来自苏联的实验物理新秀,主攻低温物理和强磁场研究。1921年起,卡皮察随导师亚伯拉罕·约费经费赴西欧访问,慕名来到剑桥希望投入卢瑟福门下。在初次谋面时,卢瑟福以实验室人满为由一度婉拒,但卡皮察机敏地反问:“您的实验结果允许2-3%的误差,多我一人也只是在误差范围内。”据传这一幽默回答打动了卢瑟福,他随即同意接收卡皮察。此后卡皮察在剑桥与卢瑟福共事达十二年之久,建立了深厚情谊。卢瑟福赏识卡皮察的独立见解和实验才能,支持他创建高磁场实验设备(大型强磁场发电机),开展液氦物性等前沿课题研究。卡皮察后来回忆说,卢瑟福起初作风严厉、一丝不苟,但熟悉之后两人亦师亦友,卢瑟福甚至允许卡皮察戏称自己为“鳄鱼”(源于初见时年轻学生对卢瑟福有畏惧之感的玩笑绰号)。正是在这种亦庄亦谐的气氛中,卡皮察成长为低温物理领域的领军人物(197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以上案例显示,卢瑟福的导师风格并非限定弟子按某一路径发展,而是善于因材施教,包容多样性人才。从沉默寡言的理论天才狄拉克,到活跃外向的实验能手卡皮察;从本土学生查德威克,到远道而来的国际访问学者玻尔,卢瑟福都能够将他们纳入自己的科研版图。这种开放的胸襟在当时并不多见。例如,卢瑟福自己作为新西兰人初到剑桥时也曾面临保守势力的轻视,但导师汤姆孙的信任与鼓励令他脱颖而出。或许正因亲历此事,卢瑟福更加懂得给予年轻人机会的重要性。他会亲自参加实验室的茶歇讨论,与不同背景的学生交流想法;他鼓励大胆假设,允许失败,强调从实验中学习。在卢瑟福眼中,只要是真才实学,不论来自何方、个性如何,都值得在他的实验室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尊重多样性的文化为卡文迪许实验室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也奠定了其后续辉煌的基础。
“诺奖工厂”的实验室文化卢瑟福执掌下的卡文迪许实验室以其卓越的科研产出和人才培养,被后世誉为名副其实的“诺奖工厂”。这一时期,该实验室孕育出一大批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形成了群星璀璨的局面。据统计,卢瑟福任主任期间,在卡文迪许工作或受训的科研人员中至少有8人后来荣获诺贝尔奖。例如,詹姆斯·查德威克因发现中子获193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帕特里克·布莱克特(Patrick Blackett)因宇宙射线研究获194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约翰·科克罗夫特和欧内斯特·沃尔顿因实现原子核人工劈裂共享195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些人都是直接在卢瑟福指导下取得突破的研究者。此外,G.P.汤姆孙(George Paget Thomson,193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爱德华·阿普尔顿(Edward Appleton,194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C.F.鲍威尔(Cecil Frank Powell,195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弗朗西斯·阿斯顿(Francis W. Aston,1922年诺贝尔化学奖)等知名科学家也都曾在卢瑟福领导下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或访学。
如此惊人的诺奖“产出率”,固然有时代和环境的因素,但与卢瑟福独特的实验室管理和培养机制密不可分。首先,卢瑟福倡导选题自由和探索精神。他鼓励研究人员自主选择富有挑战性的课题,哪怕这些课题在当时看来非常超前。例如,他支持年轻的考克罗夫特和沃尔顿尝试当时尚属冷门的高能粒子加速实验;支持莫兹利开展元素X射线谱研究,从未因研究方向冷僻而加以阻挠。卢瑟福本人会给出宏观指导,但很少微观干预学生具体的实验步骤。这种自由探索的空间使得科研人员能够充分发挥创造力,同时培养了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次,卢瑟福营造了平等交流、头脑风暴的实验室文化。他坚持每日工作之余,全组在实验室茶室聚会讨论(有名的“茶与小圆面包”时间),在轻松氛围中各层级成员畅所欲言。当时在剑桥的许多记述都提到,下午茶时间卢瑟福、查德威克、狄拉克、玻尔、卡皮察等人济济一堂,讨论从最新实验结果到理论设想的各种话题。这种非正式讨论不仅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也激发了学科交叉的新点子。例如,玻尔正是在与卢瑟福和实验同事反复讨论后,完善了关于原子结构的量子化思路;查德威克也常从与理论组同事的交谈中获得思路来解释奇异的实验现象。
再次,卢瑟福以其激情和榜样作用激励着团队。他每日早早来到实验室,对每项研究进展都保持关注,并乐于为任何难题提供建议。正如合作者C.D.埃利斯(C.D. Ellis)所评价的:“卡文迪许的大多数实验项目,其实直接或间接都源自卢瑟福的提议”。卢瑟福善于提出关键性的想法或改进建议,但又给予学生足够空间去实践。他对实验结果要求严格,但对实验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则表现出耐心和理解。这种既高标准又有宽容度的环境,让年轻研究者既有压力动力去攀登高峰,又无后顾之忧地尝试新方法。
最后,实验室内部形成了健康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风气。在卢瑟福手下,多个小组可能同时攻关相关课题,他鼓励良性竞争以加快进展,但同时倡导开放分享数据和经验。一位同事回忆道:“卢瑟福总是希望我们彼此竞争又彼此启发。”这种模式下,谁取得成果大家都会诚心祝贺,而遇到问题别的同事也会热心提供帮助。在他的引领下,卡文迪许实验室成为当时物理科研的圣地之一,吸引了世界各地学者来访交流,进一步活跃了学术思想的碰撞。
总而言之,卢瑟福将一流人才凝聚在一流平台,并通过自由探索、平等交流、以身作则和团队合作等机制,将卡文迪许实验室打造出空前的生产力。其“诺奖工厂”的盛名,并非偶然的神话,而是源于良好学术生态长期积淀的必然结果。
“所有科学,不是物理学,就是集邮”的语境与解读卢瑟福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All science is either physics or stamp collecting.”(“所有科学,不是物理学,就是集邮。”)。这句话常被解读为物理学在所有科学中居于基础和核心地位,其他学科若不从属于物理学的范畴,就不过是在做收集分类资料的工作。这种表述乍听颇为“物理沙文主义”,在生物学、地质学等领域学者中引起过一些反感。然而,深入考察语境和出处可发现,这句话的流传有一定戏谑和断章取义的成分。
首先,从出处来看,尚未找到卢瑟福本人在正式出版物中写下这句话的记录。它最早的出处之一是1939年英国科学家J·D·伯纳尔(John Desmond Bernal)的文章,他将这观点归于卢瑟福。更权威的来源是著名实验物理学家P·M·S·布莱克特(Patrick Blackett)于1954年发表的卢瑟福追思纪念讲演。在那次演讲中,布莱克特回忆卢瑟福曾说过“所有科学要么是物理学,要么就是集邮”这样半开玩笑的话。因此,这句话很可能是卢瑟福在私下或非正式场合幽默的即兴之语,并非写入他学术论文或著作的郑重论断。
其次,从语境和本意看,卢瑟福说这句话的时代背景大约是在20世纪前半叶。当时经典物理学刚刚建立起宏观和微观统一的理论框架,量子力学也初露峥嵘,物理学在自然科学中风头一时无两。卢瑟福作为一位物理学家,自然对本领域充满信心。他的原话更可能是一种诙谐的自我鼓励和同行间的打趣,意在强调物理学强调定量和基本原理的重要性。例如,他在另一场合也曾戏言:“无法用数字衡量的就不算科学”(此语有时也归于开尔文爵士)。可见,在卢瑟福眼中,科学的目的在于找出普适的定量规律,而物理学正是追求基本定律的学科代表。反之,如果一门学科仅停留在现象收集和分类(类似集邮者分类邮票),而未能提炼出定量规律,那它就还不够“成熟”。因此,这句话更多是对科学方法论的诙谐强调,并非真的全盘贬低其他学科。
然而,误读在所难免。后人常将这句话断章取义地理解为卢瑟福瞧不起所有非物理门类的科学,仿佛除了物理其它都是“小儿科”。事实上,卢瑟福本人对化学、地质等领域都有涉猎和尊重。例如,他的很多放射性研究成果发表在化学杂志上,1910年代他还与地质学家合作用放射性定年法估算地球年龄,推翻了旧有地质年代观。卢瑟福当年的调侃在特定圈子里或许引人发笑,但在更广泛语境下并不应被视作严肃的科学评价。现代科学早已证明,包括生物、化学在内的各门学科都有各自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基础原理,“集邮”式的纯粹分类描述只是科学初创时期的一种阶段,而非其他学科的全部。如今引用卢瑟福这句话时,既要了解他所处时代物理学的特殊地位,也需避免将其当作武断的价值判断。
综上,“不是物理就是集邮”更多反映了卢瑟福幽默直率的风格和对科学定量本质的坚持。正确解读这句话,需要还原其历史语境,把握其戏谑成分,而不应简单视为对非物理学科的贬低。
诺贝尔化学奖的趣闻轶事1908年卢瑟福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这对一位以物理学家自居的人而言颇具戏剧性。当诺贝尔奖消息传来时,卢瑟福据说愕然笑道:“我毕生研究了各种不同的嬗变过程,但我遇到过最快的嬗变,就是在一瞬间将我自己从物理学家变成了化学家!”(原文:“I have dealt with many different transformations with various periods of time, but the quickest that I have met was my own transformation in one moment from a physicist to a chemist.”)。这句机智的调侃成为科学史上的名言,充分体现了卢瑟福幽默达观的性格。面对诺奖评委会将奖项归于化学,他并未表现出不满,反而将之比作自身身份的“嬗变”,一语双关地点出了自己研究的主题和奖项属性的转变。
实际上,卢瑟福的研究横跨物理与化学的交汇地带,他的诺奖归属也曾引发当时一些讨论。1908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卢瑟福时的颁奖词中称赞他“对元素蜕变以及放射性物质化学的研究”。卢瑟福本人虽是物理科班出身,但他对放射性现象的研究涉及大量化学分离和分析工作——从提纯氡气到鉴定新元素衰变产物,都属于化学范畴。他早年就认识到放射性衰变“不受温度等外界因素影响,与普通化学变化毫无类比”(也即是一种全新的原子级过程)。因此,诺奖归于化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他开创“原子化学”新领域的认可。
然而,正因卢瑟福日后在原子核物理方面取得更惊人的成就,人们一度猜测他可能再获一次诺贝尔物理奖。例如,他主导发现了原子核、质子和中子这些重大成果。历史上居里夫人曾两度获奖(1903年物理奖、1911年化学奖),卢瑟福是否会成为又一位“双料”诺奖得主?据诺贝尔档案记载,卢瑟福在1920年代确实多次被提名诺贝尔物理学奖。尤其是1922年,瑞典化学家斯韦德贝里等人提名希望先授予卢瑟福物理奖,再给玻尔(因为玻尔模型建立在卢瑟福核模基础上)。但诺贝尔委员会经过讨论,否决了再次授予卢瑟福物理奖的提议,理由是:“如果现在给卢瑟福物理奖,等于承认1908年把奖给他化学奖是错误的”(委员会认为卢瑟福这两方面工作的方法类似,而玻尔的理论贡献更突出)。其后几年虽然也有人提名,但委员会普遍意见是卢瑟福的后续贡献与他已得的化学奖“领域接近”,不宜重复奖励。再加上诺奖惯例倾向于不重复授奖(居里夫人属特例),最终卢瑟福未能像居里夫人那样梅开二度。这段史实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物理、化学两大奖项分类的微妙之处:卢瑟福的研究处于学科交叉地带,以至于评委会在划分他成果归属时也显得左右为难。
卢瑟福本人对此看得颇为达观。从他的打趣话语和后来的态度看,他并不执着于头衔称谓上的物理或化学之别。他甚至将自己的科普著作题名为《新炼金术》(The Newer Alchemy,1937年出版)。这个书名巧妙地呼应了中世纪炼金术士梦想“点石成金”、化学变元素的追求,而卢瑟福以诙谐的口吻自比现代“炼金术士”,暗示自己通过核反应实现了元素嬗变。这表明他乐于跨越学科界限来看待科学问题。在卢瑟福眼里,物理也好、化学也罢,只是探索自然不同侧面的手段,本质目标都是揭示自然界的奥秘。因此,他对自己的研究被归入化学并没有过分介意,反而欣然接受并借机幽默一番。这种科学无国界、也无学科藩篱的胸襟,也是他能广交不同领域好友、培养跨学科弟子的原因之一。
有趣的是,卢瑟福在荣誉面前的达观,也影响了他周围的年轻人。正如下一节将述,他甚至出面规劝一位后辈欣然领受诺奖而莫要过分抗拒。这些轶事更让人感受到大师平易近人的一面。
劝说狄拉克接受诺奖1933年,年仅31岁的保罗·狄拉克(Paul Dirac)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与埃尔温·薛定谔并列),以表彰他在量子力学领域的卓越贡献。然而,这位年轻的理论天才却一度打算拒绝领奖。狄拉克生性极度低调内向,他认为公众的关注和繁琐的领奖仪式对自己而言是种困扰,甚至曾表示接受诺奖会“令他痛苦”。消息传出,在剑桥物理系引起不小的波澜。时任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的卢瑟福认为,狄拉克的顾虑虽然可以理解,但拒绝诺奖将是更大的事件,势必引来更强烈的公众好奇和媒体追逐。于是卢瑟福亲自找狄拉克谈话,语重心长地提醒他说:“拒绝奖项将给你带来更大的公众关注”(“A refusal will get you much more publicity.”)。这一句点醒梦人的劝告切中了狄拉克的担忧要害。狄拉克仔细权衡后,接受了卢瑟福的建议,勉强同意赴瑞典领奖。
卢瑟福与狄拉克的这段互动在剑桥广为流传,成为佳话。它生动体现了卢瑟福作为长者和导师的关怀。他并未以权威身份命令或指责狄拉克,而是站在对方角度指出拒绝反而适得其反的后果,以理服人地化解了这场潜在风波。狄拉克最终出席了颁奖典礼,虽然全程寡言少语,但他毕竟遵从了科研共同体的传统。多年后,狄拉克回忆起当年的决定,坦言要不是卢瑟福点拨,他极可能会因一时执拗而做出有损自身声誉的事。卢瑟福这一举动,不仅维护了诺奖声望,更保护了一位年轻科学家的前程,可谓用心良苦。
值得一提的是,狄拉克并非喜欢追逐荣誉的人。他一生中还曾婉拒过英王授予的爵位头衔(1953年),以免承担社会应酬。然而对于学术荣誉本身,卢瑟福希望晚辈们能够正确对待。他深知诺贝尔奖对一个科学家事业的积极影响,也认为科学共同体赋予的肯定不应轻易拒绝。卢瑟福自己的谦逊平和,在此事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他通过委婉的劝说,引导狄拉克接受荣誉,同时依然保持初心。在这场忘年交流中,我们看到一位老一辈科学家对青年才俊的爱护和期望,也侧面反映出卢瑟福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智慧。这样的软性影响力,是他作为导师的魅力所在。
与苏联科学家的学术往来卢瑟福的影响力跨越国界,在苏联物理学界也留下深刻足迹。20世纪20-30年代,正值苏联科学迅速发展之际,卢瑟福与多位苏联物理学家建立了密切联系,尤其以彼得·卡皮察和列夫·朗道(Lev Landau)这两位日后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为代表。
前文已述,彼得·卡皮察于1921年来到剑桥,在卢瑟福麾下工作长达12年。卡皮察在剑桥期间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强磁场下金属电阻研究(提出卡皮察磁阻效应)、液氦物理性质实验等,为低温物理奠定基础。卢瑟福对此功不可没——他不仅为卡皮察争取经费建立先进实验装置,还在精神上给予支持。当卡皮察取得进展时,卢瑟福总是第一个为他鼓掌;遇到瓶颈时,卢瑟福也会和他并肩分析、寻找解决方案。两人关系亦师亦友,融洽非常。
然而,1934年卡皮察返回苏联探亲时,史料记载苏联当局以“需要留下顶尖人才报效国家”为由,禁止他重返英国。卡皮察突然无法归队,令卢瑟福焦急万分。他多方奔走,联络国际科学界朋友营救。其中卢瑟福联合了尼尔斯·玻尔、保罗·狄拉克等世界知名科学家,一起以私下函电等方式向苏联政府表达关切,希望卡皮察获准回剑桥继续研究。由于政治环境复杂,这些努力并未成功,卡皮察被迫留在苏联(直到1970年代末才获准再次出国)。尽管如此,卢瑟福的奔走体现了他对弟子的赤诚之心。卡皮察留苏后也没有忘记导师的教诲,他在莫斯科建立了仿照卡文迪许模式的物理研究所,并多次在书信和回忆中提到卢瑟福对自己科学人生的塑造。
另一位引人注目的苏联科学家是列夫·朗道(Lev Landau)。朗道是苏联理论物理的奠基人之一。1929年,朗道以政府资助的名义赴西欧各国游学深造。当时年仅21岁的朗道已在量子力学方面崭露头角。他于1930年在哥本哈根与玻尔共同研究,随后于同年下半年赴剑桥,在卢瑟福的实验室逗留了约四个月。朗道虽然是理论物理学家,但他十分仰慕卢瑟福这样的实验大师。据朗道后来描述:“在剑桥的几个月,我每天都能见到卢瑟福充满干劲地穿梭于各实验桌之间,那种对物理的热情深深感染了我。” 卢瑟福也对这位来自苏联的年轻人印象颇佳。他虽听不大懂朗道那些高深的数学公式,却欣赏朗道提出问题的敏锐角度。朗道在剑桥期间主要撰写了一篇关于电子抗磁性的论文,并与卡皮察、乔治·伽莫夫(George Gamow)等同胞一道体验了英国的科研与生活。据说朗道经常穿着一件红色夹克,骑在好友伽莫夫的摩托车后座,载着他满校园飞驰,令古老的剑桥平添了一抹异国情调。卢瑟福看到年轻人朝气蓬勃,也颇为高兴,并幽默地称他们为“俄罗斯空降兵”。朗道从剑桥学到了宝贵的实验直觉和国际化视野,他回国后建立了自己的理论物理学派。在朗道的回忆录中,特地感谢了卢瑟福在他访英期间提供的方便和自由,“使我得以安心思考那些物理问题,而不必为杂事操心”。
除了卡皮察和朗道,卢瑟福与苏联其他科学家也有不少书信往来。例如,他曾与苏联物理学界泰斗、约费研究所所长亚伯拉罕·约费(Abram Ioffe)通信交流实验技术;也接待过苏联访问学者如弗拉基米尔·福克(Vladimir Fock)等人。苏联方面对卢瑟福亦非常尊敬,曾于1920-30年代多次邀请他访问苏联并授予荣誉头衔,但卢瑟福因公务缠身未能成行。尽管如此,他对苏联物理学的发展始终持关注和支持态度。二战前夕,当听闻朗道在苏联遭逮捕(大清洗时期)时,卢瑟福已抱病仍试图通过英国政府渠道交涉,所幸朗道在各方努力下获释。总之,卢瑟福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苏联科学界,在国际学术桥梁的搭建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卢瑟福与卡皮察、朗道的交往,体现了科学超越政治和国界的纽带作用。在那个年代,尽管意识形态和政局壁垒重重,但科学家之间的友谊和共同追求让交流得以发生。卢瑟福从不拘泥于国家出身来评价人才,他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科学共同体的真诚合作。对于苏联的年轻科学家而言,远赴剑桥与卢瑟福共事既是珍贵机遇,也是一生荣耀。对于卢瑟福来说,这些异域弟子的到来为他的实验室带来了新思路和新文化,他本人也从中受益匪浅。在一定意义上,卢瑟福的实验室不仅是诺奖工厂,还是一座早期的“国际物理中心”,孕育了日后全球核物理和低温物理的重要分支。这种跨文化的学术联结,无疑丰富了卢瑟福作为导师和科学领袖的传奇篇章。
结语从偏居南半球的农家子弟到引领原子时代的科学巨擘,欧内斯特·卢瑟福的成长轨迹本身就是20世纪科学史的缩影。他以敢于求真、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攻克了原子结构之谜,在物理和化学的交汇领域留下不朽功勋。同时,他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和循循善诱的风范培养出诸多栋梁之才。从剑桥卡文迪许实验室走出的学生遍布世界各地,他们中的很多人摘得诺贝尔桂冠,将卢瑟福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这种**“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的影响力,甚至超越其本人单项科学发现的意义。
卢瑟福的培养机制给后世科研管理提供了宝贵启示:自由探索与严格求真并行、个人灵感与团队协作并重、尊重个性与追求卓越并举。他创建的学术文化证明了,一个宽松而富有激情的研究环境可以极大激发创新潜能,造就连绵不绝的研究高峰。卢瑟福的名言和趣闻轶事,则展现了大师幽默平易的一面,提醒我们再伟大的科学家也是有血有肉的真人。他既能在学术上雷厉风行,又能在人际上春风化雨,正是这种全面的素养使他成为一代宗师级的人物。
对于今天的科研工作者而言,重温卢瑟福的故事不仅是了解一段历史,更是一种激励:激励我们坚持严谨治学的原则,亦不忘开放交流的初心;勇于开拓未知领域,同时善于提携后进、合作共赢。卢瑟福所秉持的价值观和培养的人才,正是科学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关键所在。这也是他留给科学界最宝贵的遗产之一。正如卢瑟福自己所相信的那样:科学精神没有国界,也没有学科的樊篱,唯有不断探索和共同努力,人类才能步步逼近对自然的终极理解。欧内斯特·卢瑟福的传奇一生,正是对此信念的最佳注脚。
参考文献:
NobelPrize.org – Ernest Rutherford Biographical
NobelPrize.org – Ernest Rutherford Biographical(续)
CERN Courier – Rutherford’s Nobel Prize and the one he didn’t get
Wikiquote – Ernest Rutherford(名言收录)
Medium – Paul Dirac: A Genius Scientist with No Ambition for Fame
Encyclopedia.com – Kapitza, Petr Leonidovich
Rutherford et al., “Radiation from Radioactive Substances”, Cambridge Univ. Press (1919) – (卢瑟福与查德威克等合著) (示例)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王春艳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wap.sciencenet.cn/blog-42659-1486752.html?mobile=1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