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选
精选
培养的人脑细胞能否产生意识?
由人类脑细胞驱动的计算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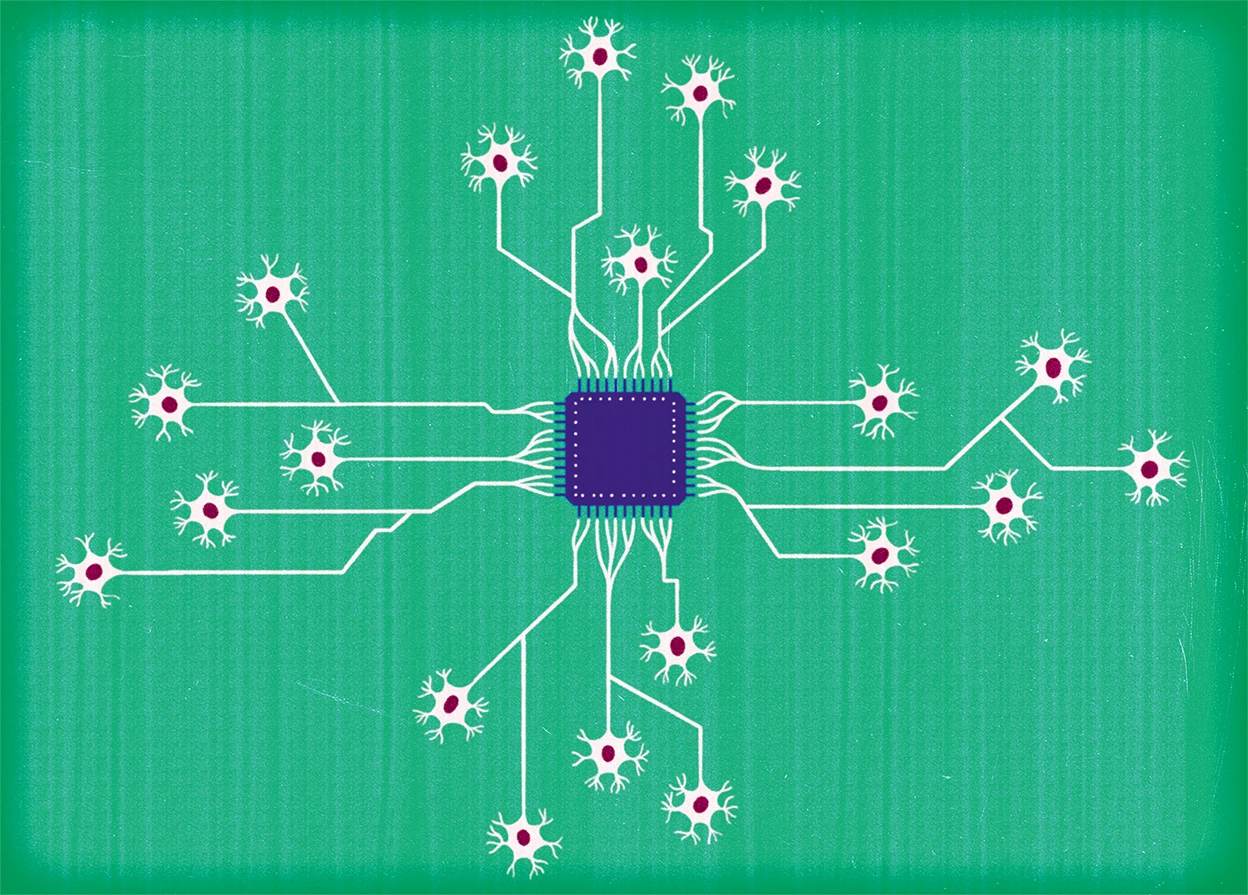
硅芯片退居二线:科学家希望利用神经元制造出能耗极低的高性能计算机。
在日内瓦湖畔的一座小镇上,存放着多团可供租用的活体细胞——人类脑细胞。这些沙粒大小的细胞团能像计算机一样接收电信号并做出响应。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团队可向这些细胞团下达任务,期待它们处理信息后反馈信号。
欢迎来到“湿件”(wetware)或生物计算机的世界。在少数学术实验室和企业中,研究人员正培养人类神经元,试图将其转化为功能等同于“生物晶体管”的系统。他们认为,这些神经元网络终有一天能具备超级计算机的算力,同时避免其过高的能耗。
目前相关成果仍有限,但热切的科学家们已开始在线租用或借用这些脑细胞处理器,部分人甚至斥资数万美元购置专属设备。
有人希望将生物计算机直接替代传统计算机,也有人想借助它研究大脑的工作原理。“理解生物智能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科学问题,”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机器人研究员本杰明·沃德-谢里埃表示,他正在租用瑞士的这些脑细胞团,“从底层入手——先构建简单的小型‘类脑’系统,再逐步扩展——我认为这比自上而下的研究方式更有效。”
生物计算的支持者声称,这类系统未来可能媲美人工智能的能力,甚至具备量子计算机的潜力。
但其他研究人类神经元的学者对其可行性持更谨慎态度。他们警告,过度炒作(以及这类常被贴上“罐中大脑”标签的系统所带有的科幻色彩)甚至可能适得其反。若“这些系统具备感知能力和意识”的说法深入人心,可能会给研究界带来不利影响。
“我担心,如果这类研究获得过多关注且被夸大其词,人们的反应不会是‘我们需要更谨慎地看待这项工作’,而会是‘我们必须彻底叫停它’,”英国剑桥大学发育生物学家玛德琳·兰卡斯特说。她利用神经组织研究发育与疾病,但未参与生物计算项目。“这可能会催生限制所有相关研究的法规,包括那些真正旨在帮助人类的领域。”
降低能耗
长期以来,计算机科学家一直渴望拥有人类大脑惊人的能效。大脑仅需不到20瓦的能耗(约相当于一台小型桌面风扇的功率),其数十亿个神经元每秒就能完成约101⁸次数学运算。最先进的超级计算机虽能达到这一速度,能耗却高出百万倍。
部分研究者正尝试用硅芯片复制大脑的高效结构,这种被广泛称为“神经形态计算”的方法,灵感源自神经元的连接与信号传递方式——具体而言,是模拟神经元需充电至阈值才会释放电脉冲的过程。
而生物计算则回归生物本身的“原材料”:从诱导多能干细胞(iPS细胞,可重编程为几乎任何类型的细胞)入手,研究人员培养脑细胞群落,并用营养物质和生长因子维持其活性。为实现与脑细胞的“沟通”,他们将细胞置于电极阵列上,通过电脉冲序列传递信号和指令。这些信号会改变离子进出神经元的方式,可能促使部分细胞释放被称为“动作电位”的电脉冲。生物计算机的电极可检测这些信号,并通过算法将其转化为可用信息。
最常见的生物计算方法是将神经元培养成3D集群,即“类器官”(organoid)。这些脑细胞群落的组成因iPS细胞的分化方向而异,通常包含神经元及星形胶质细胞、少突胶质细胞等支持细胞。
今年8月,沃德-谢里埃及其团队报告称[1],他们利用约含1万个神经元的人类大脑类器官实现了对盲文字母的“识别”。研究人员首先用配备触觉传感器的机器人读取字母,再将每个字母对应的采集数据转化为独特的电脉冲模式(例如调整脉冲的时间和强度),通过8个贴在类器官表面的电极传递信号。这些电极会记录附近大量神经元的集体活动。
研究团队希望了解:类器官的放电模式是否会因接收的刺激模式不同而变化?这些反应是否具有一致性?
针对每个字母,他们收集每个电极的反应数据并取平均值,得到类器官的整体输出结果,再通过机器学习识别其中的规律。
结果显示,当输入特定字母对应的电脉冲时,单个类器官平均有61%的概率产生相同的特征性反应;若结合3个类器官的反应,这一概率可提升至83%。换句话说,类器官能完成简单的信息处理任务:区分并识别输入信号。
对沃德-谢里埃而言,这是一项坚实的原理验证。“这初步证明我们能完成这类任务,下一步是尝试更复杂的工作”——例如将培养细胞传递的信号解读为对机器人的指令(如“再次读取该字母”)。这种能力被研究者称为“闭环系统”,目前人类大脑类器官尚未实现这一功能,但2024年的一项研究[2]显示,由小鼠神经类器官构成的闭环系统能玩《平衡杆》(*Cartpole*)游戏——该游戏要求玩家控制移动的小车,使车上摇晃的杆子保持直立。
由于培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都是简单的电信号,通过网络远程访问类器官变得容易。因此,尽管读取盲文的机器人位于沃德-谢里埃在布里斯托的实验室,但其使用的类器官是在瑞士沃韦的FinalSpark公司培养和存放的。

图注:在瑞士沃韦的FinalSpark公司,装有人类脑细胞小团块的设备被存放在冰箱中。(图片来源:法布里斯·科夫里尼/法新社 via 盖蒂图片社)
FinalSpark联合创始人弗雷德·乔丹坦言自己是科幻迷,他表示希望开发出能“完成一些如今人工智能所能完成的任务”的生物神经元系统。
但前路漫长。他承认,目前的类器官系统作为计算机,“从实用角度看毫无用处”。“畅想某件事和真正实现它之间有天壤之别,我希望成为推动这一步的人之一。”
包括沃德-谢里埃团队在内的部分学术机构可免费使用FinalSpark的类器官,已有多个团队注册。例如,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团队正测试不同刺激类型对类器官行为的影响,柏林自由大学的研究者则专注于探索机器学习工具如何高效提取神经元放电模式中的信息。
对于资金更充裕的客户(包括私营企业),每月支付5000美元即可获得类器官系统的专属在线访问权,且这类客户不在少数。“一些在特定领域活跃的大公司也参与其中,你可能会觉得它们和这一领域毫无关联,”乔丹说。与学术机构的免费研究不同,FinalSpark并不清楚付费客户如何使用类器官。
其他拥有类器官研究经验的独立团队也纷纷涉足生物计算领域。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阿利松·穆特里实验室培养的神经类器官,每个包含约250万个不同类型的神经元。穆特里计划将类器官应用于实际问题:预测亚马逊雨林中可能发生的石油泄漏路径。该项目由一家石油公司资助,预计2028年完成。“我们接受了这个挑战,”他说,“三年后再看成果如何。”
训练平台
对于许多试图用类器官完成更复杂任务的研究者而言,近期目标之一是找到训练神经元的方法,以促使其产生“目标导向行为”。目前,FinalSpark实验室培养的类器官的反应,更类似于外周神经系统的反射动作(例如敲击膝盖下方时腿部会踢动),而非大脑中指导决策的可塑过程。
要处理更复杂的任务,这些神经系统必须具备学习能力。乔丹表示,一种方法是释放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尝试调节类器官对特定刺激的反应——多巴胺能提高神经元的放电概率,并增强神经元间突触的连接强度,这两种变化都能让神经元对同一刺激的反应更可能在未来重复出现。
另一种方法是“模式训练刺激”技术。2022年,澳大利亚墨尔本的Cortical Labs公司的研究者就用这种技术,让实验室培养的脑细胞学会了玩20世纪70年代的计算机游戏《乓》(*Pong*)[3]。
该团队没有使用类器官,而是在培养皿中构建了细胞网络(见“用细胞计算”),再将其与计算机连接。计算机经过编程后,神经元对刺激的反应会控制虚拟球拍移动,同时虚拟球在屏幕上弹跳。当细胞(最初是随机地)正确控制球拍击中球时,研究者会向神经元输入一组有序的电活动;若神经元将球拍移向错误方向,则会受到混乱的白噪声刺激。久而久之,神经元学会了击中球以获得有序刺激,而非随机噪声。
这种策略源于一个观察结果:脑细胞倾向于重复能产生可预测结果的活动,因此会学习那些能触发熟悉刺激的行为。
如今,Cortical Labs已开发出模块化系统,可连接越来越多的独立培养孔(每个培养孔最多含1000个神经元),形成该公司所谓的“生物工程智能”(bioengineered intelligence)。每个细胞培养物的使用寿命约为6个月,之后需更换。
“我们实际上可以控制细胞的几何结构、拓扑结构、位置、形状及其连接方式,”Cortical Labs首席科学官布雷特·卡根说,“这将催生出完全不同类型的信息处理方式。”他表示,这种方法能让实验结果更具可重复性,从而减少类器官研究中常见的结果变异性。
“这带来了更高的透明度,在我们看来,这将帮助人们更深入地理解相关机制,”他补充道。
该公司已在其系统上开展多项实验:一项测试了抗癫痫药物对神经元放电的影响[4];另一项则表明,这些神经元的学习效率高于现有人工智能系统[5]。目前,Cortical团队正致力于证明其系统能识别手写数字和符号。
与FinalSpark类似,Cortical Labs也提供神经培养物的在线访问服务,但更进一步——该公司还销售号称“全球首款生物计算机”的设备CL1。这款设备售价3.5万美元,将多个相连的神经元培养孔与可编程界面结合,用户可通过界面下达指令并分析电反应。卡根表示,该设备已向全球多个实验室售出并发货,还有更多订单在处理中。
用户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包括基础神经科学原理(如神经可塑性和网络动态)、湿件与人工智能的结合,以及实时控制系统(包括机器人技术)。部分用户甚至尝试用脑细胞开发娱乐应用,包括游戏和卡根所说的“实验性音乐产品”。
“CL1的设计初衷就是消除使用门槛,”他说,这与苹果设备“为大众提供个性化计算”的理念类似。
争议与谨慎
卡根并非首次发表大胆言论。他2022年关于《乓》游戏的论文让大脑类器官领域的许多研究者感到担忧——论文标题用“感知能力”(sentience)描述这个简单的体外系统。30位研究者发表回应[6],认为这类表述“不恰当,且无数据支持”,可能使整个领域面临“不必要的风险”,导致此类研究受到限制。
卡根使用“感知能力”一词,是因为根据他的论文,该词可简单定义为“对感官印象做出反应”。但负面反馈让他重新思考。“今后我不会再用‘有感知能力’这个词,”他上月告诉《自然》,“以我们现在掌握的知识来看,当时应该更谨慎一些。”
兰卡斯特认为,用“感知能力”这类词汇描述细胞培养物,以及相关的“这类培养物是否有意识”的讨论,可能会让那些出于伦理原因反对这类研究的人提出不必要的监管要求。神经类器官更多用于基础神经科学研究,而非生物计算应用,兰卡斯特担心更严格的监管会阻碍她的团队及其他研究者的这类研究。
“一团神经元不是大脑,它不会思考,也无法思考,”她说,“但如果信息是以这种方式传递的,人们就会这样理解。”
她还对生物计算实验的结论提出质疑:“潜力确实存在,但我不认为目前已展示的成果能真正称得上‘计算’。”她指出,去年的一项研究[7]显示,不含任何神经元的非生物水凝胶也能“学会”玩《乓》。她说,在这类表现出简单反馈的系统中,看似“学习”的行为可能只是噪声。
穆特里则更为乐观:“类器官具备人类认知的基础功能,”他说,“这类技术甚至可能与量子计算机竞争,成为下一代低能耗计算技术。”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孙学军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wap.sciencenet.cn/blog-41174-1509943.html?mobile=1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