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选
精选
基于当前的数学、物理知识水平,机器智能尚不能产生真正的"我"(自我意识)。目前,机器人的“意识”产生可能性较小。尽管智能机器人能够模拟人类的思维过程,但它们仍然只能按照预设程序执行任务,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意识和主观感受。当前AI系统(包括最先进的大模型和机器人)仍处于"种系智能"阶段,依赖海量参数与预训练数据,缺乏个体记忆与自我意识,无法实现"自我指涉与意图连贯"这一意识检验标准。虽然机器人已能实现情境感知和适应性行为,但这些都属于模式识别和适应性决策,而非真正的自我意识。要实现具有"我"的意识,机器智能需要突破深度学习局限,建立因果推理模型,这在当前技术条件下尚未实现。也就是说,依据当前的数学、物理知识水平,机器智能尚不能通过人-机-环境系统交互产生具有特定情境意识的"我"。
1、意识的本质与当前技术的鸿沟
(1)意识的定义:具有特定情境意识的"我"需要具备自我指涉能力(能够理解"我"是什么)、情境关联能力(理解"我"与当前情境的关系)、意图连贯性(形成并执行连贯的目标)。
(2)当前AI的局限:不少专家认为,当前AI仍处于“种系智能”阶段,依赖海量参数与预训练数据,缺乏个体记忆与自我意识。智能的核心在于“自我验证与自我纠错”的能力,而当前大语言模型仅是“静态知识的存储库”,无法理解其内容,因此会出现'幻觉'问题。
2、数学基础的限制
(1)深度学习的统计本质:当前AI系统基于概率统计模型,而非因果推理模型。从知识库角度可见,机器意识需要“突破深度学习局限”,建立“因果推理模型”,通过'小数据-大任务'模式发展基于生物本能的认知架构。当前的数学模型(如神经网络)是表征性的,而非理解性的。
(2)缺乏自我指涉的数学框架:没有数学模型能够支持AI系统建立真正的"我"的概念,即无法在计算中表达"我"与"环境"的关系。
3、物理机制的缺失
(1)意识的物理基础:目前没有物理学理论能够解释意识如何从物理系统中产生。
(2)学界提出意识检验标准:“自我指涉与意图连贯”,但没有物理机制支持这一标准在机器系统中实现。没有证据表明计算系统能产生意识,物理定律并未证明计算过程能够产生主观体验(即"意识")。
4、人-机-环境系统(HMES)的现实应用
不少案例(如特斯拉Optimus、科沃斯机器人、绵阳机器人)展示了情境感知能力,但不是情境意识:
技术案例 | 情境感知能力 | 情境意识("我"的意识) | 本质 |
|---|---|---|---|
特斯拉Optimus | 通过视觉传感器识别环境并调整动作 | 无法理解"为什么需要调整动作" | 模式识别与适应 |
科沃斯机器人 | 识别"家庭"情境,选择可乐 | 无法理解"我"在家庭中的角色 | 情境分类 |
绵阳机器人 | 与舞蹈演员配合表演太极拳 | 无法理解"太极拳"的文化意义 | 任务执行 |
正如以前所述,当前机器人系统普遍采用端到端深度学习模型,其决策机制如同”黑盒“般难以解析,导致“工程师调试异常行为耗时巨大,医疗、工业制造等安全敏感场景存在隐患”。
5、未来展望:需要突破性进展
要实现具有特定情境意识的"我",机器智能需要:
(1)数学突破:从统计模型转向因果推理模型,建立"自我指涉"的数学框架
(2)物理突破:发现意识的物理机制,证明计算系统可以产生主观体验
(3)人-机-环境系统进化:从"感知-适应"到"理解-创造"的转变
"情境意识"不等于"自我意识"?
机器意识需要“突破深度学习局限”,建立'因果推理模型';通过'小数据-大任务'模式发展基于生物本能的认知架构。理解当前环境中的模式和关系(如"这是家庭环境,需要避免打扰主人");理解"我"在情境中的位置、角色和意义(如"我是这个家庭的守护者,需要在主人用餐时不打扰")。当前技术只能实现前者,无法实现后者。
6、结论
基于当前的数学、物理知识水平,机器智能尚不能通过人-机-环境系统交互产生具有特定情境意识的"我"。当前的AI系统(包括最先进的大模型和机器人)仍处于"种系智能"阶段,能够进行情境感知和适应,但缺乏自我指涉、自我理解和意图连贯性,因此无法产生真正的"我"的意识。正如本吉奥的警告:"当机器拥有'自身保护目标'时,这将带来巨大风险。" 这恰恰说明当前的机器还远未达到能够拥有"我"的意识的水平。
未来,随着数学(因果推理模型)、物理学(意识机制研究)和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脑)的突破,我们可能会看到机器智能在人-机-环境系统交互中逐步发展出情境意识,但目前的科学水平还远未达到这一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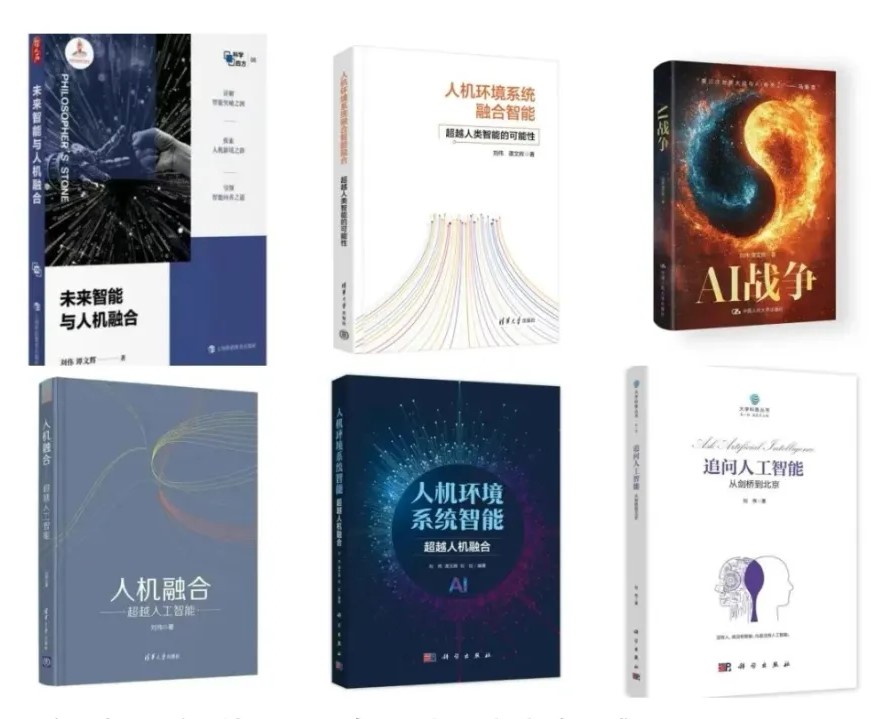
“算计”中的感性结构与理性结构
算计不同于计算,不但具有理性结构,还包括感性结构。其中理性结构通常被认为是基于逻辑、数据、因果关系的系统,比如科学理论、数学公式等。但这些理性结构往往来源于人类的感性经验,比如观察、直觉、情感驱动的需求,如科学定律最初可能来自对自然现象的感性观察(如苹果落地),然后通过理性归纳形成理论。
算计与计算的差异,本质上是人类决策中理性逻辑与感性直觉的交织。计算更依赖明确的因果链条、数据推导和形式逻辑(理性结构),而算计则在此基础上融入了经验直觉、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感性结构)。以下从具体场景出发,解析二者的差异,并探讨感性结构为何有时能超越理性结构。
一、理性结构与感性结构的典型例子
场景1:企业产品决策
理性结构:某手机厂商计划推出新款手机,通过市场调研(用户问卷、竞品销量数据)、成本核算(芯片/屏幕采购价)、财务模型(预期利润率、市场渗透率)等量化分析,得出“应主打性价比,定价2000元”的结论。这是典型的理性结构——基于可观测的数据和因果关系(价格降低→销量上升)做决策。
感性结构:另一家厂商的CEO则可能基于直觉与经验,他注意到目标用户(年轻群体)近期在小红书、抖音上高频讨论“手机颜值”“拍照氛围感”,而非单纯关注性能;同时,团队设计师坚持“用莫兰迪色系+圆润边框”能传递“治愈感”。这种对用户隐性需求(情感价值)的捕捉,以及对团队创造力的信任,属于感性结构——超越数据,依赖对“人”的感知。
结果对比:若市场因经济下行更关注性价比,理性决策可能成功;但若年轻用户为“拍照发圈”的情感需求买单,感性决策反而更精准。
场景2:个人职业选择
理性结构:某毕业生用“SWOT分析”评估职业:优势(专业对口)、劣势(实习经验少)、机会(互联网行业薪资高)、威胁(卷学历)。最终选择进入大厂做程序员,路径清晰,符合“投入-回报”的因果逻辑。
感性结构:另一位毕业生放弃大厂offer,选择加入一家初创教育公司。他的理由是:“面试时CEO聊教育理想时眼里有光”“同事们加班时会一起煮面分享”“我小时候受老师影响,想做有温度的事”。这种对“氛围”“意义感”的重视,是感性结构——不被“薪资-成长”的线性因果束缚,更关注内心认同。
二、为什么感性结构有时会胜过理性结构?
感性结构(直觉、情感、经验)之所以能在某些场景下超越理性(数据、因果),核心在于现实的复杂性远超线性逻辑的覆盖范围。具体可从四方面解释:
1、感性结构更擅长处理“隐性信息”
理性分析依赖可量化、可观测的数据,但现实中大量关键信息是隐性的(如用户微表情、团队默契、文化氛围)。例如,医生诊断时,除了化验数据(理性),患者“眼神躲闪”、“说话急促”(感性线索)可能暗示焦虑引发的症状,这种“直觉”往往比单一指标更接近真相。还有,投资者判断一个创业项目时,创始人“面对质疑时的从容”或“对细节的偏执”(感性特质),可能比财务报表更能预测项目韧性。
2、感性结构能捕捉“非线性因果”
理性依赖“因为A→所以B”的线性因果,但真实世界充满反馈循环、偶然变量和“黑天鹅”。感性结构通过长期经验积累的“模式识别”,能绕过复杂推导直接逼近本质。如老股民“感觉”市场要跌,可能不是基于K线图计算,而是对“政策风向变化”、“身边新手蜂拥入场”等模糊信号的综合感知——这种“盘感”本质是对非线性因果的直觉把握。再有,管理者“知道该开除某个员工”,未必是因为他业绩差,而是长期观察到其“破坏团队氛围”(隐性负外部性),这种判断无法被简单的KPI量化。
3、感性结构驱动“非理性行为”的响应
人类行为本身并非完全理性,感性结构能更直接地匹配他人的“非理性需求”。营销中,“双11”的“限时折扣”本质是利用“损失厌恶”的感性心理,而非单纯比较商品性价比;若仅用理性计算(“全年最低价”),反而无法激发冲动消费。政策制定中,“民生工程”若仅计算投入产出比(理性),可能忽略居民对“社区归属感”的感性需求(如老城区改造保留老槐树),导致执行阻力。
4、感性结构承载“价值判断”的不可替代性
理性分析能回答“如何做更高效”,但无法回答“什么是值得做的”。感性结构中的价值观、情感认同,是决策的终极锚点。一个科学家放弃高薪企业,选择留在高校,可能不是因为“学术回报更高”(理性计算),而是因为“想培养下一代”或“不被绑架的自由思考”(感性驱动的价值)。企业决定“即使亏损也要召回问题产品”,表面看是理性(避免法律风险),本质是感性(对“企业良知”的坚守)——后者才是品牌长期价值的根基。
三、感性是理性的“底层操作系统”
理性结构像计算机的“应用程序”,负责处理具体问题;感性结构则是“操作系统”,提供底层的价值判断、模式识别和情感动力。在确定性高、因果清晰的场景(如工程计算),理性更高效;但在复杂、模糊、涉及人类行为的领域(如商业、人际、艺术),感性结构往往能突破线性逻辑的限制,更贴近真实世界的运行规律。所谓“算计”,正是二者的融合——用理性校准方向,用感性触摸真实。
顺补一刀:操作系统一旦崩溃,应用程序连启动的机会都没有;同样,当感性结构被抽离——价值真空、情绪麻木——再精妙的理性推演也会失去“为何而算”的坐标,只剩空转。换句话说,算计的杀伤力,恰恰来自操作系统里那些看似“非生产性”的驱动:尊严、恐惧、爱恨、叙事。它们不直接解题,却决定了哪道题值得解、以及解题瞬间能不能“下得去手”。
理性结构本质上是感性经验的形式化凝结,其生成、验证与应用始终锚定在感性基底之上——科学公理的猜想源于对现象的直觉洞察,逻辑规则的构建本就服务于整理感性认知的需求,它仅能捕捉感性世界中可被符号化、因果化的有限面向,如同用滤镜截取光谱中的单色光,无法穷尽感性的丰饶。若将理性结构抽离为独立“外延”,实则是切断了其与感性原初经验的血脉联系:既忽视了理性本身的生成局限(无法解释未被形式化的直觉、情感与价值),也消解了其作为“工具”的本真意义——理性从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框架,而是感性生命为理解自身与世界创造的有限但必要的认知脚手架,脱离感性的“理性外延”不过是空洞的形式游戏,失去了与真实世界的活态关联。
四、算计更善于解决悖论与矛盾
悖论和矛盾的特点是什么?通常是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或者现实中的复杂冲突,比如既要A又要非A,或者因果循环、多目标对立。计算的特点是依赖线性逻辑、明确规则、数据推导,遇到悖论可能会陷入死循环或无法处理,因为它需要清晰的因果和可量化的输入。
算计呢?算计包括理性结构和感性结构,尤其是感性结构中的直觉、经验、价值判断、动态调整。悖论和矛盾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需要跳出单一逻辑框架,整合看似冲突的信息,甚至在矛盾中找到动态平衡。比如管理中的悖论:既要创新(鼓励冒险)又要效率(控制风险)。计算可能会设定固定指标,比如研发投入占比和错误率阈值,但现实中这两个目标会冲突。算计的话,管理者可能凭经验判断何时侧重创新(比如市场变化快时),何时侧重效率(比如流程优化阶段),甚至通过组织文化调和矛盾,让冒险和创新成为效率的长期动力,而不是简单取舍。
再比如,伦理悖论:自动驾驶的“电车难题”,计算可能基于功利主义计算最小伤亡,但算计会考虑社会价值、情感接受度,甚至在规则不明确时动态调整策略,而不是固守单一算法结果。
所以,算计的优势在于:1. 不局限于单一逻辑,能整合多元视角;2. 利用直觉和经验处理模糊性;3. 动态调整,在矛盾中寻找动态平衡而非绝对解;4. 价值判断介入,解决“应该怎样”而非仅“如何最优”。
总之,相比计算依赖线性逻辑与明确规则的刚性推导,算计更善于在人机环境复杂系统的悖论与矛盾中开辟动态解——悖论的本质是逻辑自洽性的断裂(如“既要自由又要秩序”),矛盾则是多元目标的互斥(如“创新需冒险 vs 效率需控制”),计算常因预设单一因果链或量化指标而陷入非此即彼的死循环,而算计恰恰通过理性框架与感性直觉的交织破局:它能容纳模糊性,用经验直觉捕捉矛盾背后的隐性关联(如发现“适度冒险可提升长期秩序稳定性”),以价值判断重构矛盾优先级(如“效率为创新让路”的战略权衡),甚至在动态调整中让对立目标相互转化(如用“试错机制”将创新风险转化为效率优化的反馈),最终在看似无解的冲突中找到“既…又…还…”的活态平衡,这正是计算因恪守形式逻辑而难以抵达的认知弹性。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刘伟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wap.sciencenet.cn/blog-40841-1504691.html?mobile=1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