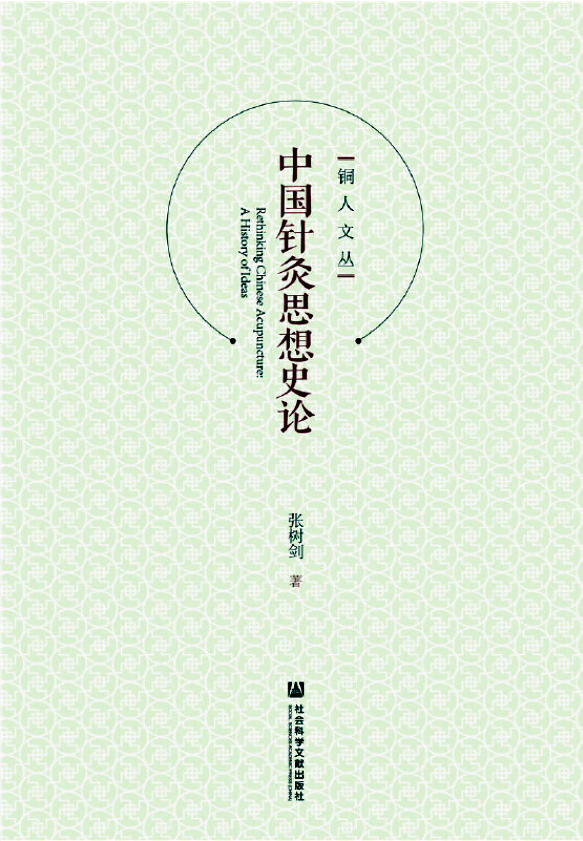

山东中医药大学张树剑教授312千字的著作《中国针灸思想史论》,于2020年6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著作首次以学术史的视野阐述针灸知识和理论的缘起及其历史演进,具有开拓性贡献。
内容简介
作者以其精致的文字、对针灸乃至中医理论独到的“历史情景化”理解,向我们展示了针灸知识和理论的缘起及其历史演进,不仅以历史主义的态度,从针灸的相关概念、理论辨析入手,将针灸乃至中医思想理论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对其做了合乎情理的理解和阐释,而且通过具体的专题研究,让读者意识到,宋元以来理论化的针灸并非中国传统针灸的全部,中医在不同时代思潮影响下不断阐释而日臻精致复杂的理论,与具体的临床实践存在着相当的差距和紧张。
作者简介
张树剑,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针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副院长、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访学,冶学务实证,反虚玄,推陈出新,视角贴近临床,思想兼容并蓄,被网友誉为当代务实派中医的杰出代表、中医界第一个突破格律的诗人。
多年来致力于中医与针灸临床,诊疗技术全面,针灸、针刀与方药兼擅,擅长针灸、针刀与中医药结合治疗多系统疑难病,尤其对颈、腰椎病、脊柱相关性内科疑难病、各类痛症有独到之处,曾应邀赴欧洲教学与临床,并多次应邀在东南大学、江苏电视台、南京新中医学研究院等机构开展中医学术或科普讲座,作为医学专栏作家在《现代家庭》《年轻妈妈之友》发表中医科普文章数十篇。
学术兴趣主要在中医针灸思想史、学术史、中医人文与传统文化、中医临床研究等,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专著数十种(篇)。
著作目录
作者简介 2
序 4
绪论:从概念到理论到学术史 10
上编 概念与理论流变 18
第一章 论经脉 20
第一节 经脉形态:观察与想象 20
第二节 奇经名实考 28
第三节 经脉数量:因天而数 53
第二章 论身形 60
第一节 经筋 60
第二节 四海 62
第三节 骨节 65
第三章 论腧穴 73
第一节 腧穴形态:基于体表解剖与触诊 73
第二节 三百六十五穴:概念背后的腧穴观 81
第三节 八风:从自然现象到腧穴 86
第四节 取穴法 92
第五节 根结标本:腧穴效应的借喻 100
第六节 常用类穴解读 103
第四章 论刺法 131
第一节 镵针之由来与早期经脉思想 131
第二节 “损益”思想与针刺补泻 137
第三节 守神、本神、治神 144
第四节 从律管候气到针刺候气 152
第五节 治乱—导气 161
第六节 驱邪—守机 169
第五章 针灸理论与概念的观念再识与解析 177
第一节 针灸理论概念的基本观念再识 177
第二节 构建针灸理论的观念基点——法天 194
下编 学术专题讨论 196
第一章 针灸的传统:历史与比较的视角 198
第二章 “子午流注”针法思想与宋元针灸理论之固化 205
第三章 中药归经:容易迷失的导游 216
第四章 宋代解剖图及其立场 223
第五章 新旧之辩——20世纪50年代朱琏“新针灸学”的浮沉 238
第六章 针刺消毒史:近代以来的曲折遭遇与社会反应 252
第七章 对针灸“辨证论治”的讨论 270
第八章 由“干针”的“入侵”与“独立”谈针灸概念、理论内涵之变革 281
第九章 现代针灸临床新学派背景与前景透视 297
征引文献 305
后记:江河不废之东方学术 324
论文选读:从文献到学术史——针灸理论研究的立场与路径
摘要:针灸学术传承有明暗两条线索,包括理论性传承与经验性传承,发展至今,主流针灸理论与经验性临床的关系渐渐相乖,对新的临床技法更是无力解释。既有的针灸理论需要严格地重新检视,新的学术成果宜应审慎地纳入。文献整理、概念考证与学术史考查则是针灸理论研究的关键路径。
对任何一项临床技术而言,理论与实践都是相辅相成的。伴随着实践的进取,理论将嬗变革新,同时,理论创新也是实践进步的重要原因与动力。然而,针灸技术一向是崇古的思想占据主流,迄今为止,我们的针灸教材中还是以传统的针灸理论占据主导,即以经络理论、腧穴理论作为针灸临床的核心基础,临床上渐呈活跃的技术思想无法进入主流理论体系,这不仅制约了临床实践的继续进步,于理论本身而言,亦将逐渐失去活力。
1 厚此薄彼的理论
目前,我们传承与修习的针灸理论与技术,主要来源于传世文本。不过,传世文本是否是技术传承的唯一途径呢?我们对文本中的理论与经验的记录是否有选择性传承呢?其实,从古到今,针灸临床的传承一直存在于明暗两种路径。
一是理论色彩极浓的文本针灸路径。这是一条明线,《内经》《难经》《黄帝明堂经》肇其源,至《针灸甲乙经》成为体系,后世《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十四经发挥》《针灸大成》《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等针灸名著不断整理、发挥,一直以来是学习针灸的正途。这一路径以文本为载体,其理论核心是经络、腧穴学说,并且在经络与脏腑理论融合的过程中,将脏腑辨证理论引入其中,民国后逐渐发展出了穴性的概念,将穴位与中药相比附,从而将针灸与中医方脉理论融为一体[1]。这一路径一直以来占据着理论的主导话语权,也是今天针灸教育与临床的主流。
此外,还有一条暗线,就是主流文本之外的以民间传承为主的针灸临床经验。这一路径多以口口相传为传承方式,而且内容体系性不强,不重说理,不容易被经络、脏腑理论所解释。不过,医家在编辑医书时亦收录了部分经验进入文本,这令我们能够看到这一传承形式的蛛丝马迹。如明代以来影响深远的《针灸大成》,全书共10卷,除卷10述小儿推拿外,多数篇目都是引述《内经》《难经》的经典论述以及腧穴主治等内容,卷9中收入了部分不适合用经穴体系解释的治疗方法,如取灸痔漏法、灸小肠疝气穴法、雷火针法、蒸脐治病法等,这些方法往往容易被忽视。近数十年来,新的针法不断出现,除了传统的刺血法、割治法等之外,皮内针、针刀、松筋针、浮针以及各类局部微针法的应用都越来越广泛。此类针法的理论基础或根本不提经络腧穴系统,或与之貌合神离。
文本传承的针灸医学理论性很强,表现为系统的脏腑、经络、腧穴、刺灸法、诊断与治疗理论,说理时丝丝入扣,但是实用性往往欠如人意。民间传承的针法虽然疏于说理,却往往确实有效。有些针法其实也有自己的理论解释,只是没有被教材所纳入,在没有形成共识及至进入教材之前,不同的临床理论泥沙俱下。如针刀医学,以软组织外科学、脊柱病因治疗学、骨质增生病因学等理论为支撑,形成了体系化的说理框架[2];而有些针灸技法却出现了不切实际的说理系统,如将八卦名称附会于人体的某些部位,甚至根据五行与八卦相合的生克关系来解释原理。
一方面新的实践技术无法得到既有理论的支持,自发发展的临床理论又良莠不齐;另一方面我们传承着基本上一成不变的传统理论,这是目前针灸临床与教育中的一组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只有将失之空洞的理论重新分析,部分解构并引入新的理论资源,形成丰富的、开放的新的针灸学术理论体系,这一任务只有理论家才能完成。
2 理论研究的立场
理论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学习与继承。既然是研究,必然是分析既有理论形态的来源、演变、内涵、外延、实用性、思想基础等,歌功颂德式的所谓“研究”是没有意义的。既有针灸理论,如经络、腧穴理论仅仅是多元针灸临床的一种解释而已,对之持以冷静的态度严格考量,还针灸技术一个清晰的理论形态,是我们所应秉持的立场。
举例而言,腧穴理论中有一个重要概念“八会穴”,出于《难经·四十五难》,原文为:“经言八会者,何也?然:腑会太仓,脏会季胁,筋会阳陵泉,髓会绝骨,血会鬲俞,骨会大杼,脉会太渊,气会三焦外,一筋直两乳内也。热病在内者,取其会之气穴也。”对本段文字,《难经》注家的理解大约一致,八会为八个腧穴,分别是腑、脏、筋、髓、血、骨、脉、气之会,合称为八会穴。如今八会穴作为一组重要的腧穴,临床应用较多,多数时候我们用“某会”去治某病,如用悬钟(绝骨)治疗脑部疾病,理由为“髓会绝骨”,“脑为髓之海”,且不说这样牵强的解释是否有道理,仅仅是对《难经》的一句表达奉若神明的态度就是不可取的。事实上,用一个腧穴通治一类组织的病变本身就是荒谬的。那么,八会穴的理论意义在哪里?明代滕万卿《难经古义》云:“按内经载热病五十九刺法,各处热邪,随分取之。此篇由是立八会法以适简约,盖此八会十三穴。诸热在身内者,各随其部分而治之。”滕氏的解读有一定见地,将八会理解为八个部位的代表腧穴。进一步思考,八会穴除了代表八个身体的不同区域之外,尚可反映古人对人体组织的认知观念。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论:古人认为人体由腑、脏、筋、髓、血、骨、脉、气等八种组织构成,或者至少主要由此八种组织构成?这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角度。
对待新的理论形态,则宜持开放与审慎的态度。新的学术成果,宜及时引入到针灸理论体系中来,而某些限于假说的理论不妨等待较长时间的临床检验。西学东渐,尤其是民国以来,西方医学的书籍不断地被推介到中国,对针灸学影响最大的成果当然是解剖学与生理学,尤其是神经生理学。民国时期针灸书中已经较为普遍地引入了局部解剖内容,神经学说也成为当时较被认同的针灸效应解释,这样的成果不仅仅是对针灸理论的丰富,更有力地推动了针灸理论革新与临床进步。相反的例子亦有,如: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重要临床理论,经由脏腑理论与穴性理论的中介,被引入到针灸临床,令针灸临床在某种上“方脉化”,虽然表面上是对针灸临床理论的发展,实际上这一“方脉化”的理论并不适合针灸临床[3]。
3 理论研究的路径
理论研究不同于实验研究与临床研究,有其独特的路径与方法。笔者经多年的摸索,认为基于文献梳理,从概念考证入手,出于学术史考查,大约为理论研究的恰当路径。
文献是理论研究的核心材料;理论研究的前提是文献整理与阅读。针灸文献的整理工作不能完全依赖中医文献专门学者,针灸理论研究者更是需要亲自动手去挖掘与梳理。一是因为针灸文献的专门性很强,对针灸理论不是非常熟悉的整理者从事这项工作难度很大,而且容易出错,尤其是而对新材料,如出土文献、古代抄本等,事实上当前针灸文献专家亦多是出于针灸学界,如李鼎先生、黄龙祥先生等;更重要的原因是,文献整理的同时,理论研究就开始了,整理文献本身就是发现与思考理论问题的过程,作为理论研究的学者是不可能避开文献整理这一环节的。
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对基本概念术语的源流的考证,是学术研究的根基功夫。很多时候,厘清了基本概念术语的源流与意义,理论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下面以“阿是穴”为例阐述之。“阿是穴”出于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灸例》:“故吴蜀多行灸法。有阿是之法,言人有病痛,即令捏其上,若里当其处,不问孔穴,即得便快成(或)痛处,即云阿是。灸刺皆验,故曰阿是穴也。” 一般认为阿是穴是无具体名称、无固定部位、以痛处为穴、多治疗局部筋伤疼痛等症的一类穴,与经穴、奇穴并列。然而,严格地说,“阿是穴”不是一类穴,其本质是一种取穴法,该取穴法的思想也不是从唐代才有的。查考古人寻取治疗部位,多不拘泥于骨度分寸,《灵枢·经筋》载:“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阿是取穴法被医家多有验证,《针灸资生经·背痛》中说:“背疼乃作劳所致。技艺之人,与士女刻苦者,多有此患(士之书学,女之针指,皆刻苦而成背疼矣)。色劳者亦患之,晋之景公是也,惟膏肓为要穴。予尝于膏肓之侧,去脊骨四寸半,隐隐微疼,按之则疼甚。谩以小艾灸三壮,即不疼。它日复连肩上疼,却灸肩疼处愈,方知《千金方》阿是穴犹信云。”本是一种取穴法,但由于针灸临床腧穴处方渐有体系,一病一症往往多穴治疗,腧穴也有了固定的部位与名称,所以,本来是泛用于腧穴取穴的阿是之法,在后世渐渐演变成经穴之外的独立类穴。后世的针灸著作中常将阿是穴与其他经穴并列作为针灸处方,如:“项强:风门、肩井、风池、昆仑、天柱、风府、绝骨,详其经络治之,兼针阿是穴。随痛随针之法,详在于手臂酸痛之部,能行则无不神效”(《勉学堂针灸集成·卷二·颊颈》)。阿是穴的本质是取穴法,在肌肉、纹理、节解、缝会、宛陷之中以手按之,病者快然,即是腧穴所在。作为临床上寻找腧穴的过程,阿是取穴之法可广泛适用于所有腧穴,从这一角度言,所有腧穴都是阿是穴,然而在腧穴体系化过程中“阿是”渐渐演变为与经穴、奇穴相并称的一类穴[4]。
概念考证是理论研究的核心,学术史研究则是理论研究的必然走向。理论的由来、演变、固化、冲突、转折等过程的考查,都是学术史研究的题中之义。为什么体系化的针灸理论越来越疏离于临床?答案必须在学术史中查找,查找针灸理论的变迁中发生了什么。笔者考查,如今的针灸理论所具备的高度稳态,基本固化于宋金元时期。唐代之前,文本资料很少,多数针灸技术还是在门阀山林医者之手;宋金元时期,文本资料很大地丰富起来,而且形成了儒医群体,这一群体对医学理论的要求较高,所以援引儒家理论进入医学,形成了固化的带有儒家文化色彩的针灸理论,如子午流注[5]。固化的理论一直延续至清代,晚清民国时期,随着科学化的思潮的风行,针灸科学化亦是一时之新,此时的针灸理论开始打破明清以来的桎梏,迎来空前的变革。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叶之后,受当时“西学中”运动的影响,针灸界又放弃了本已成绩斐然的科学化努力,折向明清针灸的传统[6]。学术史研究旨在谋求直相,所有考查的背后都隐藏着破与立的双重意义:对理论变迁的梳理可以破除对既定理论的迷信,更有勇气打破惯性的理论框架,从而吸纳新的、更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进入针灸理论体系。
4 小结
目前,针灸理论仍然处于惯性的传统之中,而临床却在独力开拓,新的针灸技术不断出现,传统的针灸理论已经无法胜任临床的解释,更遑论引领实践。针灸理论如果不打破高度固化的既有系统,将与临床渐行渐远;没有理论家参与的针灸临床自行构架的某些理论体系或假说则不切实际,针灸理论家任重道远。
欲立先破。在建立新的学术理论体系之前,需要检视既有理论的前世今生,从概念考证入手,厘清术语内涵与意义的演变,这是最基础的工作,目前,学术界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7-8]。引入社会史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将针灸理论的演变置于社会演变的历史中考量,检查学术理论形成与演变过程中的社会因素的影响,是针灸理论研究的新取向,也是很有价值的取向。
参考文献
[1] 谭源生. 民国时期针灸学之演变[D]. 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 2006.
[2] 朱汉章. 针刀医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完善[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06,8(4):85-93.
[3] 张树剑,黄龙祥,赵京生,等. 对针灸“辨证论治”的回顾与省思[J]. 中国科技史杂志,2016,37(1):92-99.
[4] 张树剑. 阿是取穴法源流论[J]. 中国针灸,2013,33(2):165-167.
[5] 张树剑. “子午流注”针法理论思想探析——兼论金元针灸理论之固化[J]. 针刺研究,2015,40(2):161-165.
[6] 张树剑. 近现代针灸科学化实践与转向——以朱琏为中心[J]. 中国针灸,2014,34(10):1009-1015.
[7] 赵京生. 针灸关键术语考论[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8] 赵京生. 针灸学基本概念术语通典[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本文原载于《中国针灸》2017年3月第37卷第3期,版权归作者所有。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聂广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wap.sciencenet.cn/blog-279293-1499265.html?mobile=1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