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转载]hLife | 从NF-κB到cGAS:陈志坚教授访谈——揭开固有免疫的奥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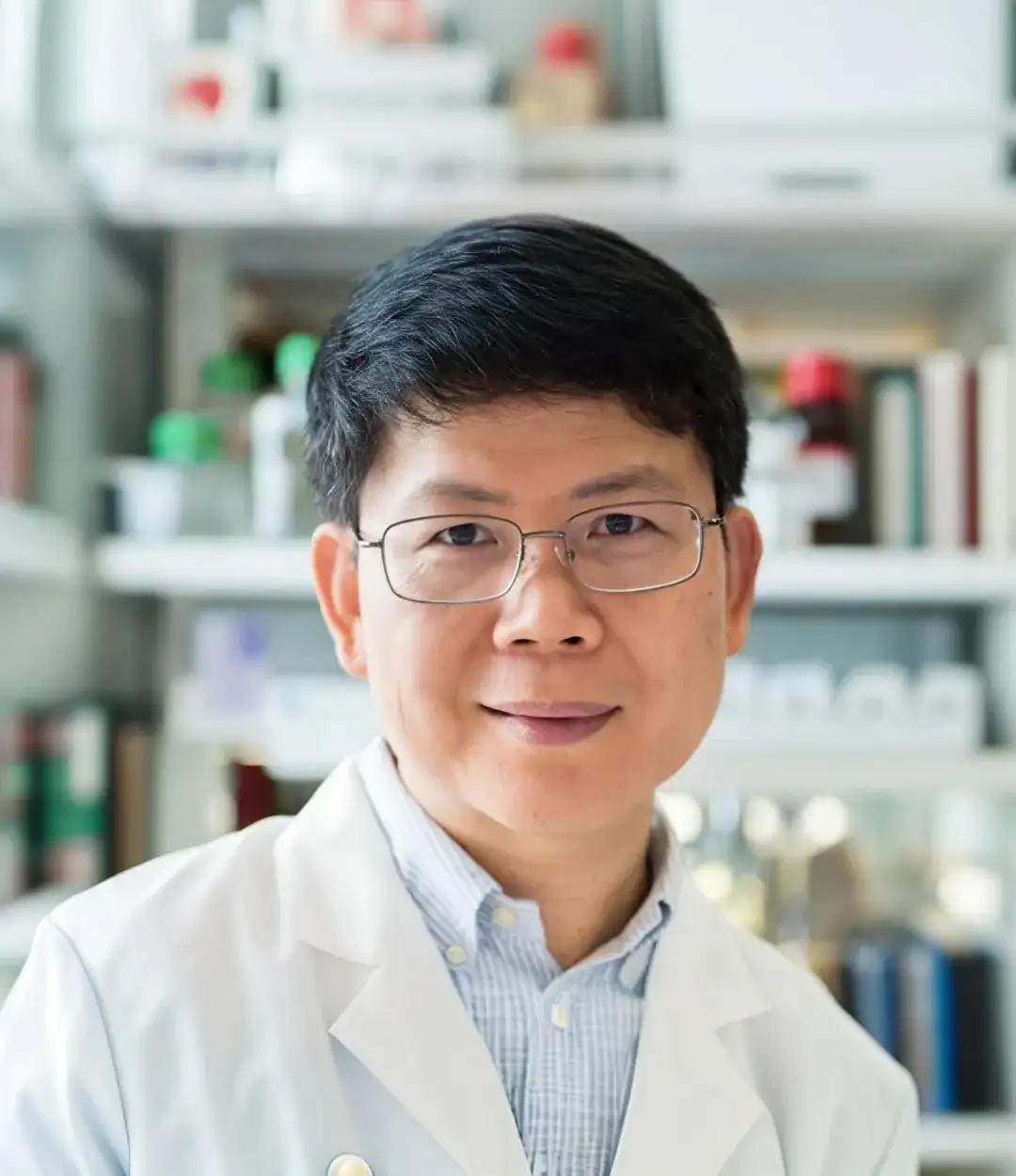
陈志坚 教授 hLife 编委
陈志坚教授,固有免疫领域的杰出科学家,因其对环鸟苷酸-腺苷酸合成酶(cyclic guanosine monophosphate-adenosine monophosphate synthase,cGAS)的突破性发现,荣获2025年保罗·埃利希和路德维希·达姆施泰特奖(Paul Ehrlich and Ludwig Darmstaedter Prize)以及2024年阿尔伯特·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Albert Lasker Basic Medical Research Award)。他的研究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固有免疫应答的理解,特别是揭示了cGAS作为细胞质DNA传感器触发干扰素应答的作用。在这次对话中,陈教授回顾了他的研究历程,从最初对泛素和NF-κB信号的探索,到MAVS和cGAS的发现,展现了他对细胞信号传导及人类疾病的持久热情。陈教授强调,科研工作的关键在于不畏艰难关注具有深远影响而且尚未解决的问题,且能坚持不懈。这次交流不仅为有志于科研的年轻学者提供了导师般的视角,也凝练了生物医学研究成功之路的精髓。
更多内容欢迎查阅hLife dialogue论文"From NF-κB to cGAS: An interview with Prof. Zhijian James Chen on unraveling innate immunity"。🌸🌸🌸
曾文文:首先,我们衷心感谢陈老师拨冗接受这次的访谈邀请。能够有机会开展这样的学术对话,我们都非常荣幸。在正式开启讨论之前,我们想先引出一个较为宏观的问题:年轻科学家应该怎样选择研究方向?例如,年轻的独立研究员(PI)在组建新的研究团队时,应该优先考虑哪些因素?当前的科学领域发展迅速,应该怎样识别值得探索的研究课题?相信您的经验可以为初入学术殿堂的年轻学者提供宝贵的指导。
陈志坚:在科学研究中,优先关注具有深远影响而且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取得突破性发现的关键。“问题驱动”作为导向的研究本质上更强调解决核心科学问题,而不仅仅是简单地积累数据。虽然数据积累很重要,但它并不等同于真正的发现或知识。所以,提出关键问题,并找到有效的解决路径,是科研中最核心的环节。同时,时刻关注新发现和具有启发性的研究也至关重要,尤其是那些不在意料之中的发现。有时候,实验结果跟预期不同,反而可能是新发现的关键。有些研究者在实验不如预期时会感到沮丧,但是也有人从这些意外中获得灵感,并进一步深入研究,反而有意义重大的发现。挑战在于,怎么准确判断哪些意外观察是“噪声”,而哪些可能蕴含突破性的科学价值。
Lai Guan Ng:科学家的道德素养至关重要,我们的责任不仅限于研究,还包括我们作为个体的行为。我们的贡献与社会紧密相连,不仅由科学成就定义,更由我们所展现的善良和正直所塑造。您希望您对科学和社会的贡献以何种形式被铭记?
陈志坚:作为一名教授和科学家,我们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所取得的发现,另一方面体现在我们培养的下一代科学家身上。在培养年轻科学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仅是传授他们技术和现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他们如何识别重要问题,以及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正是他们,将在未来做出令人兴奋的新发现。在科学发现方面,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如 MAVS 和 cGAS,已产生深远影响。cGAS 在进化中存续数十亿年,从细菌到人类,它在抗病毒免疫防御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正是基础研究的魅力所在,一个小型科学家团队能够率先发现自然界中存在数十亿年的重要通路,并且这一发现将继续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曾文文:在您的学术旅程中,从最初研究NF-κB和模式识别受体,到发现cGAS,再到如今专注于转化医学和人类疾病,可以想象挑战始终相伴。您能分享一下是什么动力让您保持持久学术热忱么?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过让您重新审视自己研究方向的时刻?
陈志坚:科研之路总是充满起伏,大多数实验并不会如预期般顺利。但只要实验设计合理,包含合适的阳性和阴性对照,每一次实验都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有些人在实验“不成功”时会感到沮丧,但这并不是正确的科研态度。正确的科研方法是认真分析数据并设计新的实验,不断推动研究向前发展。有时候,无论你多么努力,一些实验仍然无法取得预期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重新评估自己的研究目标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或许可以考虑转向其他项目。但如果它确实至关重要,并且坚信自己有能力解决它,那么就应该尝试不同的方法,继续努力,直至达到目标。
以cGAS为例,最初我们有一位博士后试图建立一个无细胞系统来识别难以捉摸的DNA传感器。他最终成功建立了一个通过STING但不是DNA激活IRF3的体外系统。于是,他转而研究STING如何激活IRF3,并发表了一篇高质量论文,阐述STING C端在IRF3激活中作用。我们本可以就此止步,但还是希望找出STING上游被DNA激活的分子,它或许就是那个DNA传感器。这项任务由实验室一位非常具有才华的博士后孙立军接手,他花了两年时间才成功建立起有效的体外实验体系。随后,他与刚加入实验室的研究生吴家曦密切合作,基于体外实验体系分离细胞提取物,最终发现了cGAS和cGAMP。那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时光,但实验过程很艰辛,许多实验都在低温室中进行,且并非总能成功。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这种DNA传感活性非常难以纯化,我们用掉了2000多皿细胞,仍然无法达到理想的纯度。当然我们没有放弃,支撑我们坚持下去的,是实验体系中持续存在的活性信号,我们知道,它的确存在,只是需要在大海捞针般的过程中找到它。
最终,我们设计了一种新的策略,结合多种纯化方法和定量质谱分析,成功鉴定出这一DNA传感器。结果表明,它是一种全新的酶,我们将其命名为cGAS。我认为,这正是科研精神的体现——坚定不移地追求目标,始终对实验数据保持信心,并在面对挑战时灵活调整实验策略。
曾文文:谈到拥抱各种技术推动研究进展,您能否分享一下您学习质谱分析的经历?这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深刻地体现了一位前沿研究者如何保持学习状态,适应并运用不断发展的技术。
陈志坚:当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读研究生时,我就深刻认识到蛋白质鉴定的重要性——一旦知道蛋白序列,就能确定对应的基因。那时,我必须纯化50微克的酶,通过Edman降解获取多肽序列,然后构建cDNA文库筛选来找到目标基因。后来,质谱技术在蛋白质鉴定方面展现出强大的能力,而质谱与基因组测序的结合,使得从少量纯化或部分纯化的样本中鉴定基因成为可能。然而,20年前,精通高灵敏度蛋白质质谱的人寥寥无几,我意识到这正是我们研究中的瓶颈。
2005年,我很幸运地成为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的研究员。当时,我决定重返实验台,部分原因是我已经厌倦了整天坐在电脑前。我选择学习质谱技术。在王晓东教授的帮助下,我前往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在那里向陈涉老师学习了一周。他负责研究所的质谱平台,对技术细节极为关注,因此能在高灵敏度下进行质谱分析。在他的帮助下,我学到了不少“诀窍”,随后在自己的实验室建立了质谱平台,并乐在其中地操作仪器。我教我的学生如何做质谱分析,他们后来比我做得更好,于是,我不得不遗憾地回到电脑前了。
事实证明,我在质谱方面的实践经验在后续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我深入了解其技术特点,包括优势和局限性。这使我构思出将不同的纯化方法与定量质谱相结合的实验策略,从而成功鉴定出cGAS——一个难以纯化至均一性的蛋白。研究者对诸如盐浓度、缓冲液组成等技术细节有深入理解,才能在生化实验中提供有效指导并解决难题。有时候,决定实验成败的,往往就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
曾文文:如果有机会,您现在想探索哪些特定的技术或知识领域?
陈志坚: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回到实验室学习如何做CRISPR实验。另外,人工智能(AI)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领域。
Lai Guan Ng:AI目前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人们普遍认为AI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挥作用。您认为AI技术会在您的研究领域带来重大突破吗?还是说它在某些生命科学研究领域仍然无法发挥关键作用?AI是否有可能在特定应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预测蛋白质结构?
陈志坚:从AlphaFold到AlphaFold3,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AI将在未来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蛋白质结构研究中,AI可以预测几乎所有蛋白质甚至一些蛋白质复合物的结构。另一个潜在的应用是预测与蛋白质靶点结合的小分子,这与药物开发密切相关。目前,许多公司和机构正在开发“虚拟筛选”系统,即基于结构的小分子发现方法,用于寻找候选分子并加速药物开发。这一方向无疑会吸引很多人的关注,并必将带来重大进展。AI在基因组学研究中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因为AI擅长处理复杂信息,如大数据分析。然而,人类的创新思想在短时间内很难被AI取代,尤其是一些原创性创新。因此,建立科学家与AI之间的有效合作将有助于加速研究效率。在我看来,AI将在未来的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大数据分析、蛋白质结构预测、小分子筛选,甚至抗体或任何蛋白质的从头设计。
Lai Guan Ng:研究范式在不久的将来会改变吗?我们应该做哪些准备来应对这些变化?
陈志坚:我认为包括AlphaFold和生物信息学在内的AI技术,都将成为未来的标准工具,每个人都应该熟悉它。现在学习AI技术变得更加方便,因为AI可以帮助你进行编码和调试。AI将在不久的将来极大地加速研究以及许多其他任务的进展。
闫群:谈到您的过去以及它如何促成您今天的成就,我读过一些关于您的故事,知道您在学校时的学术表现非常出色。您能否分享一下您当时选择生命科学作为大学专业的原因?
陈志坚:坦白说,生物学并不是我的第一选择。申请大学的时候,我列了一些心仪的大学,但最终没有被其中任何一所录取。幸运的是,我还是进入了大学,被福建师范大学生物系录取。一开始,我很难接受必须学习生物学这个事实,因为我原本准备学习物理。当时,我只有15岁,正处于叛逆期,对动物学和植物学毫无兴趣。直到大学二年级,我才意识到必须做出改变。那时,我开始上生物化学课。我的生物化学老师张其昌是一位出色的老师,他激发了我对生物化学的浓厚兴趣。一位好老师对一个人的职业生涯非常重要。对我而言,正是这种日益增长的兴趣促使我投身于生化研究,回想起来,这也算是一次幸运的偶然。如果我选择了数学或物理专业,很难想象我今天可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回顾过去,我觉得自己更适合从事生物化学的研究,因为我不仅喜欢这门学科,而且在这方面有点“悟性”。
现在,生物学研究涵盖了许多领域,包括发育生物学、神经生物学、遗传学、免疫学和细胞生物学等。我们实验室的工作也涉及多个学科方向,核心关注点是利用生物化学方法解决生物学问题,特别是在免疫学领域。因此,我们对免疫学的研究方法与经典免疫学有所不同,后者大部分依赖流式细胞分选(FACS)来识别各种细胞类型。然而,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细胞免疫学只是免疫学领域的一个分支,免疫学还包括分子免疫学、结构免疫学等其他方向。我一直认为,生物化学是一门宝贵且历史悠久的学科,因为它仍然是理解所有生物学分支的分子机制的基础。
生物化学有两种主要的研究范式:第一种是通过遗传学和其他方法证明某一分子的重要性,然后研究其机制,而生物化学则是最直接的研究方法;第二种范式是运用生物化学方法做出原创性发现,然后通过遗传学和其他方法进行验证。我们在cGAS方面的工作就是第二种范式的一个例子。我们首先通过生物化学方法找到了DNA传感器,然后再通过小鼠遗传学和结构生物学等更为标准的方法验证了这一发现。关键在于找到DNA传感器,其他的工作相对来说就是顺其自然的延申。
曾文文:生物化学方法在解决分子水平的问题上无疑至关重要。然而,当前的许多研究似乎更多关注具体的表型和应用,而非基础的分子机制。这一趋势可能与研究人员对生物化学兴趣的下降有关。对实际结果的重视超过了对基础知识的关注,引发了人们对分子研究的未来以及这一学科的重要性的担忧。
陈志坚:这是确实是个问题。如今许多年轻人,包括PI,可能会觉得生物化学已经过时,或者蛋白质纯化工作繁琐且难以持续。相比之下,从事单细胞RNA测序(scRNA)这样的研究可以生成大量数据,他们觉得这更有回报。然而,将数据转化为知识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生物化学方法专注于解决特定问题,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来识别分子。例如,蛋白质纯化已经成为一门“失传的艺术”,它需要丰富的经验和技能,但如今很多人已经不知道怎么去做,这确实很遗憾。
回顾重大发现的历史,许多诺贝尔奖获奖成果都是利用传统的生物化学方法完成的。从生物化学中获得的技能适用于各个领域,包括免疫学、神经科学、微生物学等。生物化学提供的证据通常是最直接的。例如,通过CRISPR筛选或其他遗传学方法发现具有重要功能的基因,如果该基因没有已知功能,单凭遗传学方法很难揭示其作用机制。以cGAS的发现为例,遗传学方法本可以识别该分子,但当时它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基因,其机制完全不清楚。正确猜测其机制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几个步骤的配合:首先,知道它的活性是由双链DNA激活的;其次,理解反应需要ATP和GTP;第三,识别形成的最终产物,这是一种新型的环状二核苷酸。要正确猜测到所有这些步骤是非常困难的。
闫群:回顾您的学术生涯,您有什么经验或教训想与我们分享吗?您认为成为一名成功的科学家需要具备哪些品质?
陈志坚:我的学术旅程并没有经历太多的艰辛或痛苦;相反,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虽然我成长在乡村,起点较低,但我一直在一步步稳步前进。上大学和出国留学是我小时候从未敢想过的事情,也从未计划过。小时候,我甚至没考虑过上大学,直到中学时才知道大学的存在。没能进入一所顶尖大学对我来说是一种挫折。然而,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这让我发现了对生物化学的热情,这成为了我大学经历中最重要的收获。我认为,学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培养对某一学科的热情。
后来,当我出国后,我发现实验室设备非常先进。在国内时,我甚至不知道移液器是什么。我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SUNY Buffalo)读研究生。虽然当时的实验室设备无法与今天相比,但已经远远优于我在大学时的设备,有移液器和快速蛋白质液相色谱(FPLC)可用。我觉得应该珍惜这样的条件来做研究。那时,我没有什么宏伟的抱负,我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资格考试并顺利毕业。当时的信息也非常有限,我的宿舍里没有电视,也很少看报纸,那时还没有互联网。所以,我只有一个目标:努力学习,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做实验,发表论文,然后毕业。至于毕业后做什么,我没有想太多。我大致知道有两条路:一条是学术界,另一条是工业界,两者似乎都不错。如果选择学术界,我没有奢望能在顶尖学校获得职位,我觉得能在二流或三流学校找到一个教职岗位就非常满意了。所以,我没有什么特别宏大的目标。
尽管如此,在博士期间,我在导师Cecile Pickart教授的指导下接受了很好的训练。她是一位杰出的生物化学家,教会了我蛋白质纯化和酶相关的测定方法,并将我带入了泛素这一令人着迷的领域。但是,我的导师不熟悉分子生物学,也没有克隆经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向另一个实验室的病毒学家Ed Niles博士学习了分子克隆,他成为了我的非正式联合导师。这种全面的训练使我能够从粗提物中纯化蛋白质,进行Edman降解以确定其肽序列,然后筛选cDNA文库以识别基因。这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学习经历。
虽然我研究生的研究成果没有发表在顶级期刊上,但我在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上发表了两篇论文。第一篇论文描述了一种名为E2-25K的酶,它可以合成多聚泛素链,而第二篇论文则专注于克隆编码该酶的基因[3]。虽然这些论文没有发表在所谓的“高影响力”期刊上,但它们都是很好的论文,使我得到了我很好的训练。当时,我的最高目标就是在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上发表论文。在我研究生的前两年,我甚至不知道Cell是顶刊,所以我并不太关注这些区别。我的研究生同学都很清楚哪些期刊是顶级的,而我当时比较天真。
后来,我作为博士后研究员加入了索尔克生物研究所,那里的实验室规模很大,有大约二十人,其中包括十多名博士后。起初,我感到有些自卑,认为那里的每个人都比我更有能力。他们经常谈论篮球和芝加哥公牛队,那正是迈克尔·乔丹的巅峰时期。然而,我连乔丹是谁都不知道——那时的我真是太无知了!这种事情给我留下了多少印象呢?多年后,我在达拉斯的实验室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抗病毒基因,我们命名为MAVS。MAVS代表线粒体抗病毒信号传导,这也是达拉斯小牛队(MAVS)的缩写。后来,我偶尔被邀请去看MAVS比赛,这感觉像是一种安慰或报复。学生时代的我非常天真和单纯,由于没有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我对自己的职业选择一无所知。所以我只是待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回想起来,我很珍惜那段简单的学生生活。
闫群:您刚刚提到了Cell。我们的期刊hLife也刚刚创刊,我们想听听您对学术期刊的看法。如今,许多人经常讨论影响因子,但我认为它们并不是唯一的标准,甚至不是真正的衡量标准。回顾学术界本身,您认为一个期刊应具备哪些品质才能获得您的认可和信任?
陈志坚:确实,许多重大发现并没有发表在顶级期刊上。自噬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早关于自噬的研究论文发表在当时相对冷门的期刊上。然而,那篇文章通过筛选鉴定了许多与自噬相关的基因。同样,GLP1的最早克隆也没有发表在广为人知的期刊上。然而,GLP1后来获得了拉斯克奖,而引用的文章中没有一篇来自高影响力期刊。泛素研究也是如此,阿夫拉姆·赫什科(Avram Hershko)在泛素研究领域取得了开创性发现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他曾表示他最引以为傲的文章发表在BBRC上。因此,如果你的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在10年或20年后被公认为是原创且重要的发现,这足以证明期刊的成功。如果有两篇这样的文章,那说明这并非偶然,作为编辑,你应该感到非常自豪。当然,要改变当前对影响因子的关注的现状并不容易。关键是鼓励真正原创的研究投稿到你的期刊,如果这些研究确实具有原创性,它们最终会激发大量后续研究。一些重要发现在最初几年可能不会得到很多引用,例如,第一个microRNA的发现发表于1993年,最初几乎没有引起关注,直到7年后第二个miRNA被报道,该领域才迅速升温。
因此,重要发现不一定会立即引起巨大反响,编辑需要具备识别这些文章的眼光。如果编辑能深入阅读相关论文,并找到值得信赖的评审专家进行评估,那么刊登那些具有潜在重要性的研究,对于期刊而言至关重要。例如,在Cell创刊之前,生物学领域的顶级期刊是Science和Nature。Cell的创刊编辑Benjamin Lewin说服了哈佛和麻省理工的研究人员向Cell投稿,他承诺每篇文章他都会亲自阅读,并亲自决定是否录用,而不完全依赖审稿人的意见,同时,他还保证一些文章可以快速发表。正因如此,一些哈佛和麻省理工的教授开始向Cell投稿,这本期刊最终跻身顶刊行列。因此,编辑的作用至关重要,而编辑对科学的品味尤为关键。Benjamin Lewin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编辑,他能敏锐地判断出哪些研究重要,并洞察领域的发展方向。
闫群: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正如您所提到的,如今许多期刊编辑并非科学家,这导致他们在决策和邀请稿件时,往往更倾向于关注近期获得大奖的研究领域,或者那些未来可能成为热点、具有高引用潜力的方向,而不是评估一项研究是否具有真正的原创性和科学价值。很多时候,期刊的选择受趋势所左右,而非基于研究本身的重要性和原创性。
陈志坚:影响因子作为期刊评价指标,必然会对期刊的发展产生影响。但衡量一本期刊真正成功与否的标准,最终仍要经受时间的考验。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科学发现,比影响因子更为重要。如果你的期刊能率先发表两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那才是真正的成功。
Lai Guan Ng:今天很高兴能与陈教授交流,我们期待未来能更多地了解您的研究进展。
透过陈志坚教授的故事,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科学家的成就,更看到了一个科研工作者如何在逆境中寻找机遇。犹如在荆棘丛中摘下那朵最美的玫瑰,需要付出无数的汗水与坚持,但正是有着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才让这一切变得可能。谨以陈志坚教授这段导师般的谆谆教诲,与大家共勉!
作者简介

曾文文 教授 通讯作者 机构:清华大学

Lai Guan Ng 资深研究员 通讯作者 机构:上海市免疫治疗创新研究院

陈志坚 教授 通讯作者 机构: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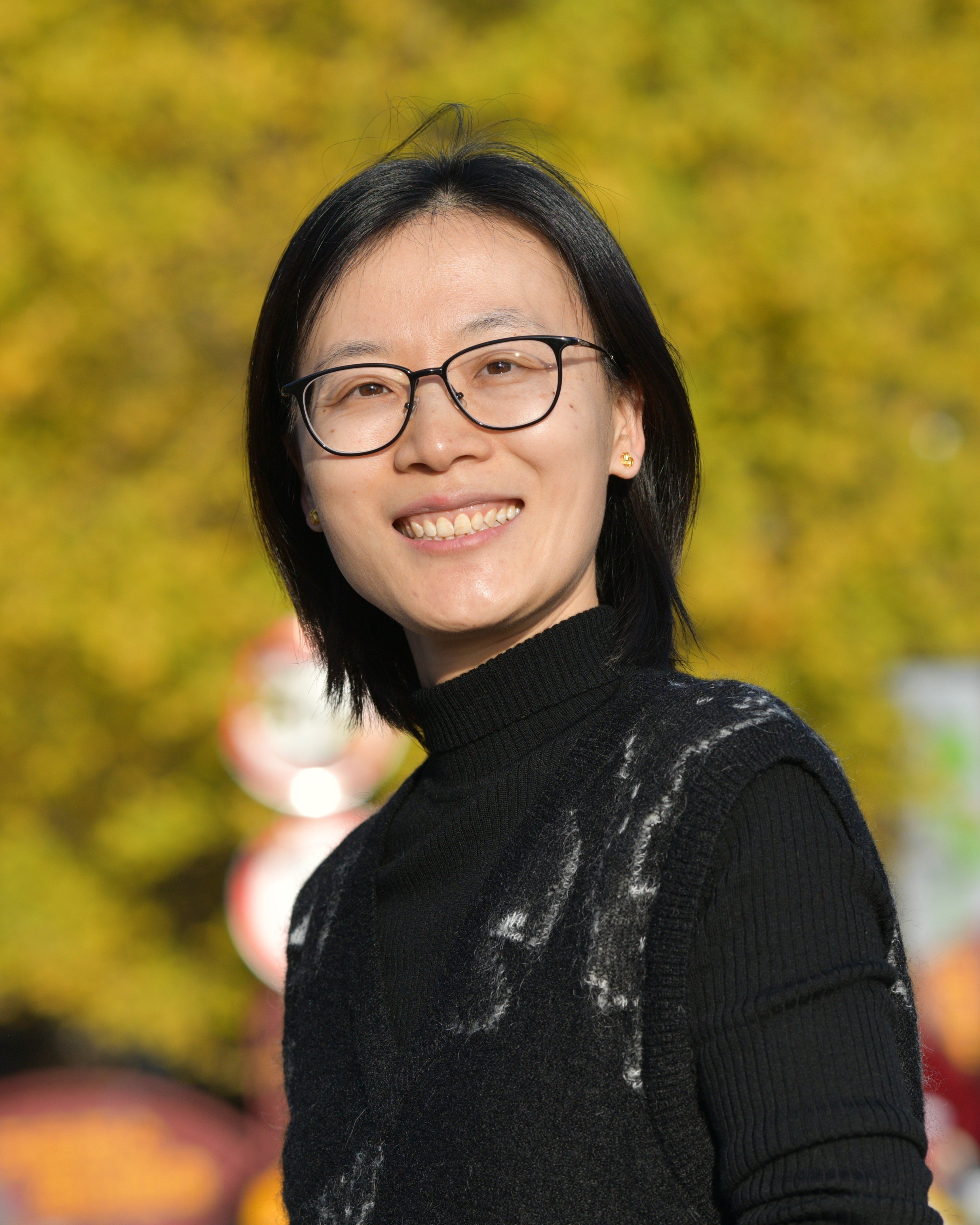
闫群 副编审 通讯作者 机构: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引用格式:Zeng W, Ng LG, Chen ZJ, et al. From NF-κB to cGAS: An interview with Prof. Zhijian James Chen on unraveling innate immunity. hLife 2025; https://doi.org/10.1016/j.hlife.2025.03.002.
参考文献
1. Sun L, Wu J, Du F, Chen X, Chen ZJ. Cyclic GMP-AMP synthase is a cytosolic DNA sensor that activates the type I interferon pathway. Science 2013; 339: 786–91.
2. Chen Z, Pickart CM. A 25-kilodalton ubiquitin carrier protein (E2) catalyzes multi-ubiquitin chain synthesis via lysine 48 of ubiquitin. J Biol Chem 1990; 265: 21835–42.
3. Chen ZJ, Niles EG, Pickart CM. Isolation of a cDNA encoding a mammalian multiubiquitinating enzyme (E225K) and overexpression of the functional enzyme in Escherichia coli. J Biol Chem 1991; 266: 15698–704.
4. Gao GF, Dong C, Hoffmann JA. hLife: Linking basic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hLife 2023; 1: 1–2.
5. Tsukada M, Ohsumi Y.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utophagy-defective mutants of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FEBS Lett 1993; 333: 169–74.
6. Mojsov S, Heinrich G, Wilson IB, Ravazzola M, Orci L, and Habener JF. Preproglucagon gene expression in pancreas and intestine diversifies at the level of post-translational processing. J. Biol. Chem 1986; 261: 11880–9.
7.Ciehanover A, Hod Y, Hershko A. A heat-stable polypeptide component of an ATP-dependent proteolytic system from reticulocytes. Biochem Biophys Res Commun 1978; 81: 1100–5.
8. Lee RC, Feinbaum RL, Ambros V. The C. elegans heterochronic gene lin-4 encodes small RNAs with antisense complementarity to lin-14. Cell 1993; 75: 843–54.
9. Pasquinelli AE, Reinhart BJ, Slack F, Martindale MQ, Kuroda MI, Maller B, et al. Conservation of the sequence and temporal expression of let-7 heterochronic regulatory RNA. Nature 2000; 408: 86–9.
期刊简介
hLife由高福院士、董晨院士和Jules A. Hoffmann教授(2011诺奖获得者)领衔,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主办,中国生物工程学会,浙江大学陈廷骅大健康学院,西湖大学医学院,上海市免疫治疗创新研究院和广州霍夫曼免疫研究所联合支持,与国际出版商爱思唯尔合作的健康科学领域综合性英文期刊。
hLife聚焦健康科学领域的前沿进展,旨在促进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的融合发展。期刊发表与医学相关各研究领域最新成果,学科领域包括(但不限于)病原生物学、流行病学、生理学、免疫学、结构生物学、疾病监测、肿瘤、药物、疫苗和健康政策等。
hLife是一本金色开放获取期刊,月刊出版;2022年成功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高起点新刊”;2023年11月正式创刊; 2024年5月被DOAJ收录;2024年8月被Scopus收录。
2026年前hLife接收的稿件免收文章处理费(APC)。
期刊网址: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journ
https://wap.sciencenet.cn/blog-3552961-1486714.html
上一篇:[转载]hLife | 广州医科大学李锋/唐小平研究团队成功建立猴痘病毒IIb分支I和II型干扰素通路双缺陷小鼠感染致病模型
下一篇:[转载]hLife | 浙大刘越/王海波团队通过元基因组挖掘揭示dsDNA病毒中的新型病毒组蛋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