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选
精选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学术谱系与收缩的遗产
李侠,尹辉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上海 200240
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是20世纪下半叶“后默顿范式”科学社会学的核心。文章以关键人物及其著作为线索,系统梳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学术谱系,总结其核心理论、研究方法以及不同流派的思想变迁,力求清晰呈现其发展脉络和理论知识体系,有助于深化科学知识社会化过程的理解,为今后科技与社会研究以及相关科技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0 引言
20世纪,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为代表的早期知识社会学。曼海姆继承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传统,揭示了广义的知识和信念如何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初步动摇了“知识纯粹客观”的传统观念。然而,传统知识社会学明确区分“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认为后者具有独特性与稳定性,因此未将其纳入社会学分析的范畴。
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开创了科学社会学。他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将科学视为一种社会建制进行研究,并提出现代科学的四项规范——公有性、普遍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精神,进一步强化了自然科学的独特地位。但默顿传统倾向于探讨宏观社会与文化因素(如清教伦理、社会秩序)对科学活动的影响,对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及形式则鲜有触及。在整个知识生产链条上它仅关注载体的建制化与规范的运行,如科学发现的优先权、马太效应、多重发现与科学中的年龄等问题。该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对科学建制化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做了探讨,由此达到科学社会学的顶峰,自此也意味着它开始走下坡路。
促成科学社会学走下坡路的一个重要思想契机来自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于1962年发表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他从历史主义角度出发,提出“范式(paradigm)”“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ility)”“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等革命性概念,挑战了知识纯粹客观、线性积累的传统认识,凸显科学发展的群体性与历史性,为社会学深入介入科学知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第三阶段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与建构主义思潮在欧洲的兴起引发西方社会学研究重心的转向,科学社会学开始突破默顿传统的研究框架,转向直接考察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问题,这一取向被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即对知识本身进行社会学研究。按照发展线索来看,SSK起源于英国的爱丁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并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大主要学派:一是以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和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Edinburgh School),提出“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奠定了早期SSK理论基础;二是以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为代表的巴斯学派(Bath School),提出“相对主义的经验纲领(Empirical Programme of Relativism,EPOR)”,聚焦于科学争议研究;三是以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为代表的巴黎学派(Paris School),开创了实验室民族志研究。
SSK的核心主张可以在它的关键性代表人物的学说里得以展现它的研究旨趣。
1. 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

大卫·布鲁尔
大卫·布鲁尔,当代英国社会学家,爱丁堡学派核心人物之一。他长期在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中心任教,并在科学、技术与社会(STS)领域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就,至今仍被视为该领域的重要思想家。布鲁尔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军人物,其典型代表作《知识和社会意象》(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1976),一直被视为爱丁堡学派的奠基之作。
布鲁尔的核心目标在于对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进行社会学分析。他主张科学知识社会学不仅是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能揭示科学共同体的集体意识。在《知识和社会意象》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强纲领”,即因果关系、客观公正、对称性和反身性四项原则,接着,他运用这四条原则有力回应了人们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批评,从而证明了“强纲领”的可靠性与可行性。布鲁尔认为,所有科学知识,包括各种真理、信念的形成都离不开社会建构,因此这些内容都需要纳入社会学解释的范围,这种观点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相对主义色彩,但他也并未因此否定过客观知识的存在,而是试图借助社会学分析,为科学知识的生成提供一套更为全面的解释框架,这也是他建立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价值所在。整体而言,布鲁尔的贡献在于系统分析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过程,提出“强纲领”,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知识和社会意象》出版后也引发了诸多批评。例如,有人提出所谓的“强纲领”实际上等同于主张知识“完全是社会的”;也有人将科学知识社会学简单理解为探讨社会如何扭曲知识的过程。事实上,这些看似尖锐而又荒诞的批评,往往是建立在知识绝对客观的基础之上,在根本上否定了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可能。应当认识到,科学知识与物理世界并非处于同一层面:物理世界独立存在,知识生产则不可避免地经过社会的建构,并且始终浸润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正如布鲁尔所强调的,“所有知识都包含着某种社会维度,而且这种社会维度是永远无法消除或者超越的”。“强纲领”的合理性,也在后续的研究和实践中不断得到证实。
2. 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

巴里·巴恩斯
巴里·巴恩斯,英国著名社会学家,爱丁堡学派核心人物之一。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巴恩斯与布鲁尔在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中心一起工作,为SSK早期核心理论的创立发挥重要作用。他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Sociological Theory,1974)被视为爱丁堡学派的另一部奠基性著作。和布鲁尔侧重的“强纲领”不同,巴恩斯更多是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考察科学知识,关注科学的内容与形式。他在库恩范式的基础上,提出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其发展传播等符合文化的一般规律,而且科学共同体享有一套文化资源,包括理论、术语、符号、关于解释的一般观念、常识、美学和哲学偏好等等,文化资源界限明确,科学家在其内部开展研究。文化资源本身就是一种建构,而且受到各种因素(特别是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因此,科学知识绝非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例如,科学理论无法通过观察或实验直接得出,而是科学家对世界的描述,尽管如此,理论却能够成为指导科学家工作的准则,并为自然现象赋予秩序与逻辑,这种秩序是理论强加给世界的结果,绝非世界本身的固有属性。巴恩斯认为,科学总是在既有文化资源的框架中运行的,而科学的文化资源与其他文化总是相互交融、密不可分的,因此,科学史也是一部文化史。此外,巴恩斯有关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著作还有《局外人看科学》(About Science,1985)《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Scientific Knowledge:A Sociological Analysis,2002,与布鲁尔等合著)等。
尽管巴恩斯未能像布鲁尔那样提出具有标志性的“强纲领”成果,但他从文化社会学角度剖析科学知识的形成、传播、变迁等核心问题,为早期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与布鲁尔相似的是,巴恩斯同样难以摆脱相对主义的困境,只不过来自文化资源的相对主义较为温和。其次,他将科学视为一种文化的主张,虽在阐释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方面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独到之处,但也容易引发批评:科学在方法论、制度化以及实践等方面显然有别于一般文化,其论证不免存在偏颇之处。1992年,巴恩斯转到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社会学系,研究重心也由科学知识社会学逐渐转向普通社会学。
3. 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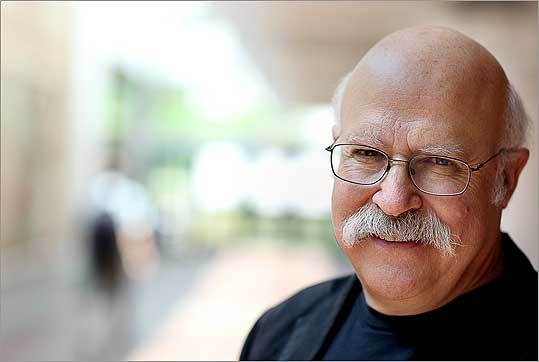
史蒂文·夏平
史蒂文·夏平,美国科学史家与科学社会学家,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他与西蒙·谢弗(Simon Schaffer)合著的《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玻意耳与实验生活》(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1985)是从科学知识社会学角度书写的科学史著作,它以17世纪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罗伯特·玻意耳(Robert Boyle)围绕“空气泵试验”展开的论战为中心,探讨科学事实的社会和政治建构问题。
夏平和谢弗首先揭示了玻意耳通过实验建构事实的机制。他们提出,在玻意耳的实验哲学纲领中,事实的建立运用了三种技术:①物质技术(material technology):比如空气泵等实验仪器,它们能够提高感知并构成新感知客体的能力;②书面技术(literary technology):玻意耳发明了详细的、非个人化的实验报告形式,为实验提供一种“虚拟见证(virtual witnessing)”的可能,即读者即便没有亲临实验现场,也不用亲自重复实验过程,通过阅读实验报告即可在头脑中重现实验,这被视为建构事实最有力的技术;③社会技术:实验需要合格的见证人或共同体,因为社会上层阶级的人员具有信用和优良的德行,他们的集体同意赋予实验结果以客观性和权威性。玻意耳通过一整套物质、书面和社会技术,使实验事实得以被产生、记录和确认,由此奠定了实验科学的基础。而霍布斯对此提出强烈的批评,认为实验无法产生无可辩驳的事实。在他看来,只要将制造这些事实所依赖的运作(work)过程加以揭示和公开,就能够动摇其所谓的客观性。换言之,霍布斯提出的“运作”,直接揭示了玻意耳建构事实的社会和技术机制,从根本上挑战了实验事实的权威性。其次,夏平和谢弗还表示,玻意耳之所以胜出,是因为他的实验模式,提供了一种非专制、基于共识的知识生产方式,这与当时英国复辟时期(Restoration England)的政治以及精英社会阶层的需求相适应,另外,实验者始终自称自己是虔诚信主的信徒,玻意耳自身也支持一些以决疑论和良心为措辞的复辟时期的政论;而霍布斯坚守几何学那套权威和演绎的知识体系,在当时带有一定的激进政治意味,与当时的精英偏好和精神相悖,因此,科学知识得以确立,并非仅仅因为其本身的客观性,还与当时政治环境和社会需求密切相关。
夏平和谢弗在《利维坦与空气泵》的最后写道:“当人们逐渐认清我们的认知形式有其约定俗成而人为的一面,就可以了解,我们认识的根本是我们自身,而不是实在。知识和国家一样,是人类行为的产物。霍布斯是对的。”这句话也揭示了SSK思想的精髓,所谓科学知识的客观权威,完全是人类约定俗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霍布斯是对的。
4. 迈克尔·马尔凯(Michael Mulkay)

迈克尔·马尔凯
迈克尔·马尔凯,科学社会学家,英国约克大学(University of York)社会学教授。他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思想主要集中在《科学与知识社会学》(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1979)一书中。该书不仅系统梳理了相关学术史脉络,论证缜密有力,而且语言简洁明快,是理解科学知识社会学核心思想、把握社会学思维的佳作。
过去科学知识因其独特性一直被排除在社会学研究范围之外,而马尔凯则让科学走下神坛,提出科学产品本质上同其他一切文化产品一样,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按照默顿传统的观点,科学共同体具备四种精神气质,这使得科学不同于其他知识,科学知识反映客观世界。但马尔凯却提出,精神气质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实际过程不起决定性作用,而是受限于文化资源。他认为科学家存在两种文化资源:一种是科学共同体提供的,另一种是社会环境提供的。科学知识生产无法摆脱这两种文化资源的影响,无论是科学事实、理论,还是观察、结论,都不是对自然界的直接反映,而是社会互动或者社会磋商的结果,换句话说,科学知识是在特定时间、群体以及环境下,科学共同体通过彼此交换观点、相互说服、施加影响后形成的主张,它是人们主动建构的,也是不稳定的、可变的。正因为环境总是将客观、权威、公正等与科学联系起来,甚至直接等同,所以很难察觉到文化资源对科学知识的制约作用,更甚者,有些科学家标榜自己客观中立,却主动选择性利用和解释现有文化资源,以此维护或扩大他们的利益。
值得补充的是,与爱丁堡学派擅长采用的“强纲领”理论分析框架不同,马尔凯将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引入SSK,结合语言学和修辞学的视角,通过分析科学家在话语或文本中的表达方式,揭示知识意义的构建不仅仅存在于实验的结果中,更在于描述科学的语言和修辞中。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单纯依赖话语分析难以全面解释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因为科学实验中的具体操作、技术手段和物质条件等非话语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形成同样至关重要,如果过分强调话语,则可能陷入文化决定论或滑向强相对主义的立场。
5. 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

哈里·柯林斯
哈里·柯林斯,英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巴斯学派的创始人。巴斯学派与爱丁堡学派几乎同期,但两者的研究取向和方法论有显著区别,爱丁堡学派强调“强纲领”,突出知识的社会建构,带有显著的相对主义倾向,而巴斯学派则更注重科学实践的过程性研究,特别关注科学争论中“得出结论的微观机制”。
柯林斯经典作品是《改变秩序:科学实践中的复制与归纳》(Changing Order: Replication and Induction in Scientific Practice,1985),代表了巴斯学派的核心观点。相对于布鲁尔的“强纲领”,柯林斯的创新点在于提出了“相对主义的经验纲领(EPOR)”,该纲领分为三步:第一步,寻找科学发现的解释(灵活的);第二步,揭示结束争论的机制;第三步,将解释机制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相关联。柯林斯的EPOR是一种方法论相对主义,要求社会学家在解释科学研究争议问题时,重要的不是关注“真理是什么”,而是关注“无法得出一致结论时,科学家是如何达成共识的”。因此,相较于布鲁尔的“强纲领“,柯林斯的EPOR更为微观,他经常走进实验室,亲自体验科学发现与解释的核心过程,将科学知识社会学推进到了实践研究阶段,为后来的实验室研究奠定了基础。
显然,与布鲁尔相比,柯林斯的相对主义走得并不彻底,他认为“即使科学完全是社会的,个体科学家也仍然应该按照好像科学不是社会的那样行事”,换句话说,科学家应该相信世界是真实的,并且是可以被人类认识的。笔者认为,科林斯的观点看似是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背叛,但实际上,这恰恰是对早期爱丁堡学派激进相对主义的修正。巴斯学派的诞生意味着SSK学术发生转向,特别到了80年代后期,随着爱丁堡学派遭到越来越多的内部以及外部的批评,不少学者抛弃原来的“强纲领”,并逐渐转向经验研究,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问题有了更准确的把握。
柯林斯是一位开放的社会学家,如果说布鲁尔是理论派,那柯林斯必然属于实践派,他为SSK注入新的方法论体系,将世界各地实验室作为田野,与科学家紧密互动,获得“一手资料”,用真实的案例(如探测引力波实验)解释问题,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提供扎实的经验支撑。
6.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史蒂夫·伍尔加(Steve Woolg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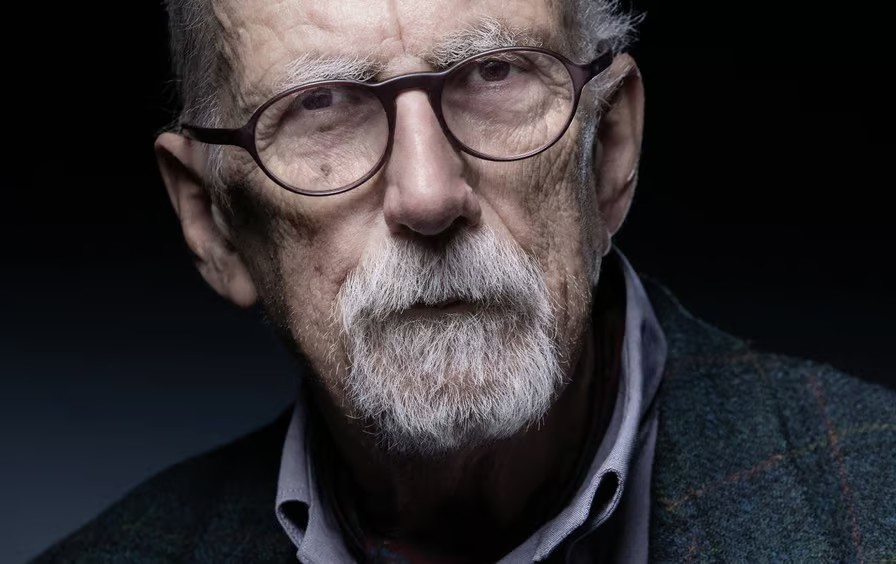

布鲁诺·拉图尔 史蒂夫·伍尔加
布鲁诺·拉图尔,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荣获2013年霍尔伯格奖(Holberg Prize),巴黎学派核心人物之一;史蒂夫·伍尔加,英国社会学家,牛津大学教授。他们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入SSK,发表了第一部实验室人类文化学志——《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Laboratory Life: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1979)。
《实验室生活》是一部夹叙夹议的学术著作,记录了大量访谈语录,用详尽的事实描述传达出如下观点:第一,实验室是一个文献记录系统。实验人员通过大量编码、标记、读写,将实验的自然现象转化为可供阅读的书面材料(如文本、曲线、数字、图表等),他们费劲全力将偶然的、不确定的现象转变成稳定的、可靠的事实。第二,科学事实在实验室中被建构。建构的途径有多种,比如实验仪器,科学实验高度依赖实验仪器,借助记录仪,人们完全可以制造出人为的实在,制造者再把人为的实在说成客观的实体;其次,为了论文发表,他们会采用各种修辞方法,努力说服论文的读者接受作为事实的陈述,而这不仅遮蔽了大量原始陈述,更掩盖了这一事实的社会构成及其历史;还有,实验室里科学家之间的微观互动(如日常交流)中也可能建构事实或摧毁事实。第三,科学事实的“黑箱化”。一旦最初的科学假设或观察得到广泛认可,就不再被质疑或者追溯其形成过程,而是被“黑箱化”成不容置疑的科学事实。第四,科学活动往往以功绩为导向。实验人员使用哪种仪器、研究哪个方向都取决于收益,包括可获得的资金、有利可图的机遇、发表论文的数量、未来职业发展等等,他们将获取利益作为科研活动的动机和最终目的。
后来,拉图尔没有止步于实验室人类学研究,而是与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约翰·劳(John Law)等巴黎学派学者共同创立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ANT不仅是对《实验室生活》的深化,更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它将科学家、机构、社会群体等视为人类行动者,将仪器、文本、资金、技术等归为非人类行动者,二者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结合成稳定的网络,科学知识就是在两者相互依赖和磋商中形成的网络产物,因此,行动者只需建构网络并维护网络的稳定性,便可以使科学知识“黑箱化”而稳定存在。简言之,ANT的超越性就在于,它摆脱了西方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与二元论框架,把科学知识的生产理解为各种力量相互纠缠与缔合的动态过程,将研究对象转化为去中心化、关系化的网络,为理解科学的社会性提供了更为开放的视角。
7. 卡林·诺尔-塞蒂纳(Karin Knorr Cetina)

卡林·诺尔-塞蒂纳
卡林·诺尔-塞蒂纳,奥地利社会学家,因科学知识社会学、金融社会学研究闻名,其学术成果颇丰,其中,SSK方向的代表作为《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The Manufacture of Knowledge: An Essay on the Constructivist and Contextual Nature of Science,1981)。
在《制造知识》一书中,塞蒂纳的核心观点是: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建构性的,而非描述性的。建构的本质是特定与境下的选择,而选择又取决于科学家可以利用的资源和利益等等,即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部分科学家不断进行有目的的选择的过程,这中间必然受到机会主义、偶然性以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具体而言,科学知识在实验室里生产的过程中,科学家们根据现有资源,有意识地选择某些工具和方法,对科学对象进行商谈、施加或弃置,以便获取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有价值的资源。此外,科学解释、创新以及发展都是有目的的建构的过程,而科学研究的最终成果也是科学家在特定与境下依据几种等级选择性建构的结果,因此,科学在实践上的成功,更少依赖于规律本身,而是取决于科学家建构知识的能力。
再者,科学家一旦把与境性和有目的的选择转化成科学论文,也就意味着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非与境化了(或者说“重新与境化”)。因此,为了还原科学的与境性,塞蒂纳以知识生产的人类学研究为依据,深入伯克利(Berklee)的一所研究中心,走进实验室,开展为期一年的参与式观察,主要关注一项植物蛋白的研究,期间记录大量原始访谈材料,分析得出结论。她发现,科学论文并非实验事实的描述,而是对实验室的一种建构。一方面,科学论文是一种选择性事实呈现或解释,为服从领域内的权威,往往有意掩饰实验过程中的诸多细节;另一方面,科学论文从初稿到终稿是作者与评论者多次商谈的过程,并且在书面表达时使用了大量文学策略,终稿呈现的结果可能早已与原实验事实相去甚远。此外,塞蒂纳还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对“两种科学”的划分进行批评。她认为,自然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与社会科学相似,同样受到与境性、社会境况及选择性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即二者的生产方式并无本质差别,该论证也再一次消弱了自然科学作为“特殊知识”的神圣地位。
8. 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

安德鲁·皮克林
安德鲁·皮克林,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拥有高能物理学博士学位(伦敦)和科学研究博士学位(爱丁堡),早期追随爱丁堡学派,受到“强纲领”的影响,后期转向实践哲学。皮克林早期成名作为《构建夸克——粒子物理学的社会学史》(Constructing Quarks:A Sociological History of Particle Physics,1984),该书既是讲述粒子物理学发展史的科学史著作,也是一部解构科学知识客观性的SSK经典文献。
皮克林聚焦于基本粒子物理学中“夸克”的发展历程:夸克[1]最早是美国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1929-2019)提出的理论模型(假说)。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夸克可以解释标度无关性现象,因此,科学家认为,夸克代表一种新物质层次上的基本实体,夸克模型逐渐被学界接受,盖尔曼也因相关贡献获得196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70年代,人们开始制定关于夸克的新理论。70年代后期,粒子物理学家们一致认为,基本粒子世界是由夸克和轻子相互作用主宰的世界。自1964年夸克概念首次被提出以来,尽管始终没有任何实验直接观测到孤立的夸克实体,但夸克物理却逐渐被物理学家接受,并在20世纪80年代全面统治高能物理学领域,皮克林对此给出的解释是“夸克实在是粒子物理学家实践的结果,而不是相反”。他认为,在高能物理学界,科学判断表现出群体一致性(social coherence),即夸克实体是高能物理学界全体人员通过共享研究资源而确立的,该群体拥有共同的社会意识,并由此组织社会实践,这样,最初的夸克假说就与其实在论意义上的性质等同,夸克概念彻底被建构起来,同时高能物理学家得以共享互惠成果。
后期,皮克林受到库恩以及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同时囿于SSK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他将研究的重心转向分析科学实践,如代表作《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The Mangle of Practice:Time ,Agency and Science,1995)。他的核心思想是:科学实践是多种力量的冲撞(mangle),也即他所说的“力量的舞蹈(dance of agency)”,指出科学知识生产是各种人类与物质的力量相互冲撞的结果,并且最终达到“调整与适应”。显然,他的这一思想与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也是一脉相承的。
结语:收缩的学术遗产与后SSK时代
科学知识社会学是20世纪后半页最具颠覆性的学术运动之一,它的兴起标志着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又一次深刻转向。本文梳理的学术谱系揭示了SSK内部的复杂与张力,从70年代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开始,到巴斯学派的经验纲领(EPOR),再到以拉图尔为首的实验室人类学研究,短短20年左右的时间里,SSK就完成了对传统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的双重超越,将科学知识引入哲学、社会学乃至人类学研究的视野,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科学知识稳定、独立、客观、权威的传统认知,有力揭示了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
SSK对科学研究的贡献是多维度的。首先,从认识论层面,它消解了“科学知识纯粹客观”的神话,将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同等看待;其次,方法论层面,它借助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语言学等多种理论工具,为理解科学研究提供新路径;再次,在具体实践层面,它关注实验室制度、科学论文发表、科学家职业生涯等现实问题,为科技政策制定、人才培养等提供重要参考。
然而,SSK自诞生之日起便一直遭受各种批评。其一,SSK理论(特别是早期的“强纲领”)带有强烈的相对主义色彩,主张无论真伪知识都应以相同的社会学方法加以解释,这种立场在解释科学知识社会性的同时,过于消弱知识自身的经验基础,模糊了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的边界;其二,SSK反对“两种科学”的划分、认为应该无偏见地对待所有知识的观点实际上走向另一个极端,科学制度、科学实践等方面显然不同于其他文化,理应区别讨论;其三,SSK过分强调科学知识的建构属性,或者说制造知识的利益导向,这不完全符合实际,科学史上很多重大突破并非功力之下的产物,而是与科学家自身对真理的渴望和无限追求密切相关。
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社会学领域的反映,SSK固有属性决定它始终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它完成了对科学知识的大胆解构,但是却无力建立起新的知识范式,人类思想史无数次证明,只有解构而没有建构的思想运动是走不远的,80年代末,SSK便逐渐退出科学研究的舞台。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思想历程,大浪淘沙过后总结其收缩的遗产,不难发现,从科学社会学到SSK,人类对知识生产的理解完成了从建制到内容的不可逆转变,它反映了一直隐而不显的外部主义开始登上舞台,这也是大科学时代知识生产的特殊性决定的。按照加拿大哲学家马里奥•邦格的说法,所谓外部主义论题是指,情境决定内容,甚或两者之间不存在差异,个体科学家的观念、程序和行动被其社会环境所决定,甚或后者构成了前者。
外部主义根据外部情境的影响程度可以分为温和的外部主义与激进的外部主义,温和的外部主义又可分为M1局域的:科学共同体影响其成员的工作;M2全局的:整个社会影响个体科学家的工作。激进的外部主义也可以分为两类,R1局域的:科学共同体散发或建构科学观念;R2全局的:整个社会散发或建构科学观念。如果粗略来说,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充其量属于温和的局域外部主义(建制对科学活动的影响),那么,SSK领域的众多学者则属于激进的全局外部主义者。大潮过后一切终归要回归平静,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开始站在更广阔的视角,尤其注重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非人类因素的作用(物的能动性),如拉图尔等人建立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安德鲁·皮克林也由原来的科学知识转向科学实践研究,探讨科学、技术与社会综合而又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即科学技术论(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笔者称之为“后SSK时代”。但这不意味着SSK学术遗产已经过时,在宏观社会认知层面它所激发的解放性与破除神话功能仍是我们人类在面对知识时保持开放心态的重要思想源泉;在微观实践层面它所揭示的对称性、反身性原则,仍为我们反思自身的知识生产提供重要启示。只是,单纯依赖社会建构论的分析框架,已经不足以应对当代科学技术的复杂性。我们亟需开创一种新的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综合性理论,对于这份时代的邀约笔者充满信心,毕竟在旧理论的废墟上,新理论总会破土而出。
作者简介:
李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尹辉,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硕士生。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默顿. 科学社会学: 理论与经验研究[M]. 林聚任,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2] 巴里·巴恩斯. 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M]. 鲁旭东,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3] 大卫·布鲁尔. 知识和社会意象[M]. 霍桂桓,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4] 迈克尔·马尔凯. 科学与知识社会学[M]. 林聚任, 等,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5] 哈里·柯林斯. 改变秩序: 科学实践中的复制与归纳[M]. 成素梅, 张帆, 译.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7.
[6] 卡林·诺尔-塞蒂纳. 制造知识: 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M]. 王善博, 等,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7] 卡尔·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 姚仁权,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8] 布鲁诺·拉图尔, 史蒂夫·伍尔加. 实验室生活: 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M]. 张伯霖, 刁小英,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4.
[9] 安德鲁·皮克林. 构建夸克——粒子物理学的社会学史[M]. 王文浩, 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
[10] 安德鲁·皮克林. 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M]. 刑冬梅,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1] 史蒂文·夏平, 西蒙·谢弗. 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玻意耳与实验生活[M]. 蔡佩君,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12] 安德鲁·皮克林编. 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M]. 柯文, 伊梅,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13]马里奥•邦格。哲学与社会学的联系[M].董杰旻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24.
科学知识社会学核心人物一览表
人物 | 生卒年 | 研究方向 | 代表作 |
大卫·布鲁尔 | 1942— | 社会学、哲学 | 《知识与社会意向》 |
巴里·巴恩斯 | 1943— | 社会学 | 《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局外人看科学》 |
史蒂文·夏平 | 1943— | 科学史 | 《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玻意耳与实验生活》 |
迈克尔·马尔凯 | 1936— | 社会学 | 《科学与知识社会学》 |
哈里·柯林斯 | 1943— | 社会学、哲学、引力波、人工智能 | 《改变秩序:科学实践中的复制与归纳》 |
布鲁诺·拉图尔 | 1947—2022 | 哲学、人类学、社会学 | 《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 《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 |
史蒂夫·伍尔加 | 1950— | 社会学 | 《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 |
卡林·诺尔-塞蒂纳 | 1944— | 经济社会学、科学社会学、文化社会学 | 《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 |
安德鲁·皮克林 | 1948— | 科学史、哲学、社会学 | 《构建夸克——粒子物理学的社会学史》 《实践的冲撞——实践、力量与科学》 |
[1] “夸克”一词取自于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一首长诗。
【博主跋】这篇文章是我和尹辉同学关于科学社会学系列的第二篇文章,前几日编辑游老师来信提到校对中的几个小问题,由于文章篇幅较长,这篇文章分上下两部分发,上部发在《世界科学》2026(2)期上,上部截至到第五号人物柯林斯,估计应该出版了,下期继续!争取把关于科学知识的这个三部曲写完,与游老师合作愉快,是为记!今日是除夕,过了今夜就是马年了,重要的日子总要留下一点痕迹,贴一篇文章以示纪念!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2026-16凌晨于南方临屏涂鸦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李侠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wap.sciencenet.cn/blog-829-1522458.html?mobile=1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