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选
精选

从“大教堂”式研究到“预制房”式研究
——科学精神蜕变中的科研文化
叶菲楠 李侠
(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对科学精神进行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认识论层面的概念分析阶段,而应回到在科学精神的引领下对主体行为的分析上,否则我们无法看到一种内隐的理念对于个体世界观的改变以及对于个体实践模式的塑造。换言之,坚持或信奉科学精神一定会在实践层面有所表征,并给个体真实生活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尤其是伴随着近代市场经济的兴起,科学精神的信奉者一定会基于该理念而得到实质性的(有形或无形的)回报或收益,并进行计算,然后做出调整或新的选择,否则,科学精神是无法传播更远或被更广泛的人所普遍接受的。为此,我们不妨看看国外学者对此类趋势的研究现状。
纵观国外学术界关于对科学精神和科学行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科学精神与科学行为之间呈现出双向建构的关系:科学精神规范主体的科学行为,科学行为反过来又影响科学精神的重建。
在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科学狂飙时代中,“科学精神”的概念经过众多科学家的实践与修正,其内涵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充。1892年,英国科学家皮尔逊(Karl Pearson,1857-1936)率先在他的科学哲学名著《科学的规范》中分析了科学的一些特质和精神要素,如普遍性、客观性、实证性、合理性、怀疑性、简单性、审美性、一致性、进步性、公有性、公正性、为善性等。他将其提升并称之为科学精神。【1】信奉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家艾耶尔(Ayer)等人把科学的事实判断与伦理分开,主张伦理只是一种情感表达,而没有意义。1942年,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2003)突破了逻辑实证主义的事实/伦理的二分,首次提出科学的精神气质(ethos of science)的四条原则,也就是被后世广为称道的“默顿规范”。它们分别是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后来又加上了独创性。【2】科学评价的普遍性强调依据客观标准,而非个人特质;公有性主张科学知识应归于公共领域;无私利性要求科学家在研究中排除私人利益的干扰;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提倡系统性的批判;独创性原则规定科学发现必须具有创新性。到了默顿这里,科学才从价值中立到了价值承认,这是一次认识上的突破,之后又演变出科学的内部主义和外部主义,前者认为科学进步依赖认知价值(如解释力、简洁性),外部伦理仅影响目标选择;后者强调科学受社会、经济和政治语境的塑造(以SSK为代表的建构主义),比如,生物技术伦理需考虑环境与社会公平等。
1954年,保罗·伯克霍尔德(Paul R. Burkholder,1903-1972)认为,真正的科学精神应该激发人们为了知识本身而追求知识,而不仅仅是为了物质利益。除了求真,科学应该还要有美学价值。【3】1956年,布鲁诺乌斯基(Jacob Bronowski,1908-1974)在《科学和人的价值》(Science and Human Values)中强调,科学追求真理,将其视为终极价值和目标。在观察和思考过程中,追求真理者需保持独立,社会亦应维护其独立性。科学界需要异议和自由;为了科学的持续发展,应将历史研究与未来探索相结合,而宽容则是必不可少的。【4】传统的科学观是线性渐进的,并不断趋近真理,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范式理论为解释科学精神提供了新的见解。【5】他认为科学发展是不同范式的更迭,科学革命是对旧理论的抛弃,新理论的接受,科学共同体接受了一个新的共同纲领或研究范式。所以科学精神应是对真理的追求和对新知的开放,这对应着默顿的第四条(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和第五条原则(独创性)。
在真实的研究环境中,科学家的行为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分布式认知理论提出,实验室是一个“认知-文化系统”,科学家的行为会受到共享工具、符号系统和集体实践的影响。哈佛大学的认知科学家南希·内尔塞西安(Nancy J. Nersessian)引用克拉克的“延展心智”理论,强调实验室环境本身就是认知系统的一部分。【6】在实验室中,科学家使用计算机模型可视化神经元网络,开发了新的符号系统CAT——活动轨迹中心来形成共享心智模型。而每周例会、跨学科的讨论以及在维基百科上的协作都是实验室的集体实践,科学家们可以随时调整研究目标、思路设计,彼此之间形成一个如同棘轮的认知系统。
那么科学精神能否一如既往地规范科学行为?到了21世纪,科学界的科研文化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变化,科学精神出现了异化。切尔尼科娃(Chernikova)认为如今的科学伦理已经从古典科学伦理转向技术科学伦理。古典科学的学科边界清晰,主要追求对自然规律与理论的发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分离。技术科学则跨学科融合,如NBIC(纳米-生物-信息-认知)技术群,研究对象从古典时期的外界客观事物转变为人类自身的增强技术或人工智能。技术科学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融合,从解释世界转向改造世界,最重要的是,技术本身不再是中立的,而是价值负载的。【7】
在基金、竞争、评奖等多种压力下,学者的科学行为并不总是遵循科学精神。加拿大科学家丹尼尔•布克曼(Daniel Z. Buchman)等人研究了在加拿大大麻合法化的背景下,科学家由于接受产业资助而陷入道德困境,商业逻辑在实践层面对默顿规范中的“无私利性”原则造成了严重挑战。政府对科研的资助不足,科学家转向求助产业资助,而产业的出资方最终会主导研究方向,从而损害学术的公信力。【8】
麦尔曼(Meirmans)探讨了激烈竞争的基金制度如何塑造了科研实践活动。由于基金评审要参照以往的学术成果,研究者变得回避创新,而穿上了“学科紧身衣”开始做渐进性研究。尤其在人文社科领域,三到五年的短期项目制迫使学者放弃需长期积累的“大教堂”(cathedrals)式研究,学界普遍追求短平快的“预制房”(pre-fab house)式研究。研究规划本身可能需十年甚至更长,涉及长期数据的积累,但项目制的时间限制让学者只能做“短期可交付的成果”(short-term deliverables)。迫于短期成果压力,学术研究无论是在研究问题、思路还是方法上都变得保守且可预测。资助体系鼓励研究者采取小步前进而非高风险创新的策略,“人人都在跳相同的圈,科研多样性被削弱”。当前科研资助体系的核心矛盾变成了:项目制评价标准(如短期产出、确定性成果)与研究本质需求(长期投入、探索性创新)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从而形成了预制房式研究的规模化生产学术的现象。文科跨学科的评审常因为非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而被评审拒斥,导致学术不公。所谓的大型项目合作则常常流于形式,效率低下。麦尔曼发现,基金竞争的程度越高(中标率越低),政策干预越大,研究者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就越差(有理由推测,其成果的创新性也越差)。对此,笔者不禁想到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它始建于1248年,直至1880年才由威廉一世宣告完工,历时632年,这才造就它的恢宏与壮观,试问如果采用当下的“预制房”模式来建造,还能建造出这样的奇迹吗?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崔教授(Anne S. Tsui)总结出如今科研文化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如下几种:其一,学术与实践脱节,研究者追求论文发表的数量和速度(“计数文化”),忽视对实践的价值。其二,经验资深的学者逐年积累学术资本后,学术发表更加容易,产生了“赢者通吃”文化,反过来促使经验尚浅的学者以忽视科学精神的方式生产学术成果,比如篡改数据等。如Summerlin的伪造数据、哈佛研究者Darsee篡改实验结果,都反映出制度性激励(名利竞争)对科学诚信的侵蚀。【9】贝德安(Bedeian)等学者发现超半数教师目睹此类行为。【10】其三,全球盲目追求北美的期刊标准,理论创新停滞。崔教授将科学精神归纳为三个核心:追求真理(通过严谨方法逼近现实);改善人类生存(如爱因斯坦所言,科学应使普通人生活更好);研究自主性(免受商业排名干扰)。【11】而以上三个问题已经背离这些核心旨趣,也就是在实践层面背离了科学精神。
这些新的科学行为,虽然背离了传统默顿规范所指涉的科学精神,但也催生了新的价值观。杰奎琳(Jacqueline Dalziell)在对澳大利亚合成生物学的定性研究中发现,合成生物学家日常面临的伦理困境(如产业压力、性别不平等)会反向塑造其科学理念。【12】研究者面临着短期合约压力,会选择更容易出成果的保守课题;成果剽窃、数据作假频发,女性研究者受到不公正对待,大量塑料耗材的浪费,都是在实践层面上的伦理冲突。正如他们提出的良心拷问:“当科学家为下一份合同忧心时,他们如何能安心思考技术的社会影响?”所以他们形成了一种新的“实用主义伦理观”,意在努力适应这种科研困境和诚信危机。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哲学家约纳斯(Hans Jonas,1903-1993)就提出了应对技术科学伦理的责任伦理。默顿规范只是针对科学家的即时行为,但无法应对科技带来的长远、系统的风险。基因编辑、原子能等技术不仅影响当代人,还会影响人类后世许多代,且后果无法控制、不可逆,所以科学家也必须要考虑未来人类的利益。【13】西班牙社会学家瓦莱罗(Valero Matas)也赞同这一点,默顿规范是一个理想的、普适的价值体系,但如今各学科发展迅速,互相之间也未产生共识(学科间与学科内),建立一个新的伦理体系迫在眉睫。新的伦理体系要分为核心层和外围层,核心层是普适的默顿规范(公正、不伤害、追求真理等),外围层则根据不同学科的特性,制定特殊的规范,比如生物医学伦理协议,这样就能形成弹性治理框架。瓦莱罗呼吁,科学伦理要超越旧的默顿规范,让科学家参与社会实践,进行跨学科协作,不仅要追求真理,还要将责任伦理内化在研究中。【9】崔提出要建设社会责任型学术(Socially Responsible Scholarship),包含“三优先”框架(平衡利益、语境敏感、伦理至上)。在行动上, 年轻学者选择有社会意义的研究问题,而不是追随计数文化;资深学者支持创新研究,而不是亦步亦趋前人的固有研究;院校改革“数量优先”的评价体系;期刊把实践的相关性也纳入审稿标准,而不是选择与实际脱节的论文。崔的社会责任型学术得到了切尔尼科娃(I Chernikova)的支持。切尔尼科娃也赞同科技伦理从封闭学术规范向开放社会责任转型。【14】默顿的规范是让科学家内化的价值观,依靠科学家内心的道德秩序来规范自身,但仅凭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具体在运动科学领域,阿罗拉(Nitin Kumar Arora)梳理了运动科学研究的伦理规范与方法学挑战,提出通过健全的试验设计和伦理审查框架来减少学术不端,并呼吁建立“健康与运动研究誓言”(HERO)以提升行业标准。运动科学领域存在隐瞒兴奋剂副作用,学者重复投稿,只筛选阳性数据导致证据偏差等科学行为失范的问题。HERO誓言就是要求研究者:坚守“道德指南针”,抵制发表压力导致的学术不端;承诺遵循最高伦理标准(如《赫尔辛基宣言》和GCP准则),确保证据的可解释性与社会信任;通过机构监督(如伦理委员会)和同行评审形成约束机制。如此才能将行业规范内化在研究者心中,把伦理准则转化为实践规范。【15】
总而言之,国外学者关于科学精神的研究多集中在科学行为失范、建立新的科学伦理方面,涵盖了运动科学、生物医学、通信技术等各个学科的领域。可以清晰地看到,尽管默顿规范等经典理论为科学精神提供了重要基础框架,但在当代科技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科学行为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对科学精神的内涵提出了新的挑战。虽然科学精神仍是科学家或研究者内心的道德指南针,但他们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经济、政治、个人价值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建立新的以责任伦理为中心的科学精神,已成为国外学界关于科研文化的核心议题。

参考文献:
【1】皮尔逊. 科学的规范[M]. 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9-11.
【2】Merton R K. 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science[M]//Merton R K, ed.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3】Burkholder P R. The spirit of science[J]. The Georgia Review, 1954, 8(4): 373-382.
【4】Bronowski J. Science and human values[M]. New York: Julian Messner Inc, 1956: 35, 83, 86-87, 88-89.
【5】Kuhn, T.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1962.
【6】Nersessian N J. Research labs as distributed cognitive-cultural systems[J]. European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24, 14(4). https://doi.org/10.1007/s13194-024-00618-0.
【7】Lektorsky V A. Rationality, social technologies and human destiny[J]. Epistem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11, 29(3): 35-48.;Shvyrev V 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and projective-constructive functions in classical and modern science[M]//Knowledge, understanding, design. Moscow: IP RAS, 2008: 30-48.
【8】Buchman D Z, Magel B, Shier R, et al. Canadian cannabis researcher perspectives on the conduct and sponsorship of scientific research by the for-profit cannabis industry[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25, 364: 117556. https://doi.org/10.1016/j.socscimed.2024.117556.
【9】Valero Matas J A, Romay Coca J, Miranda Castañeda S. Scientific behaviour: values and epistemology[J]. Acta Scientiarum.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s, 2011, 33(1): 21-31. https://doi.org/10.4025/actascihumansoc.v33i1.10752。
【10】Bedeian A G, Taylor S G, Miller A N. Management science on the credibility bubble: Cardinal sins and various misdemeanor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 2010, 9(4): 715-725. https://doi.org/10.5465/AMLE.2010.56659889。
【11】Tsui A S. The spirit of science and socially responsible scholarship[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13, 9(3): 375-394. https://doi.org/10.1111/more.12035.
【12】Dalziell J, Rogers W. Scientists’ views on the ethics, promises and practices of synthetic biology: A qualitative study of Australian scientific practice[J]. Science & Engineering Ethics, 2023, 29(6): 1-20. https://doi.org/10.1007/s11948-023-00461-1.
【13】Jonas H. Principio de responsabilidad[M]. Barcelona: Herder, 1979.
【14】Chernikova I, Bukina E. From the classical science ethos to the techno scientific one[J]. IOP Conference Series: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20, 953(1): 012044. https://doi.org/10.1088/1757-899X/953/1/012044.
【15】Arora N K, Roehrken G, Crumbach S, et al. Good scientific practice and ethics in sports and exercise science: A brief and comprehensive hands-on appraisal for sports research[J]. Sports (Basel), 2023, 11(2): 47. https://doi.org/10.3390/sports11020047
作者简介:
(叶菲楠、李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博士生与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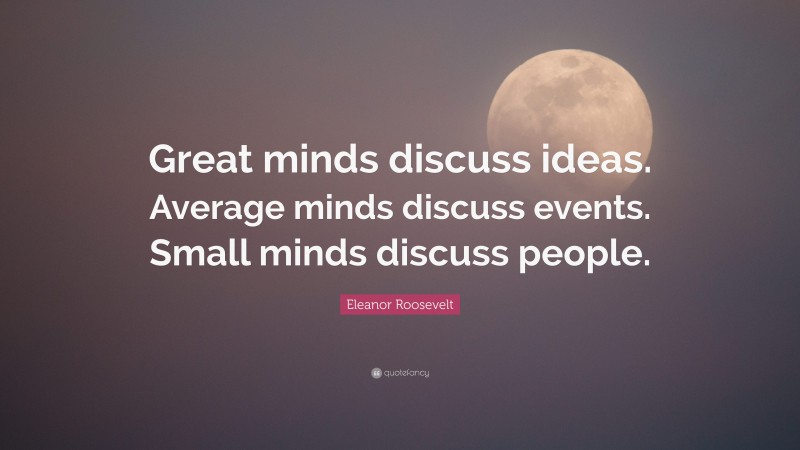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是前些日子写的,主要是想看看国外学者关于科学精神都在关注啥,现发在2025-7-23日的《三思派》微信公众号上,与李辉博士、张老师合作愉快,是为记!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路,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2025-7-23于办公室临屏涂鸦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李侠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wap.sciencenet.cn/blog-829-1494915.html?mobile=1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