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上生 守护经典文本的历史形态——《红楼梦》文本“修订说”质疑
黄安年 推荐 黄安年的博客/2025年7月16日发布/36982篇
【按:刘上生先生的文章《守护经典文本的历史形态——《红楼梦》文本‘修订说’质疑》在7月15日《红楼梦学刊》公众号发布后,引发学界广泛关注,昨天上午通过微信直接转发来的就有俞晓红、刘上生、石中琪、陈熙中等学人。熙中教授专门提及“您博客可转发”并引述“一个人的跟贴”称“终于见到一篇理性评价的石校本《红楼梦》的文章”。我问刘先生“与上次稿(指7月3日他发来的同名文章)有无变动之处”,他答复“加了一点,特别是敬圻先生论父子关系的高论。”
记得四年前的2021年 6月。吕启祥在人文社《红楼梦》新校注本第四版修订开始之际,初步完成有关新校注本的口述资料时写道:回忆文稿中提出经过四十年的实践,我们的新校本要更符合曹雪芹原著,更趋完善和精准,是为“补天”工程而非重另起炉灶;要兼顾可读、语境、研究的需求;要充分吸纳海内外研究成果;要实行吸纳各方研究成果的可持续出版运行机制。
(吕启祥忆《红楼梦》新校注本第四版修订(2021年6月)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5年7月13日发布,第36963篇)
吕启祥在写于2022年7月暑伏天中的“来之不易 来日方长----《红楼梦》新校本四十周年”一文中写道:
注释方面,提升的空间更大。《红楼梦》素有百科全书之喻,我们的闻见不广,知识储备不足,许多不同意见只能暂时搁置,不敢擅改,以待高明。
当然,期待变为现实,需要有可持续的运行机制来保障,做到确保相对稳定的专家和出版社编辑精诚合作、吸纳最新研究成果,不断完善校注,使出版的《红楼梦》更加接近曹雪芹原著、更加有利于文字择优也更加吸引最广大的读者。
来日可期,我们盼望新的更完善的校注本的出现。
(吕启祥著:《一份缘--我的师友亲人们》(2024年中国红楼梦学会出品)
感谢刘上生先生同意我在科学网博客上转发并寄来他的近照。

**************************
原创 刘上生 红楼梦学刊
2025年07月15日 07:31 山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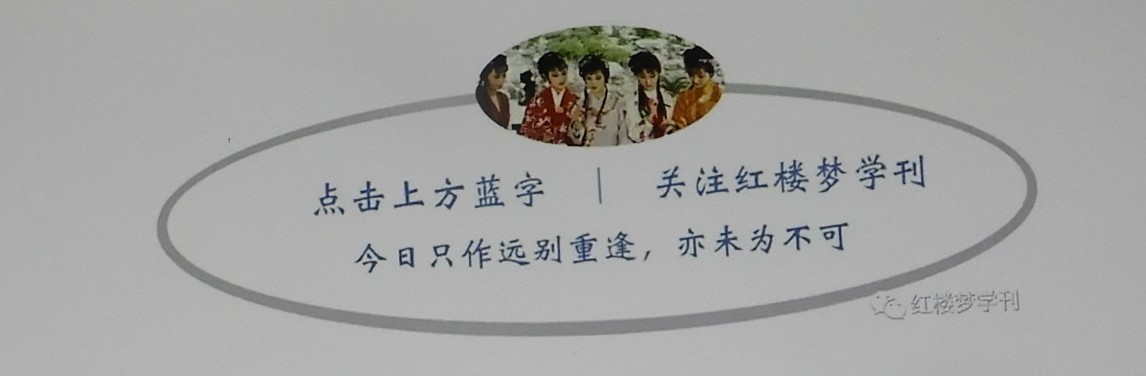
内容提要:“修订说”为了造势,着意夸大渲染《红楼梦》文本的“问题”及“危险”,贬低甚至否定现有文本,特别是红研所本,这是完全错误的。“修订”的主观性极易导致对经典文本和作家的伤害,特别是前八十回。修订者的个人探索应该尊重,但为红学百年大计,必须坚持红研所本尊重历史尊重作者守护经典文本历史形态的正确方向,保持《红楼梦》文本稳定完善,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
一
最近,石问之(李应利)先生的校订本《红楼梦》(以下简称石校本)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是红学界一件引人注意的事件。张庆善先生作序称道“石问之是近年来红楼梦研究中崭露头角的卓有成就的学者。”他的《玉石之间》《见微知著》等著作,我都拜读过,很钦佩他的精细功夫和缜密思维,也给我不少启发。收到石校本后,我认真读了前言和一些部分。因为年老目衰,未能细读,没有资格写书评。但有一个认识大概是符合实际的。就是石校本名曰“校订”,其实是“修订”《红楼梦》。校订本《前言》(以下简称《前言》)已经宣称:“本次对《红楼梦》的修订是全面的系统性的修订。”《前言》实际上就是作者“修订说”的认知和操作宣示。
石问之是一位认真执着的学者。他的校订本有自己的特色。由于“修订”,给人新鲜感。作为一种探索,石校本自有其存在意义。正如《前言》所说,“能出现《红楼梦》脂评本、程高本、程晋本、修订本、续写本等同时并存,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这对红学事业的发展其实是大有好处的。”从这个方面说,浙江古籍出版社推出石校本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当然,既然作为一种文本推出,学界、大众、市场和历史都将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前言》很善于造势,为了使修订变得合理,一开始很尖锐地指出“在四大名著之中,《红楼梦》也是文本问题最严重的一部。”以下罗列诸如人物年龄混乱、时序混乱、情节自相矛盾、叙事或断档或突兀等众多问题,“至于‘五次增删’对文本造成的冲击,更是遍布前八十回之中”,以及后四十回的严重问题等等。再述及版本问题,从程高本到混合本:“程高本因其前八十回失真严重,日渐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抛弃,各种混合本的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又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两张皮的状态,且后四十回也面临日渐被读者抛弃的危险”,“以一百二十回的整体形象存在了二百多年的《红楼梦》面临着实实在在被割裂的巨大危险”……由此,他为自己确定了“将混合本的初阶混合水平提升到高阶混合水平,从简单的拼配状态提升到真正的融合状态”的修订目标。
《前言》强调文本修订的意义,“既要着眼于现在,也要着眼于未来,不仅要着眼于国内,还要放眼世界”,为此一再贬斥现有《红楼梦》文本:“一个处处充满矛盾的文本,与整本书阅读的要求显得有些不大相称”,“一个充满着矛盾的文本,显然不利于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公允评价和广泛接受”,“从有利于文化交流互鉴的角度看,我们也应当将《红楼梦》文本的修订工作尽早提上日程。这是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我们要不辱使命。”这些“高大上”的语言给人一种印象和压力:《红楼梦》文本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影响其传播、接受和国际声誉的大局了。
笔者很佩服这种“睥睨前人”的气概和“舍我其谁”的勇气,但不能同意这种对《红楼梦》文本(版本是其存在形态)“问题”和“危险”的不合实际的描述。笔者此文,仅就《前言》关于“修正说”的一些观点提出质疑。
 二
二
笔者的疑虑主要有两点:一是《红楼梦》的文本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应该怎样评价现有文本?二是,已经成为经典历史形态的《红楼梦》文本,是否需要后人修订?“修订”是不是守护存在“问题”的经典历史文本的正确方向?
笔者认为,《前言》为了达到为修订《红楼梦》造势的目的,有意夸大了《红楼梦》的文本问题。这不符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学术要求。
《红楼梦》的文本问题是否严重,应该包含两个基本点:一是它在《红楼梦》整体文本中所占分量,二是它对《红楼梦》的阅读、传播、研究乃至国际声誉的影响。当然,这里还有一个视点的问题,同样一个事物,在正常视力观照与显微镜放大镜下的观察结果是不一样的。在显微放大镜下,绝代佳人也会变得无法接受。
《红楼梦》的文本问题,究竟是如《前言》所言那么严重,“处处充满矛盾”,还是并不影响整体阅读和接受的“小疵微瘆”?老实说,无论从量的角度还是质的角度,我都得不出作者的结论。这不但是《红楼梦》巨大思想和艺术魅力的遮蔽,也是除极少数研究者之外绝大多数阅读者的共同体验。《前言》所列举的人物年龄混乱等诸多问题“究竟在全书中占多大比重?”诚然,“仅仅是一次秦可卿故事的改写,在书中就产生了众多文本自相矛盾的问题”,但谁都知道,秦氏故事是特例,其他《风月宝鉴》旧稿故事掺入,于整体影响并不大。①至于说“‘五次增删’对文本造成的冲击,更是遍布前八十回之中”,这话就很夸张了。什么冲击?遍布了多少?石先生的著作中也没有这样阐述过。这些话,总给人一种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过甚其词”的感觉。
《红楼梦》的文本不是空中楼阁,它是依附于一定的版本形态存在的。在《红楼梦》二百余年传播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文本无疑是两种:一是程高本,二是被称为混合本的红研所校注本,简称“红研所本”。笔者很想弄清《前言》所说“处处充满矛盾”的问题“严重”到影响《红楼梦》接受和国际声誉的究竟是哪一种版本?
《红楼梦》的文本问题是否严重,这不是谁说了算的事情,《红楼梦》接受和传播的历史与现状已经做出了回答。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程高本和红研所本在不同历史时代都做出了贡献。程高本的时间更长。可以说,《红楼梦》的经典化、大众化、国际化都是在程高本时代完成或开始实现的。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一百二十回程高本结束了《红楼梦》文本抄写时代的动态化过程,将近二百年独领风骚,成为“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经典;成为王国维、胡适、鲁迅等开创近现代红学的版本依托;成为建国以来普及亿万民众的版本依托;成为何其芳、蒋和森、吴组缃等一大批前辈学者研究和培养后人成为红学中流砥柱的版本依托;成为海外汉学家研究和《红楼梦》赢得世界性国际声誉的基本版本依托,等等。当伟人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称为历史中国在世界的“骄傲”时,他当时用的是程高本。程高本能说是“处处充满矛盾”的“文本问题严重”的《红楼梦》文本吗?当然不能这样说。石校本也引用了俞平伯晚年自认腰斩“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的话。只是因为后出的红研所本更为接近曹雪芹原稿的优势,程高本有所边缘化,但在学界仍有巨大影响,北师大启功注释程甲本,特别是张俊、沈治钧《新批校注红楼梦》等,仍有极高声誉。《前言》说程高本被“日渐抛弃”完全是危言耸听。
三
那么,石校本所谓“处处充满矛盾”的“文本问题严重”的《红楼梦》文本何所指呢?是混合本亦即红研所本吗?
红研所本是《红楼梦》版本史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吸收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陆续发现的脂本系统文本及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等一大批版本学家的研究成果,使前八十回的版本选择和整理尽可能接近作者曹雪芹生前定稿原貌,但又没有否定后四十回程高本的历史形态。可以说,红研所本基本完成了《红楼梦》的经典历史形态的定型,它哺育了并将继续哺育新时期的红学人和亿万大众,是新时期红学最重要成果之一。
红研所本能够取得如此成就,是冯其庸等老一代红学家积聚红学历史成果与集体智慧,呕心沥血,长期努力的结果,也是与他们能遵循保护经典历史文本的正确方向分不开的。这种尊重作者尊重原著的严谨的学术态度在其《校注凡例》中有鲜明体现,并付诸实践。诸如谨慎选择时代较晚保存较完整比较接近曹雪芹前八十回定稿原著的庚辰本为底本,以各脂评本、抄本及程甲乙本为参校本,“底本与各参校本之异文,凡属底本明显的衍夺讹舛者,据参校本增删改之,凡校改底本之处,择要作出校记;凡底本文字可通者,悉仍其旧。”至于文字改易,只有一种情况:“底本文字明显错误,各脂本沿袭其误,此类情况,即径改之,并作校记说明。”这类文字错误,有的可能是抄写错误,如第四十五回“走一趟”,底本原文为“走一淌”(611页);第五十一回“娇嫩”,原误为“蛟嫩”(700页)等。有的则可能是引用出处错误,如第十七八回,宝玉不知“绿蜡”出处,宝钗告诉他,出唐钱珝咏芭蕉诗头一句“冷烛无烟绿蜡干”,“校记”指出:底本“‘钱翊’为‘钱珝’之误,……唐人韦縠选编的《才调集》卷一误作‘钱翊’……抄本均误作‘钱翊’,今改。”(251-252页)说明了原文错误发生的原因,体现了不妄改一字的严谨态度。对后四十回,红研所本选择了程甲本,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程甲本底本来源于脂本系统,而程乙本对前八十回做了许多背离作家本意的不当修改。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走近曹雪芹,守护《红楼梦》经典文本的历史形态。
由于红研所本的学术性和权威性,它已经取代程本成为新的学界通用本和市场流行本。红研所本的方向也奠定了《红楼梦》版本整理的正确方向。红研所本没有掩饰也没有修改《红楼梦》文本中诸如年龄时序等存在的问题,甚至明显可见的错误,也依原文。如第二回冷子兴叙说王夫人大年初一生育元春后,“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说来更奇”,即衔玉而生的贾宝玉。姐弟相差仅一岁,与后文完全不符。究竟是冷子兴口述有误,还是他所听传闻有误?把文本问题交给读者和研究者去思考解答,使后人能够面对真实的历史文本,而不是被改造的“伪文本”。
红研所本也有引起争议和待改进的问题。当年冯其庸先生选择庚辰本作为底本,除了认为庚辰本定稿较晚,更接近曹雪芹原稿之外,也因庚辰本保存七十八回,较为完整。但他们也尽量吸收了其他版本的优点,完善底本。应该说,这是一种减少争议,较易取得共识的做法。但学界对庚辰本与甲戌本抄本的年代定位,仍有争议,《周汝昌批点校订本石头记》就较多采用甲戌本原文,有的择优拼合各脂本,如《蔡义江新批红楼梦》。至于具体字句的校勘,也有可议之处,石校本第三回把庚辰本的“方下来”改为杨藏本的“放下来”(0036页),就是好例子。《葬花吟》红研所本舍庚辰本的‘“一堆净土”,而取程本的“一抔净土”,不符底本取舍原则,笔者也已提出异议。②但不论还有多少缺点,红研所本守护经典文本历史形态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从实践效果看,学界(包括海外学者)和大众都是欢迎和肯定的,至今印数超千万册,毫无愧色地成为“整本书阅读”和《红楼梦》国际传播的经典文本。人们理解文本的不完美和缺陷。至于所谓“两张皮“即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存在矛盾不能统一的问题,读者都知道,是因”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所致,这是任何人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前言》对“混合本”的批评,甚于程高本。因为程高本已经近二百年考验。而“混合本”行世未久。《前言》将其称之为“初阶混合水平”、“简单的拼配状态”,红学所前辈们数年数十年的心血就只不过换来了“初阶混合水平”、“处处充满矛盾”、“问题严重”的文本评价。不仅于此,从《前言》所叙可知,红研所本前八十回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构架也被石校本推翻,成为甲戌、乙卯、庚辰拼配为底本其他为参校本的格局。如此一来,石校本的所谓“全面的系统性的修订”实际上意味着对红研所本的全面否定。冯其庸等老一辈红学家在天之灵,会作何感慨?石校本自陈用功九年,冯其庸等前辈可是潜心研究了一辈子,为红研所本贡献了数十年才有我们今天后人享受的成果,怎能如此贬低甚至否定?张庆善老会长曾经多少次不遗余力地宣传红研所本的优长,宣传红研所本体现的当代学术水平,③《前言》对混合本的评论,与老会长所论大相径庭。如果混合本果真处于“初阶混合水平”,需要“修订本”将其提到“真正的融合状态”的“高阶混合水平”,还要重定版本底本,来一个自我否定和重建,那可是一件将引起巨大学术争议和动荡的事情啊!
总之,笔者认为,《红楼梦》文本虽然存在问题,但二百余年的接受传播史证明,程高本和红研所本是基本适应经典化、大众化、国际化的历史和现实要求的,并不存在被抛弃否定的“危险”。孙伟科会长在中国红楼梦学会2024年年会致辞指出:
“当代红学是红学历史中的黄金期。因为自这部经典产生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多的读者喜欢《红楼梦》,精读《红楼梦》,深研《红楼梦》,空前的学者队伍和民间学者、爱好者团体,形成了当代红学的超文化现象。……”④
毫无疑问,致辞所说的读者“喜欢、精读、深研”的《红楼梦》文本,主要就是近四十余年来广泛普及的红研所本,这是对《红楼梦》经典文本形态业已完成的明确肯定。正因为如此,致辞把“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作为“当代红学发展的时代主题”。这是完全正确而富有远见的。
令人遗憾的是,《前言》为了为“修正说”张目造势,不公正地贬责现有文本,宣扬《红楼梦》文本的“问题严重”,“充满矛盾”甚至存在“危险”。这当然令人无法接受。笔者认为,为红学健康发展和百年大计计,《红楼梦》的文本应该稳定完善,红研所本应该坚持守护经典的历史文本,维护前辈的红学成果,这是人心所向。
本来,立意“修订”《红楼梦》是一件个人的事,谁也无权干预。无论如何,为红学献身都是崇高的事业。但把问题提到如此“高大上”,涉及红学史甚至《红楼梦》的未来。这就使普通红学人也有所感奋了。笔者愿意“高大上”地说一句:守护还是“修订”改造经典文本的历史形态,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个方向问题,是一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向问题。
四
同样一个问题,人们认识角度和水平不同,可能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结论。《红楼梦》的文本问题是一个客观事实,仅其所谓年龄时序错误,就议论已久。沈治钧《红楼梦成书研究》有专章探讨,并修改周汝昌《红楼纪历》专列《新编红楼纪历》一节。⑤《红楼梦》年龄问题,以沈著所列最详,从成书角度分析也最透彻。然而沈先生从未提过要“修订“,他尊重原著。从成书和传抄过程两个方面分析原因,已是学界的共识。但很少有人从曹雪芹作为伟大作家的独特时间观念和叙时艺术的角度去深入探讨,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上世纪九十年代,王蒙先生就以文学家的独特敏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在《红楼启示录》中首次阐述了他称为时间模糊化的“红楼梦现象”,指出:
但《红楼梦》里的时间,却是相当模糊的。首先,全书开宗明义,第一章已反复说明“无朝代年纪可考”,在时间的坐标系上,失去了自己的确定的位置。其次,各章回极少用清晰的语言表明时间顺序与时间距离。……
在《红楼梦》中,确定的时间与不确定的时间,明晰的时间与模糊的时间,瞬间与永恒,过去、现在与未来,实在的时间与消亡了的时间,这些因素是这样难解难分地共生在一起,缠绕在一起,躁动在一起.《红楼梦》的阅读几乎给了读者以可能的对于时间的全部感受与全部解释。在《红楼梦》中,时间是流动的,可变的,无限的参照却又是具体分明的现实。⑥
作为文学家的王蒙与曹雪芹是真正的隔代知音。因为他不是从一般的生活逻辑或写实逻辑而是从艺术创造的视角去认识《红楼梦》与曹雪芹。笔者近年提出曹雪芹的“大时间观”并研究曹雪芹的叙时艺术也是受此启发。换一个角度思考,认识就大不相同。曹雪芹一再强调他的作品“无朝代年纪可考”,明显有阅读导引意图,读者却抓住年龄问题不放,还视为“致命性痼疾”,要加以“修订”,这未必是对作者的尊重。例如第四十五回林黛玉说“我长了今年十五岁”,把林黛玉的年龄提升了三岁,由于有庚辰批语,可以肯定是曹雪芹的手笔,至第四十九回又特别用群钗“皆不过十五六七岁”相呼应。但石校本就因为与第二十五回贾宝玉十三岁年龄线相矛盾,擅自删去这两处年龄提升文字。表面看,似乎与宝玉十三岁年龄线实现了“和谐”,但这样一来,原来贾宝玉十三岁年龄线所遭遇的家族史叙事与青春梦叙事的矛盾就重新凸显出来了。这正是曹雪芹有意提升林黛玉年岁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弄清楚曹雪芹提升林黛玉年岁及群钗年龄的意图,也没有理解曹雪芹所创造的叙时双线手法,就贸然修改曹雪芹本人的文字,这至少是太莽撞了吧。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已经有专文论述了。⑦可见,即使要谈修订,也必须首先读懂《红楼梦》,理解曹雪芹,以一己之见妄改原文,恐怕不是走近曹雪芹,而是适得其反了。
五
由此想到“修订”的主观性问题。
自小说从世代累积进入个人写作时代以后,作品文本都是作家在一定历史语境下个体化个性化创造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人在当代语境下从自我感知出发的文本“修订”都是难以成功的。因为修订者的当代性和主观性必然成为回归历史和原作的障碍。
有学者精辟指出,版本校勘求真,文本修订求美,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范畴。求真比较容易取得共识,求美却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很难找到共同标准。读者对版本形态文本的要求是还原,而非修饰,是作者和历史的“真文本”而非“伪文本”,是走近曹雪芹而不是背离曹雪芹。
笔者想从石校本举几个例子说明“修订”的主观性对“求真”的影响。
例一,因人物年龄问题而修改不当者。前文已论,有些所谓“年龄时序错误”,如黛玉年岁添加等,实际上是曹雪芹的哲思艺术时间观(即“大时间观”)对史传时间观的突破,是“假语”时间观对“真事”时间观的突破,但史传“真事”时间观却视为错谬。在如此两种观点解读对立的情况下,在作家创作过程、传抄过程复杂性,又加上作家艺术构思和创新的复杂性难以确证索解的情况下,哪些该改,哪些不该改,不能改,怎样改,谁人充当终极裁判官?
例二,因主观感受“不得体”而修改者。如第二十二回结尾,修订者把原文写贾政走后的一段生动活泼文字全部删掉,理由是“原本文字问题非常严重。宝玉、宝钗和王熙凤三人的言行皆不得体”。(石校本300页)所删文字为:
且说贾母见贾政去了,便道:“你们可自在乐一乐吧。”一言未了,只见宝玉跑至围屏灯前,指手画脚,满口批评,这个这一句不好,那一个破的不恰当,如同开了锁的猴子一般。宝钗便道:“还像适才坐着,大家说说笑笑,岂不斯文些儿。”凤姐自里间忙出来插口道:“你这个人,就该老爷令你每日寸步不离方好。适才我忘了,为什么不当着老爷,撺掇叫你也作诗谜儿。若果如此,怕不得这会儿正出汗呢。”说的宝玉急了,扯着凤姐儿,扭股儿糖似的只是厮缠。
由于第二十二回惜春谜后底本文缺,后文系从戚序本补,此处可供讨论的空间更大。张俊沈治钧评这段文字(程高本仅个别异文)曰:“贾政去后,宝玉与众姐妹嬉笑欢乐,无拘无束,回映上文,再补一笔,以反衬政老之‘迂拘可嫌’,此即脂评之所谓‘背面傅粉法’也。”⑧但石校本不认可,将生动的情境和性格描写删改为一叙述语句:“这里贾母又与众人说笑了一会”。这种修订并非因年龄时序等硬伤,而属于修订者个人感受的审美范畴,是戚序本原文“文字问题非常严重”“皆不得体”?还是不必修改,如红研所本所取?还是石校本修改的文字过于干瘪无味?见仁见智,显然很难取得共识。
例三,修改前八十回文字以适应后四十回者。修订者强调“以前八十回内容为准绳,让后四十回的思想内涵、故事脉络、人物形象尽可能与前八十回保持一致,是本书修订时确立的基本原则。”但第七十八回却出现了“因为后四十回续书内容与此段文字存在矛盾”而修改此回文字的情况(石校本1088页),而被修改删除的内容恰恰是庚辰本独有很可能是曹雪芹原稿的文字:
“近日贾政年迈,名利大灰,然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因在子侄辈中,少不得规以正路,近见宝玉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们,各各亦皆如此,虽有深精举业的,也不曾发迹过一个,看来此亦贾门之数。况母亲溺爱,遂也不强以举业逼他了。”(红研所本,1101-1102页)
原稿(贾政)“年迈,名利大灰”及“就思及祖宗们”至“遂也不强以举业逼他了”数句被石校本删去,改为”贾政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所以近日是这等待他”。(石校本1088页)这种删改的思路和做法暴露了修订者的两难:是依据曹雪芹文本的意图改变后四十回?还是与后四十回“宝玉读书中举”相衔接修改前八十回?结果他选择了后者,而这恰恰是人们批评后四十回的主要议题之一,修订者也背离了其自订的“基本原则”。刘敬圻先生二十年余前曾对石校本删改的这段文字有过极为精彩的论述,指出:
作家以明白无误的语言,直截了当地写出贾政对贾宝玉“这一种风流”的认同……更有趣的是,这种正面认同心态,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也没有任何调侃他人或自我调侃的味道,而是十分认真十分严肃的“史”的回顾与前瞻,甚至是以“祖宗”的荣辱、祖宗的“成败”为参照系的。……
父子二人较量了十余年,最后还是以贾政的妥协与放弃告终。他放弃了主流文化与宁荣二公对贾宝玉天经地义的价值期待,他认同了贾宝玉对“仕途经济学问”的拒绝及其相关的活法。⑨
本来,要解决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的矛盾,就应该尽可能体现曹雪芹前八十回的思路,曹雪芹用《西江月》词句暗示了贾宝玉“贫穷难耐凄凉”的末世境遇,丝毫没有暗示他后来读八股应举,怎么能够修改前八十回文字去与后四十回“衔接”呢?粗读石校本对后四十回的修改,可以见到并没有脂批所提到的原稿“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等景象,反倒是保留了后人批评后四十回违背曹雪芹构思意愿的大部分内容,如鲁迅所言“殊不类茫茫白地,真成干净者矣”,也与修订者本人对后四十回的批评大异其趣。究竟修订者为何如此处理,不得而知。
以上三例,都是对前八十回文本的修改,其中两例是对曹雪芹原稿的修改,由此可以看出修订者的实际态度,也可以看出修订的主观随意性。笔者不禁要问:这就是修订者所说的提升现有“初阶混合水平”达到“真正的融合状态”的“高阶混合水平”吗?伟大作家的文本被如此处理,笔者深感痛心。
六
提出“修订”《红楼梦》文本这个问题也许具有某种普遍性,引申出来,就是中华文化的经典文本的历史形态,后人是应该尊重和守护它们,还是可以因为其不完美或有缺陷而修改使之完美?
古典小说四大名著的文本都需要修订吗?《三国演义》那么多地名史实错误,需要修订吗?《水浒传》梁山好汉对妇女的态度,如强抢强娶、对“淫妇”开肠破肚,需要修订吗?《西游记》的荒谬宇宙论,需要修订吗?除“少儿版”外,《红楼梦》中的粗俗词语,薛蟠的粗俗酒令需要修订吗?自上古先秦以来,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经典的存在“问题”的著作作品都需要修订吗?
如此推想,所有的经典都是历史的产物,都不可避免地打上历史局限和个体局限的印记,也都落后于时代和今人,都是需要修订的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可是伟人的谆谆之言。
红学从来是开放的。不但有关于作者的百十种探索,有索隐探佚的论著和作品,即以后四十回而论,笔者所见所闻的“修订”创作就不少,有另起炉灶的,也有修改程高本的。已过世的退休工程师九旬老人刘可,曾一次又一次地用端正小楷把修改后四十回的文字贴在原文本旁边,寄给我听取意见,后终得以《红楼梦后四十回校注》出版,笔者至今尊敬和怀念这位忘年交。⑩
笔者质疑“修订说”,但并不否定修订者的努力。石问之是笔者真心佩服的一位卓有建树的中年红学家。我们虽未谋面,但笔者也曾经向他陈述过“对改前八十回持审慎态度”的意见,笔者对《红楼梦》叙时艺术的探讨,既受石著的启发,也是个人异议的表达。笔者相信,石校本自有其探索和存在价值。但在文本问题上,笔者坚持认为,“修订”不是方向。已经成为经典的历史形态的《红楼梦》文本,应该在红研所本的正确方向下,守护完善,而不是“修订”。经典文本,包括它的不完美和缺陷,都是后人阐释研究的对象。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超越前人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是我们后人的神圣职责和义务。尊重前人,尊重历史,这也是对待所有经典文本历史形态的正确态度。即使非经典文本,古籍出版修复还原,也绝没有“修订”的任务。
红研所混合本出世未久,受到广大读者欢迎认可,至少“让子弹飞”一百年,让它为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贡献吧。读者希望版本稳定可靠,不希望《红楼梦》文本处在动态“修订”中争议不休,令人无所适从。笔者乐见红研所本、程高本、各种混合本、修订本的百花齐放,也乐见在经典的历史文本和后人的“修订”文本的良性竞争中,学界、大众和市场将做出的选择。

注释:
①参见朱淡文《红楼梦论源》第二编第三章,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
②刘上生《“一抔净土”还是“一堆净土”》,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2024-7-5.
③参见张庆善《一卷红楼万古情——写在冯其庸先生诞辰百年之际》,载《传记文学》2024年4期;《多少功夫筑始成——红研所校注本<红楼梦>出版四十周年纪念暨2022年修订版新版发布会在京举行》,《红楼梦学刊》公众号2022-8-24.
④孙伟科《当代红学发展的时代主题》,载《红楼梦学刊》2025年第1辑。
⑤沈治钧《红楼梦成书研究》,中国书店2004年版,180-201页。
⑥王蒙《红楼启示录》,三联书店1991年版,296页,305-306页。
⑦参见刘上生《换一个角度思考——<红楼梦>人物年龄问题错迕问题新探》,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2024-10-9.。刘上生《林黛玉的年龄提升和曹雪芹的“大时间观”——<红楼梦>人物年龄错迕问题新议》,载《曹雪芹研究》2025年弟1期。
⑧ 张俊、沈治钧《新批校注红楼梦》,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425页。
⑨刘敬圻《贾政与贾宝玉关系的还原批评》,原载《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2期,收入刘敬圻《红楼梦补说》,台湾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4年版,53-66页。
⑩《红楼梦学刊》微信公众号《红学书目》(一)2019-2-21.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黄安年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wap.sciencenet.cn/blog-415-1493940.html?mobile=1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