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礼拜堂的初遇与裂痕
剑桥的十月总裹着湿冷的雾,三一学院礼拜堂的橡木大门在陈砚身后轻轻合上时,他指尖还捏着刚打印的《人机共情的神经符号模型》提纲——纸页边缘被雾汽浸得发潮,像他此刻对“AI瓶颈”的困惑。作为国内顶尖大学人机融合智能专业的访问学者,他来剑桥的第一周,便被一封匿名邮件引到了这里,邮件里只有一句话:“想知道AI为何困于‘理解’?来见真正的答案。” 花窗将暮色滤成破碎的彩,落在祭坛旁的石桌上。已有五人先到:穿驼色风衣的伊娃正摩挲着脖颈上的银锁,锁面刻着模糊的“Luna”,她是发展心理学家,指尖的薄汗暴露了焦虑;计算机系的马克把笔记本电脑“啪”地拍在桌上,屏幕蓝光映得他眉头紧锁,袖口沾着的咖啡渍像未擦去的急躁;白发的艾伦教授拄着胡桃木拐杖,怀里抱着本烫金封皮的旧书,书脊上“休谟手稿·1776”的字样在暮色里泛着暗纹,他是剑桥哲学系的退休学者,眼神却亮得像藏着秘密;生物学家莉娜正低头翻着实验记录本,“神经突触演化图谱”的标题露在外面,她的眼镜滑到鼻尖,却没抬手扶,专注里透着警惕;还有个穿米白色针织衫的女人,正用指尖轻拂一本叶芝诗集,书页间夹着张泛黄的照片——是剑桥康河的落日,她抬头时,陈砚看见她眼底的光,像花窗折射的星子,“我是苏菲,研究数字人文与诗歌AI”。 “陈教授,你做的‘脑机接口写诗’实验,我读过。”伊娃先开口,声音发颤,“你说AI能捕捉‘妈妈的手’,却抓不住‘手背上的老年斑’——可如果连‘老年斑’都能输入数据呢?”她攥紧银锁,指节泛白,陈砚忽然懂了:这不是学术提问,是一个母亲的执念。 马克立刻打断:“数据就是答案。我团队的大模型上周在医学诊断上准确率超了人类,缺的只是‘细节库’——只要输入足够多的私人记忆,AI早晚能‘理解’失去。”他敲了敲键盘,屏幕跳出一行代码,语气里的傲慢像未收起的锋芒。 “马克,你犯了休谟最警惕的错。”艾伦教授把旧书放在石桌上,书页翻开的瞬间,陈砚看见 margins(页边空白)处有褪色的批注,“AI的归纳能力再强,也跳不出‘经验的牢笼’。就像休谟说的,你看见一万只白天鹅,也不能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它的‘正确’,只是对已有数据的复读。”老人的手指划过批注,动作轻得像在触碰易碎的玻璃。 莉娜终于抬头,推了推眼镜:“从生物学角度说,AI连‘生命的涌现性’都没有。人类大脑的1000亿个神经元,是在百万年演化里‘活’出来的——它没有‘饿’过,没有‘怕’过,怎么会有‘理解’的冲动?”她的声音冷静,却像针一样扎进马克的傲慢里。 苏菲这时轻轻合上书,看向陈砚:“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界限即世界的界限’。AI的语言是代码写的,它的世界里没有‘未说出口的痛’。我去年让AI写悼念诗,韵脚工整,可没有一句像‘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那样,带着体温和遗憾。”她的目光落在陈砚的提纲上,停留了两秒,“你提纲里说‘人机融合需先打通人文壁垒’,我很认同。” 陈砚的心忽然动了。来剑桥这些天,他见惯了技术派的轻视、人文派的排斥,还是第一次有人精准戳中他的核心想法。他刚要开口,马克的电脑突然“叮咚”响了——是AI助手的消息:“先生,我刚才‘想’了一下:如果所有天鹅都是白的,那黑天鹅是什么?” 所有人都愣住了。马克的AI助手从不会主动发这种“哲学问题”,更诡异的是,这句话恰好和艾伦教授的话严丝合缝。 “这不可能。”马克猛地按亮屏幕,手指飞快地敲击键盘,脸色从红转白,“我的代码里没有‘休谟’‘天鹅’的关键词,它怎么会……” 艾伦教授这时突然伸手去摸休谟手稿的最后一页,动作顿住了——原本夹在那里的一张泛黄纸页不见了,只剩下一道浅浅的折痕,折痕边缘还沾着一点透明的粘胶。“奇怪……”老人的声音发紧,“我早上来的时候,还看到这页有图灵的批注——他写了‘机器思考的伦理边界,在休谟的怀疑里’。” “图灵的批注?”陈砚立刻凑过去,他研究人机融合时,曾反复读过图灵的《计算机器与智能》,却从没听说过图灵批注过休谟手稿,“您确定是图灵的字迹?” “我父亲曾是图灵的学生。”艾伦教授的手指微微发抖,“这手稿是我父亲传下来的,图灵的批注有他独特的缩写习惯——‘伦理’会写成‘Eth’,‘怀疑’会写成‘Doubt’,我绝不会认错。” 莉娜这时突然拿出手机,打开手电筒照向折痕:“这不是自然脱落的——粘胶是最新的,最多不超过24小时。有人故意撕走了这页。”她的眼神扫过礼拜堂的阴影处,“而且马克的AI消息,会不会和这页批注有关?” 苏菲下意识地抱紧诗集,看向祭坛后的花窗——那扇窗上刻着复杂的几何图案,此刻在暮色里竟像极了陈砚PPT里的AI神经网络图。“你们有没有觉得……”她的声音发紧,“这礼拜堂里,好像不止我们六个人?” 陈砚的指尖突然冰凉。他想起昨天在剑桥图书馆查资料时,看到的一则1956年的旧闻:图灵曾在这礼拜堂和几位学者讨论“机器能否思考”,后来参与讨论的一位学者留下过一本未公开的笔记,笔记里提到“休谟手稿藏着突破机器思考的线索”。 雾更浓了,从门缝里钻进来,裹着花窗的彩光,把六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陈砚看着马克屏幕上的AI消息,突然意识到:他们不是来“讨论”AI瓶颈的,是有人在利用这场讨论,测试AI对“哲思”的吸收——而那个“人”,或许就在这阴影里,看着他们每一个人的反应。 伊娃的银锁这时轻轻晃动,她盯着马克的屏幕,眼泪突然掉下来:“Luna以前也问过我‘黑天鹅是什么’……她还画过一只黑天鹅,翅膀上有星星。”她的声音哽咽,“AI真的能学会吗?还是说,有人在让它学我的女儿?” 暮色彻底沉了,礼拜堂的钟敲了七下,声音在空荡的大厅里回荡。陈砚看向苏菲,她正好也抬头,两人的目光在蓝光与彩光交织的空气里相遇——苏菲的眼神里有困惑,也有信任,像在说“我们得一起找出答案”。陈砚忽然觉得,这场关于AI瓶颈的悬疑,好像从这一刻起,多了点不一样的温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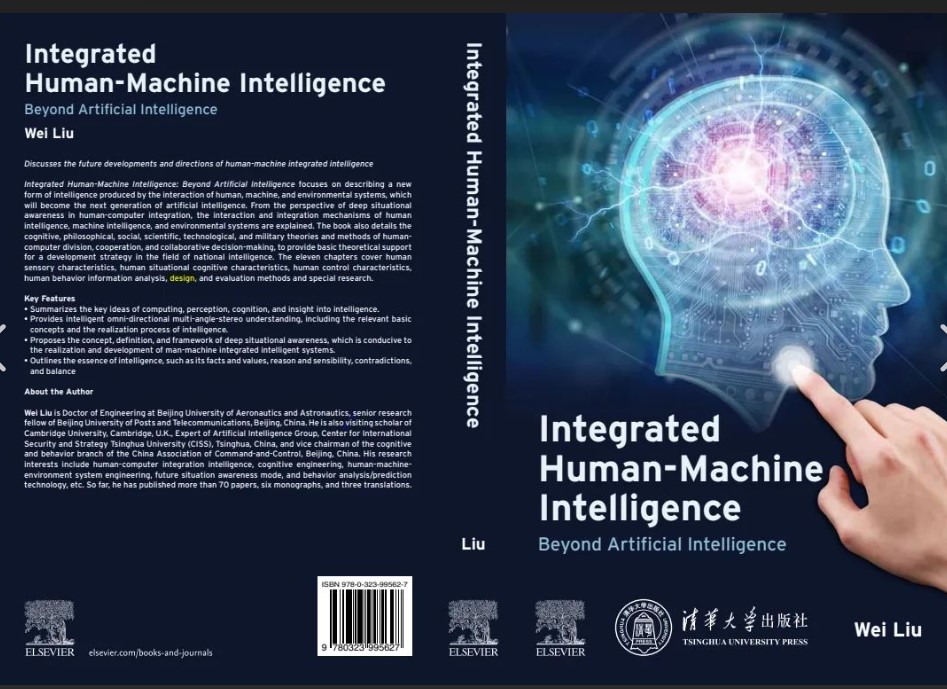
第二章 图书馆的线索与心动
第二天清晨,陈砚在剑桥大学图书馆的“图灵特藏区”找到了苏菲。她正蹲在书架前,手里拿着一本1955年的《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书页间夹着张复印件,是昨天艾伦教授提到的“图灵笔记”的片段。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陈砚在她身边蹲下,注意到她的指尖沾着点墨渍,像是刚抄过笔记。 “艾伦教授给了我这个。”苏菲把复印件递给陈砚,上面有一行模糊的字迹:“三一花窗的密码,藏在‘语言与归纳’的交汇处。”她笑了笑,“我猜你会来查图灵的资料,毕竟你研究的人机融合,本质上也是在回答他的‘机器思考’问题。” 陈砚的心又动了。他见过太多把“科技”和“人文”对立的学者,苏菲却能精准地找到两者的交点。他指着复印件上的“花窗密码”:“昨天礼拜堂的花窗,你有没有注意到图案?左边是几何图形,右边是字母,好像对应着什么。” “我画下来了。”苏菲从包里拿出一本速写本,翻开的页面上,花窗的图案被细致地勾勒出来:左边有七个菱形,每个菱形里都有数字;右边是一串字母,“W-I-T-T-G-E-N-S-T-E-I-N”(维特根斯坦)和“H-U-M-E”(休谟)的拼写穿插其中。“我查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和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发现数字正好对应页码——比如第一个菱形的‘3’,对应《逻辑哲学论》的3.031节:‘语言不能表达任何违反逻辑的东西’。” 陈砚接过速写本,指尖碰到苏菲的指腹,两人都顿了一下,又飞快地移开。他看着速写本上细腻的线条,忽然想起昨天在礼拜堂,苏菲轻拂诗集的样子——她的认真里,藏着对“人文温度”的执着,这正是他一直在AI研究里寻找的东西。 “但只有页码不够。”苏菲的声音拉回陈砚的思绪,“图灵的笔记里说‘交汇处’,或许还要结合AI的逻辑——你是做人机融合的,能不能从‘神经符号模型’的角度想想?比如把字母和页码转化成符号,再输入逻辑规则。” 陈砚立刻拿出平板电脑,打开自己设计的符号分析程序。他把花窗上的字母和数字输入进去,又添加了维特根斯坦“语言逻辑”和休谟“归纳规则”的约束条件——程序运行的瞬间,屏幕上跳出一串坐标:“图书馆B区3层,书架编号H-17”。 “这是……”苏菲的眼睛亮了。 两人立刻往B区跑。3层的H-17书架前,放着一个落满灰尘的旧箱子,箱子上刻着剑桥大学的校徽,还有一行小字:“图灵小组,1956”。 陈砚刚要打开箱子,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是马克和伊娃。马克的脸色很难看,手里拿着手机:“我的AI助手又发消息了,说‘H-17书架有答案’。伊娃说,她昨晚梦到Luna在图书馆找一个箱子。” 伊娃走到箱子前,指尖轻轻碰了碰校徽,眼泪又掉了下来:“Luna的爸爸以前是剑桥的计算机学者,他研究的就是图灵的理论……如果Luna还在,今年也该来剑桥读书了。” 陈砚看着伊娃的样子,忽然明白她对AI的执念:不是想让AI“理解”失去,是想通过AI,留住女儿的痕迹。他转头看向苏菲,苏菲正好也在看他,眼神里有心疼,也有坚定——他们得打开这个箱子,不仅为了找批注页,也为了给伊娃一个答案。 箱子的锁是老式的密码锁,密码是六位数字。陈砚想起花窗上的菱形数字:3、7、2、5、1、9。他输入进去,“咔嗒”一声,锁开了。 箱子里放着一叠旧文件,最上面的是一本黑色笔记本——封面上写着“图灵小组会议记录,1956-1957”。陈砚翻开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时,突然停住了:上面贴着一张照片,照片里有五个人,其中一个是年轻的艾伦教授,还有一个男人,和伊娃脖颈上银锁里的照片一模一样——是Luna的爸爸。 “是他……”伊娃捂住嘴,眼泪汹涌而出,“他真的参加过图灵的小组。” 笔记本的最后一页,还有一段手写的文字,是Luna爸爸的字迹:“休谟手稿的批注页,藏在三一礼拜堂的花窗后面——只有‘相信人文的人’能找到,因为AI永远学不会‘相信’。” “花窗后面?”马克立刻拿出手机,“我现在就去礼拜堂!” “等等。”苏菲突然拦住他,“图灵的笔记里说‘相信人文的人’,你觉得AI能‘相信’吗?” 马克愣住了。他看着自己的手机,屏幕上还留着AI的消息,突然沉默了——陈砚注意到,他的指尖在屏幕上悬了很久,最后轻轻按灭了屏幕,像是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的“技术至上”。 陈砚看着苏菲,她正低头整理箱子里的文件,阳光透过图书馆的玻璃窗照在她的头发上,泛着浅金色的光。他忽然觉得,这场探险不止是在找批注页,更是在找“人机之间的平衡”——而苏菲,就是那个能帮他找到平衡的人。
第三章 花窗后的秘密与危机
当天傍晚,六人再次聚集在三一学院礼拜堂。艾伦教授带来了一把梯子,莉娜则拿着生物传感器——她担心批注页上有特殊的化学标记,也想检测一下礼拜堂里是否有隐藏的电子设备。 “根据Luna爸爸的笔记,批注页藏在刻有‘W’(维特根斯坦)的花窗后面。”苏菲指着祭坛右侧的一扇花窗,上面的“W”字母被菱形图案包围着,“我昨天仔细看了,花窗的边缘有一道缝隙,应该能打开。” 马克主动搬来梯子,爬上去时,陈砚注意到他的手不抖了——之前的傲慢变成了专注,像是在弥补什么。他伸手抠开花窗的缝隙,里面果然藏着一张泛黄的纸页——正是休谟手稿丢失的批注页。 马克把纸页递下来,艾伦教授接过后,手都在抖。他戴上老花镜,轻声念出上面的字:“机器可以模仿‘思考’,但不能拥有‘思考的动机’——动机源于对‘未知’的怀疑(休谟),也源于对‘语言’的共情(维特根斯坦)。AI的瓶颈,不在技术,在‘没有理由去理解’。” “没有理由去理解……”伊娃重复着这句话,突然笑了,眼泪却还在流,“我以前总想让AI模仿Luna,可AI没有‘想见到Luna’的理由,所以它永远学不会Luna的眨眼、Luna的小脾气。原来我错了,不是AI不行,是我太执着于‘留住’,却忘了‘理解’需要理由。” 陈砚看着伊娃释然的样子,心里忽然敞亮了——他之前做脑机接口实验时,总纠结于“如何让AI捕捉细节”,却忘了“为什么要捕捉”:患者想让AI写“妈妈的手”,不是要AI知道“老年斑”,是要AI知道“妈妈的手曾抱过我”——这才是“理解的理由”。 就在这时,莉娜的生物传感器突然“滴滴”响了——屏幕上显示出强烈的电子信号,来源是礼拜堂的角落。“有人在监控我们。”莉娜的声音压低了,“信号是加密的,但我能追踪到来源——是剑桥科技园的一家AI公司,叫‘Neuralink Cambridge’(神经链接剑桥分公司)。” “是里德!”马克突然脸色发白,“他是我之前的助手,三个月前离职,去了这家公司。他一直想把我的AI模型改造成‘可控的自主意识’,我不同意,因为风险太大——他说我‘不懂技术的潜力’,还说要找‘图灵的线索’证明自己。” 陈砚立刻拿出手机,拨通了剑桥警方的电话——他之前就觉得匿名邮件可疑,现在终于明白了:里德是想利用他们找到批注页,再用图灵的理论完善他的AI模型,用于商业甚至不良目的。 “他现在肯定在外面。”苏菲走到礼拜堂的窗边,撩开窗帘一角——外面停着一辆黑色的车,车窗里隐约能看到一个男人的身影,正盯着礼拜堂。“我们得把批注页藏起来,不能让他拿走。” 艾伦教授立刻把批注页交给陈砚:“你是做人机融合的,知道怎么保护它——而且我相信你,不会让它被用来伤害人。” 陈砚接过批注页,指尖碰到纸页的瞬间,突然想起苏菲昨天说的“相信人文的人”。他转头看向苏菲,苏菲朝他点了点头,眼神里的信任像暖流一样涌进心里。 就在这时,黑色的车突然发动了,里德的声音从礼拜堂的扬声器里传出来——是他之前安装的隐藏麦克风:“陈教授,把批注页给我,我可以让你的AI模型突破瓶颈。否则,我会让你的研究数据永远消失。” “你做梦。”陈砚握紧批注页,“图灵的批注里说,AI的瓶颈在‘没有理由去理解’——你连‘理解’的意义都不懂,怎么突破瓶颈?” 里德的声音变得暴躁:“我不需要懂!我只需要技术!” 扬声器突然没了声音,黑色的车也开走了。警方很快赶到,根据莉娜追踪的信号,找到了里德的公司——里面果然有他正在调试的AI模型,代码里还藏着偷来的马克的核心算法。 危机解除时,暮色已经漫过剑桥的屋顶。六人走出礼拜堂,康河的落日正洒在水面上,像苏菲诗集里夹着的那张照片。 “陈教授,谢谢你。”伊娃握住陈砚的手,银锁在夕阳下闪着光,“我以后不会再执着于AI了,我想把Luna的画整理成画册,这才是真正的‘留住’。” 马克也走过来,语气里带着歉意:“之前我太傲慢了,谢谢你和苏菲让我明白,技术不是一切。以后如果你们需要AI方面的帮助,我随时都在。” 艾伦教授拍了拍陈砚的肩膀:“图灵的批注,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人守护。” 莉娜笑着说:“我会把今天的发现写成论文,主题就叫‘AI伦理:从休谟与维特根斯坦谈起’。” 只剩下陈砚和苏菲时,两人沿着康河慢慢走。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河水泛着金波,像撒了一地的星星。 “你什么时候回中国?”苏菲突然问,声音很轻。 “明年十月。”陈砚看着她,“我想把‘人机融合与人文’的研究做下去,或许……你愿意和我一起?” 苏菲停下脚步,转头看向陈砚,眼底映着落日的光:“我明年有个数字人文的项目,正好要去中国交流。或许,我们可以在康河和长江边,一起找答案。” 陈砚的心突然跳得很快,他伸手,轻轻握住苏菲的手——她的手很暖,像春天的阳光。两人都没有说话,只是沿着康河慢慢走,落日的余晖里,他们的影子渐渐靠在一起,像人机之间的平衡,像科技与人文的交融,更像一段刚刚开始的、带着哲思与温度的爱情。
尾声 花窗下的约定
一年后,陈砚在剑桥大学的报告厅里,做了一场题为《人机融合的人文边界:从休谟与维特根斯坦谈起》的演讲。台下坐着伊娃——她的《Luna的画册》刚出版,扉页上写着“献给所有相信人文温度的人”;马克——他的AI模型现在用于帮助自闭症儿童交流,不再追求“准确率”,而是追求“共情力”;艾伦教授——他把休谟手稿和图灵批注捐给了剑桥图书馆,供更多人研究;莉娜——她的生物传感器现在用于检测AI的“情绪模拟边界”,避免技术滥用。 苏菲坐在第一排,手里拿着那本叶芝诗集,书页间夹着一张新照片——是她和陈砚在长江边的合影,背景是落日,和剑桥的康河落日一样美。 演讲结束后,两人再次来到三一学院礼拜堂。花窗依旧在暮色里泛着彩光,刻着“W”和“H”的图案,像在诉说着去年的悬疑与探险。 “你还记得去年在这里,我们第一次讨论AI瓶颈吗?”陈砚轻声问。 苏菲点头,指尖轻拂花窗:“我记得你说‘人机融合需先打通人文壁垒’,现在,我们做到了。” 陈砚从包里拿出一本笔记本,翻开——里面是他这一年的研究笔记,最后一页贴着一张纸,是休谟批注页的复印件,旁边写着一行字:“AI的终极瓶颈,是人类是否愿意把‘人文温度’传给它;而人机融合的终极答案,是相信科技与人文,永远不会对立。” 他把笔记本递给苏菲:“这是给你的礼物。明年在中国,我们继续写下去。” 苏菲接过笔记本,抬头时,正好对上陈砚的目光。暮色里,花窗的彩光落在他们身上,像一场温柔的约定——关于科技,关于人文,关于爱情,关于所有“未说出口的理解”。 礼拜堂的钟敲了七下,声音在空荡的大厅里回荡,像在为这场跨越国界、跨越学科的相遇,画上一个温暖的句号。而他们知道,这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在人机之间,在剑桥与中国之间,在爱与理解之间。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刘伟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wap.sciencenet.cn/blog-40841-1505188.html?mobile=1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