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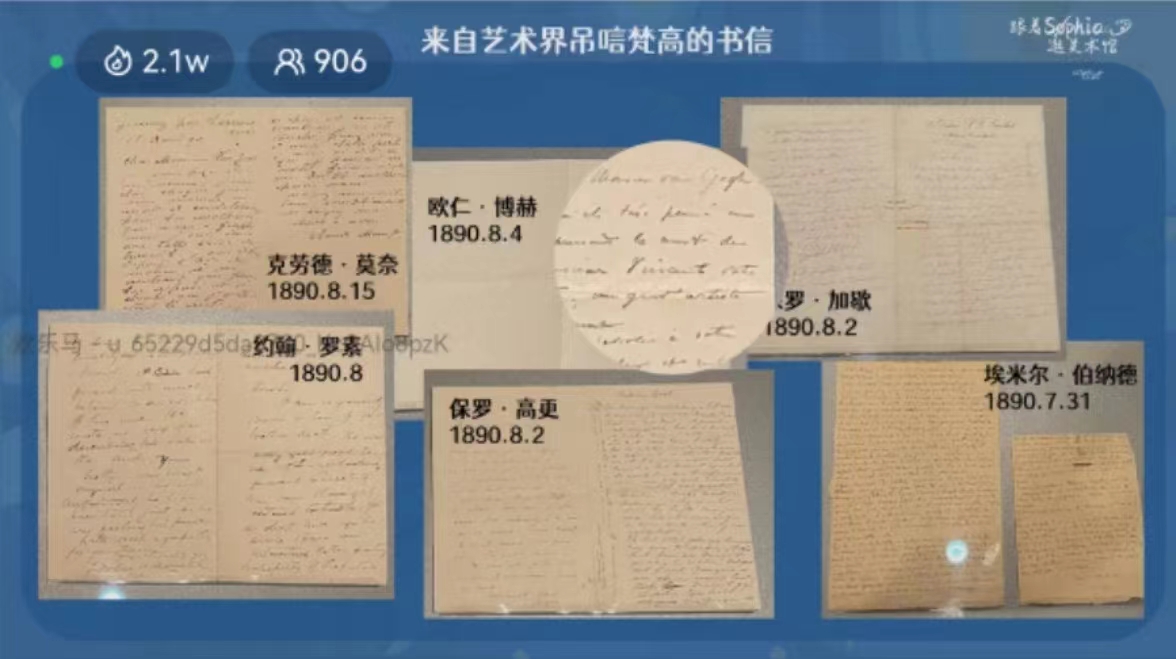

讨论画家的书籍、文章和影视作品,数量最多的恐怕是以凡高为主题的了。1942年时有过一项统计:自1890年凡高去世那年起,50年内,有关他的著述共计出版了777件,至他去世已百年有余,论述他的文章仍源源不绝,其生平故事被改编成电影已不下20部。凡高其人宛如谜团,集意志、疯狂、苦难于一身,引人探究,惹人怀想。作为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特殊人物,凡高拥有安德烈·布勒东所说的“砸不开的黑夜内核”,正因为砸不开,就越发引起猜测和推演,赋予传记文学长盛不衰的魅力。
为体现史料呈现的完整度对不同时期凡高形象塑造的影响,本节内容主要关注这些作品中的第一代,也即主要基于1914年出版的三卷本《文森特·梵高致弟弟的书信集》所开展的创作。这部分作品有两个共性,即普遍比较强调凡高疯狂和怪异的性格对其创作的影响,且相信凡高死于自杀。
传记小说《渴望生活》及其中文版的出版
1934年,可以说是凡高形象传播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1931年,年仅26岁,毫无写作经验的美国传记作家欧文·斯通(Irving Stone)追随凡高的足记遍访英国、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的凡高亲友和曾与他有过交往的人后,回到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单身公寓,以凡高写给弟弟提奥并由其弟媳乔安娜翻译出版的那些信件为主要素材来源,在几近发狂的状态下,用6个月时间四易其稿写成的凡高传记小说《凡·高传——对生活的渴求》(Lust for Life,又译为:《渴望生活》),在这一年终于由英国一家老出版社的小分社——朗曼格林出版社出版。人们从中既看到了一个因善良受苦的天使,也看到了一个用色彩享乐的天才。作者声明,该书中除了一些对话和个别细节为作者所创造之外,故事基本是真实的。在删减了十分之一的手稿后,该书的市场前景仍未得到乐观的预计,出版社怀着求神保佑的心理,只印了5000册。而在那之前的接连3年里,这部手稿先后被美国的17家大出版社拒绝,理由如出一辙:不太可能让正处于萧条时期的美国公众,接受这么一位默默无闻的荷兰画家的故事。但这本书出版以后,被翻译成80余种文字在全球发行,几十年里屡印不衰,影响了世界各地的亿万读者,越来越多的人被凡高的艺术魅力和强烈的个性所吸引。正如该书作者所言,最能打动读者的不是名人深厚的成就和辉煌,而是他们追求和探索的过程。
在笔者的童年时代,《渴望生活》就是笔者所在的小学要求学生们暑假必读的一本课外读物。由这部传记所引发的不同样式凡高题材文艺创作也开始绵绵不绝地诞生。
1947年,法国诗人、戏剧理论家安托南·阿尔托的《梵高:被社会自杀的人》一书,堪称这一时期以凡高为主题的文艺创作中的异数。他在书中将凡高的死归咎于同样有精神疾患的“恶灵”加歇医生,而视凡高为“画家中最纯粹的画家”,指出“他生前不曾片刻稍离绘画(或被称做绘画的东西),不曾离开颜料、画笔以及画布与写生的框架。他不求助于轶闻趣事、故事、戏剧、多彩多姿的情节;也不诉诸主题、对象本身固有的美,却能为自然和对象注入如许热烈的激情。在心理和戏剧性的层面,爱伦・坡、梅尔维尔、霍桑、奈瓦尔、阿尔尼姆及霍夫曼等人最精彩绝伦的故事也不比凡・高最平常的画说得更多。事实上,凡・高的画作都是小尺寸,朴素得仿佛出自刻意。”阿尔托充满激情地为凡高正名固然与他本人也曾因精神病入院的感同身受的经历有关,但也为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凡高打开了窗口。
阿尔托还独具慧眼,在一篇富含闪光见解的评论文章中写道:“我认为高更主张,艺术家应该追求象征、梦想神话,将生活的事物一直扩大成为梦想神话,而梵高则主张,艺术家必须善于演绎最贴近生活的事物的梦想神话。因此我认为,梵高的主张对极了。因为,现实远远高于任何故事、任何寓言、任何神性、任何超现实。只需具有天赋,才善于演绎出来。”
1954年12月22日,中国台湾诗人余光中在他的散文《凡·高——现代艺术的殉道者》中,向汉语世界普及性地介绍了凡高的一生。文章开篇就引用欧文·斯通《凡·高传——对生活的渴求》中高更调侃塞尚的话说,塞尚作画用眼,修拉作画用脑,罗特列克作画用脾脏,卢梭作画用幻想,而凡高作画用心,强调凡高性格中的赤诚和激情转化成画面上“严肃的沉痛”和“爱的气势”。其中讲到“凡高童年极为快乐”似是误解,更多历史资料显示,凡高在童年时代就是一个孤独的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并不亲密,被看作“家庭的陌路人”,他那世俗且因失去第一个孩子而可能长期处于慢性忧郁中的母亲尤其不以这个总是异于常人的儿子为荣,因为在生他之前有过一个和他同名的哥哥,还没生下来就夭折了。在母亲心目中,仿佛那才是她完美的孩子。凡高自己对童年的描述也“是阴郁的、冷酷的、贫瘠的……” 1955年,余光中开始翻译英文版《渴望生活》。
1970年代,在《荷兰先驱》杂志担任编辑的苏格兰作家、有“艺术家侦探”之称的肯·威尔基曾带着杂志主编弗农·伦纳德提供的1500荷兰盾(折合约375英镑),用三个礼拜的时间,沿着凡高当年在荷兰、英国、比利时及法国的22个不同地方生活所途径的“阿姆斯特丹—艾恩德霍芬—尼厄嫩—艾恩德霍芬—蒂尔堡—布雷达—安特卫普—布鲁塞尔—奥斯坦德—多佛—加来—蒙斯—巴黎—阿尔勒—巴黎—阿姆斯特丹”这条火车线走访,在与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馆开幕同期出版的《我们有一样的孤独:梵高的爱与秘密》一书中,寻找当年与凡高有过真正接触的人们以及画家神秘的一生,从困扰凡高的可怕疾病梅毒到他充满禁忌的私生子秘密,试图揭示凡高由纽南的老朋友心目中“慷慨而仁慈的人”转变为巴黎的朋友眼中“冷漠而脾气暴躁的人”的原因,特别是他在伦敦时期对房东女儿(也有说是房东本人)的一场失败求爱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生的转折性作用。
到1982年,《渴望生活》已经被翻译成80种文字,销出约2500万册。78岁的传记作家欧文·斯通在贝弗利山回忆自己23岁那年在巴黎受索邦大学一位年轻学生的怂恿,于卢森堡画廊偶遇凡高画作的场景时说:
“画廊的墙上,并排悬挂了大约七十到八十幅光辉灿烂的油画,都是温森特在阿尔、圣雷米和瓦兹河边的奥维尔画的。这间稍微小了一点的沙龙,在色彩的辉映下,就像阳光透过彩绘玻璃照进大教堂一样,波光流泻,色彩斑斓。对于受过意大利宗教画和巴黎寓意画过多熏陶的我来讲,绘画已经成了一种不能令人激动的艺术。然而,此刻,突然间面对着温森特的这个由色彩、阳光和运动组成的骚动不安的世界,我的确惊呆了。当我惊诧不已地徘徊于一幅又一幅壮丽辉煌的油画面前时,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整个世界豁然开朗:在人、植物、动物从那富有生命感的大地升向富有生命感的天空和太阳,然后又向下会聚到同一中心的运动中,一切生命的有机成分都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伟大崇高的统一体。”
那是继凡高身后提奥为他举办一次小型画展之后的第一次较大的凡高画展,从欧文·斯通的回忆中可见,凡高不同于传统绘画的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风格深切地打动了作家的心,让他感觉“能够把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
1982年,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还没多久,用将近两年的业余时间废寝忘食地译完《渴望生活:凡·高传》的中国译者常涛认为,那是中国可能可以接受凡高的合适时机。但是,在1960年代中国“反对资产阶级文化”运动的阴影下,为了让书顺利出版,常涛在将译稿交给出版社之前,还是违心地添加了一篇百般说明的文字。1983年,凡高在他离世93年后与中国人见面,《渴望生活:凡·高传》先后出版18版,为广大中国读者所接受。自那之后,中国文化界掀起了断断续续的“凡高热”,海子、吴冠中、冯亦代、梵高奶奶等文化人和普通人,以各自作品对凡高及其笔下向日葵形象的加工,将凡高形象进一步普及到中国大众心中。作为大众文化IP的乡间老妇人“梵高奶奶”以凡高的向日葵为主题的创作,尤其在网络上引发了关于“凡高到底画得好不好?”的讨论,启发了中国民众对现代艺术的认识。
相当程度上,凡高的表现主义画法和中国画讲究“意在笔先”“气韵生动”是暗合的,用吴冠中先生的话说:“形式美和意境美在梵高的作品里得到了自然的、自由的和高度的结合,在人像中如此,在风景、静物中也如此。”这可能也是凡高其人其作在中国得到广泛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凡高人生经历中所包含的个性解放和理想主义色彩,与其传入中国时中国正经历的“文化热”所包含的主旨也正好契合。
《渴望生活》等凡高题材电影和纪录片的推出
同德加、莫奈和雷诺阿不同,凡高在电影出现之前就去世了,因此,他没有留下有他影像的电影胶片。但他通过他的书信和作品完整地展现了他的生活。通过他的作品,后人也依然可以和他进行精神的沟通。
1956年9月,美国好莱坞根据小说《渴望生活》改编、拍摄了一部由美国著名影星柯克·道格拉斯主演的同名传记影片《梵高传》。在解释凡高的种种惊世骇俗的行为上面,编剧下的功夫看来还不够,柯克·道格拉斯则卖力地把凡高塑造成一个无赖般的先天性疯子,呈现在画面上的多是一些停留于表面的疯狂举动。单凭这些,对凡高了解不够深入的人们不太可能进入画家的内心,看完全片只会留下“这是个疯子”或“艺术家都是疯子”的印象。片中凡高对高更说的那句“Paul, when you look back, so much of life is wasted in loneliness.”令人对两人友谊的瓦解尤感唏嘘。影片不时地将凡高的传世名作定格在画面上,提醒观众留意与画作对应的画家的内心世界。柯克·道格拉斯的外貌与凡高惊人地相似,尤其是那双眼睛。主演《梵高传》时,他的年龄刚好是37岁,与凡高去世时的年龄一致,加之影片获得了提名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资格,这些都为当时的影片增加了话题性。
BBC1963年推出的系列科幻剧《神秘博士》第5季第10集——《凡高与博士》,也以凡高为主人公。剧中,博士穿越时空把凡高带到了现代。凡高来到博物馆中陈列自己画作的展厅,望着来来往往的众生,惊讶地听到馆长对自己的评价:“他对色彩的掌控无与伦比,他一生饱受折磨,而他却把这些苦难转化成了画布上激情洋溢的美。痛苦很容易刻画,但糅合热情和痛苦,来展现人世间的激情、喜悦和壮丽,前无古人,也许也后无来者。对我来说,这样一个奇特的、狂野的、徜徉在普罗旺斯田野里的男人,不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作为一个人,也是同样伟大的。”画家因为得到后世的理解而热泪盈眶。
1972年,由瑞典女导演梅尔·柴特琳于前一年执导的彩色纪录片《荷兰人文森特》由BBC播出。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好莱坞演员迈克尔·高夫(Michael Gough,1916—2011)在其中评论称:“在西方,没有几个人不受文森特看待世界的方式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有机会,就要对他进行颂扬。”
1987年,澳大利亚人保罗·考克斯(Paul Cox)拍摄的纪录片Vincent突出了凡高人生的戏剧化色彩。
1990年,由罗伯特·奥特曼(Robert Altman,1925—2006)执导,荷兰、英国、法国合拍,讲述凡高和弟弟故事的Vincent & Theo,重点表现凡高的亲情、友爱和对大自然的热爱。同年,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的第28部电影——《梦》上映,影片由他所做的日照雨、桃园、暴风雨、隧道、乌鸦、赤富士、鬼哭和水车村等八个梦组成,以凡高为部分题材,其中第五个梦“乌鸦”是与凡高有关的:男主角在画廊中欣赏凡高的作品,借由《阿尔的朗卢桥与洗衣妇》进入画中,经历了凡高作品中出现的种种场景,与画中人对话,甚至找到了凡高并与之倾谈。一直在画中世界漫游的男主角,直至走入一片麦田,惊起一群乌鸦,才幡然醒悟,从《群鸦乱飞的麦田》重新回到现实。
有人将《梦》称为黑泽明的精神自传,其实片中主人公的形象也正是黑泽明自己。他从小就对绘画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对凡高和塞尚的画情有独钟。凡高绘画中题材处理和色彩使用上的重复性,以及色彩的装饰性、抒情性,对黑泽明的武士系列等电影产生了重要影响。影片中,他通过一些虚构和想象,表达了自己对凡高的理解和敬意,也借凡高之口说出了自己对艺术的见解和追求。
1991年发行、由法国著名导演莫里斯·皮亚拉(Maurice Pialat)执导的《凡·高传》主要记述了凡高生命中最后67天的非常经历,是以凡高为题材的电影中较为成功并具有较高影响力的一部。皮亚拉为了拍摄这部电影,特地去到凡高临死前生活的小镇奥维尔,拍摄凡高最后生活、绘画的地方,这次经历为他理解凡高奠定了基础。对他“捕捉真实的凡高瞬间”、以绘画创作的方式构思影片提供了最初的灵感。该片描述了凡高自杀前在奥维尔度过的最后十多天生活,细心复原了凡高最后画作的创造过程,再现了那些永远留在画布上的人物和场景。作为艺术家的传记片,影片对光线和景物的追求达到了完美的境界,具有印象派风格和完美的艺术欣赏性。片中呈现了凡高起先与高更冲突的关于自然的概念。编剧帕特里克·巴洛让高更问凡高:“那些你看不到的东西呢?在自然的中心,到处都是,那些幽灵和精灵们,你虽然看不到它们,它们却依然存在。文森特,他们是世界中的世界,神秘中的神秘。”。米歇尔·马利在法国Armand Colin 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新浪潮:一个艺术流派》(La Nouvelle vague. Une école artistique)一书的第六章里提到:“20世纪80、90年代的法国影坛,笼罩在莫里斯·皮亚拉耀眼的个性光芒之下,他编导的《凡·高传》是90年代法国影坛罕见的杰作之一。”该片中的男主角、凡高的扮演者雅克迪·特隆还借此片获得了1992年第十七届法国电影“恺撒奖”的最佳男主角称号。
美国在2004年发行的英语纪录片《A&E梵高传》(Van Gogh)侧重讲述了凡高改变现实、促成表现主义诞生的历史。
2006年,由荷兰制作的纪录电影《荷兰大师梵高传》中,来自凡高基金会、凡高博物馆的专家和艺术评论人在带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凡高画作真迹前为观众解读这些作品和它们背后的画家,这些带着各国口音的真人讲述由于讲解者本身情感的代入,使传主及其作品更亲切可感。
《Vincent》等纪念性流行歌曲的发行
受凡高作品《星月夜》(《The Starry Night》)的意象启发,美国民谣歌手唐·麦克林(Don Mclean)在20世纪70年代初专门为凡高写了一首歌曲——《Vincent》(《文森特》),随其专辑《American Pie》(《美国派》)发行。唐麦林略带沙哑却无比柔和的嗓音,在简单的木吉他伴奏下缓缓流淌,管弦乐的加入增添了旋律的悠扬和哀愁,轻轻诉说歌者的怀念和忧伤:
Starry, starry night(繁星点点的夜晚),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ey(为你的调色盘涂上灰与蓝),Look out on the summer's day(你在那夏日向外远跳),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用你那双能洞悉我灵魂的双眼)。Shadows on the hills(山丘上的阴影),Sketch the trees and the daffodils(描绘出树林与水仙的轮廓),Catch the breeze and the winter chills(捕捉微风与冬日的冷冽),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以色彩呈现在雪白的画布上)。
唐·麦卡林非常用心地读过凡高日记,因为这歌词里有的话就是凡高的原话,如第三句:“Look out on the summer’s day”,就是凡高在圣雷米住院期间说过的话。1889年夏季,在圣雷米疗养院的夜晚,凡高经常从病房里望向窗外,遥望东边阿尔提勒山的星空,由此产生创作的冲动。但是星月夜也让人想起凡高说过的另一句话:“我们以死亡为意,穿梭群星。”唐·麦克林以诗一般美丽的语言重现了凡高作品中的夜空、树木、花朵、麦田和农夫,将凡高的眼睛捕捉到的安静、美丽的世界和那个世界里的他心灵深处的寂寞、苦楚一起,如画卷般慢慢舒展于听者的脑海中,表达了深切的精神关怀。歌者显然明白凡高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传递的思想,也了解凡高曾经经历怎样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理解、可以倾听这动人的故事,他为凡高而歌。
今天,在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凡高博物馆门前,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们都能听到这首感人至深的歌曲在循环播放,向一生坎坷的而依然对生活充满渴望、对人间充满爱的艺术家致以不息的敬意。这首歌曲也至今在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人群中广为流传,如目前收藏《星月夜》这幅作品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每天开馆和闭馆时,都会播放这首曲子。虽然许多听众并不知道它的歌词与凡高的关系,但歌曲通俗的旋律和动人的意境仍然让众多普通人爱上了它。它的广泛传播,某种意义上,拓宽了凡高精神的流传边界,人们在满天繁星下那个寂寞、宁静的世界里,与自己的心灵对话,尝试更多地理解自己,同时也为不知何时与凡高的相遇做好了心理准备。笔者曾看到报道说,北京人艺艺术处处长、《燃烧的梵高》编剧吴文霞手机铃声用的正是这首歌,她表示,凡高的纯粹和执着一直激励着自己追寻梦想。
在唐·麦克林的《Vincent》之后、香港歌手王菀之的《画意》、大陆歌手李志的《梵高先生》、台湾歌手阿沁的《梵高的左耳》等与凡高相关的纪念性流行歌曲相继发行,使凡高题材的音乐和影像创作渐渐加入了大众文化的流行。
当代中国文化人笔下的凡高
国内建国后最早出版的凡高传记《麦田里的人:凡·高》,作者是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林和生,于1998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台湾牧村图书公司于2000年7月也出版了此书,书名为《麦田里的人性和艺术:梵谷——现实和绘画中的麦田》。该书通过对凡高思想的疏解来阐释他的生活和以麦田/故土之爱为起点的创造历程,提供了一个研究和认识凡高的新角度,是国内同题材传记中值得推荐的一部精品。
在被问及为何对凡高情有独钟时,林和生表示,自己对像凡高这类人特别感兴趣。除凡高之外,他还写了卡夫卡和克尔恺戈尔。这些人在思想上、个人气质上,甚至个人命运上都存在着一种“家族类似”。一方面,他们都是“不合群”的,性格上具有明显的叛逆性,他们的思想、创作都不被容于所处的时代,因此不仅不被理解,甚至还遭到周围人的冷嘲热讽和侮辱唾骂;另一方面,他们常被认为是怪人、变态者、疯子。他们也想过一种与大家一样的生活,但没有相应的能力。换句话说,他们除了具有在死后才被承认的天才之外百无一用。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1日出版的《吴冠中画韵美文》一书中,刊出了吴冠中所写的一篇题为《梵高》的散文。和前文提到过的丰子恺一样,画家吴冠中也将凡高的作品和他为追逐艺术理想而不惜融化自己的生命扑向“太阳”的伊卡洛斯式人生紧密结合起来看,将他与周方、郭熙、吴镇、仇英、提香、柯罗、马奈、塞尚等对描绘对象保持超然的客观冷静的画家相比较,突出了凡高与老莲、石涛、八大山人、波提切利、德拉克罗瓦等中外艺术大家相似的人格特质,即:超越匠气,作品与人生浑然一体。吴冠中本人的情感、价值观、职业操守都使他对凡高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和特别深沉的理解、欣赏之情。在他的笔下,凡高已完全不再是一个“怪人”的形象,而成为一个虔诚的上帝使徒、一个心灵高贵、意志坚定、不畏艰险的艺术界行道者。
中学时读过余光中翻译的欧文·斯通《凡·高传》、并曾于1970年代曾负笈法国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的台湾《联合文学》社社长、美学家蒋勋一站站重访凡高当年作画的现场,重温年轻求学时保存在他脑海里、笔记本里的画家故事。他于2007年出版的台版《蒋勋破解梵高之美》解读了《向日葵》《自画像》《星月夜》《麦田群鸦》等80幅凡高名作背后的美学奥秘,带领读者领悟凡高纯粹的爱与孤独、他作为一个信仰殉道者所饱受的肉体与灵魂的燃烧之苦。该书大陆版于2015年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蒋勋优美深情的文字、对画家情感与理性之深入幽微的洞悉、富有哲思的人性探索和在广阔艺术史视野下的专业解读,都使该书兼具高尚的文化品位和深入浅出的美学普及效应。近年来,其在“喜玛拉雅”等有声阅读平台上的内容转化呈现,更扩大了它的受众,使更多艺术圈外的公众有机会走近凡高。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他不是大多数人认为的无理性的疯子”这个要到2009年六卷本《凡·高书信全集》中文版全球首发式上,才被《凡·高书信全集》主编莱奥·扬森(Leo Jansen)公布的、随书信集完整的出版而得出的最重要的新发现,知识和情感储备贯通文学和绘画的蒋勋,在之前就已经凭借他对画家客观而感同身受的理解,作出了与之一致的判断。事实上,类似的判断欧文·斯通在《渴望生活》里也通过凡高自己的口吻作过初步的表达:“我被一个复杂的演算所吸引,演算导致了一幅幅快速挥就的画作的迅速产生,不过,这都是事先经过精心计算的。”即便如此,该书还是把更重的笔墨放在了对凡高非理性个性的刻画上,这也是凡高离世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文艺创作中对他形象刻画的主流。某种意义上,这也折射出世人心中潜在的世俗“有色眼镜”——一个落魄失意、穷困潦倒至死的画家,能有多少理性呢?不是因为疯狂,又为何要过这样的生活呢?只有那些真正具有洞悉世界之眼光的艺术家,才会看到现象背后的真实,就像希腊神话里在黄昏起飞的猫头鹰,在黑暗中,拥有明亮的眼睛。
转载本文请联系原作者获取授权,同时请注明本文来自陈怡科学网博客。
链接地址:https://wap.sciencenet.cn/blog-1341506-1428233.html?mobile=1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