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科学的起源——中世纪如何奠基现代科学》简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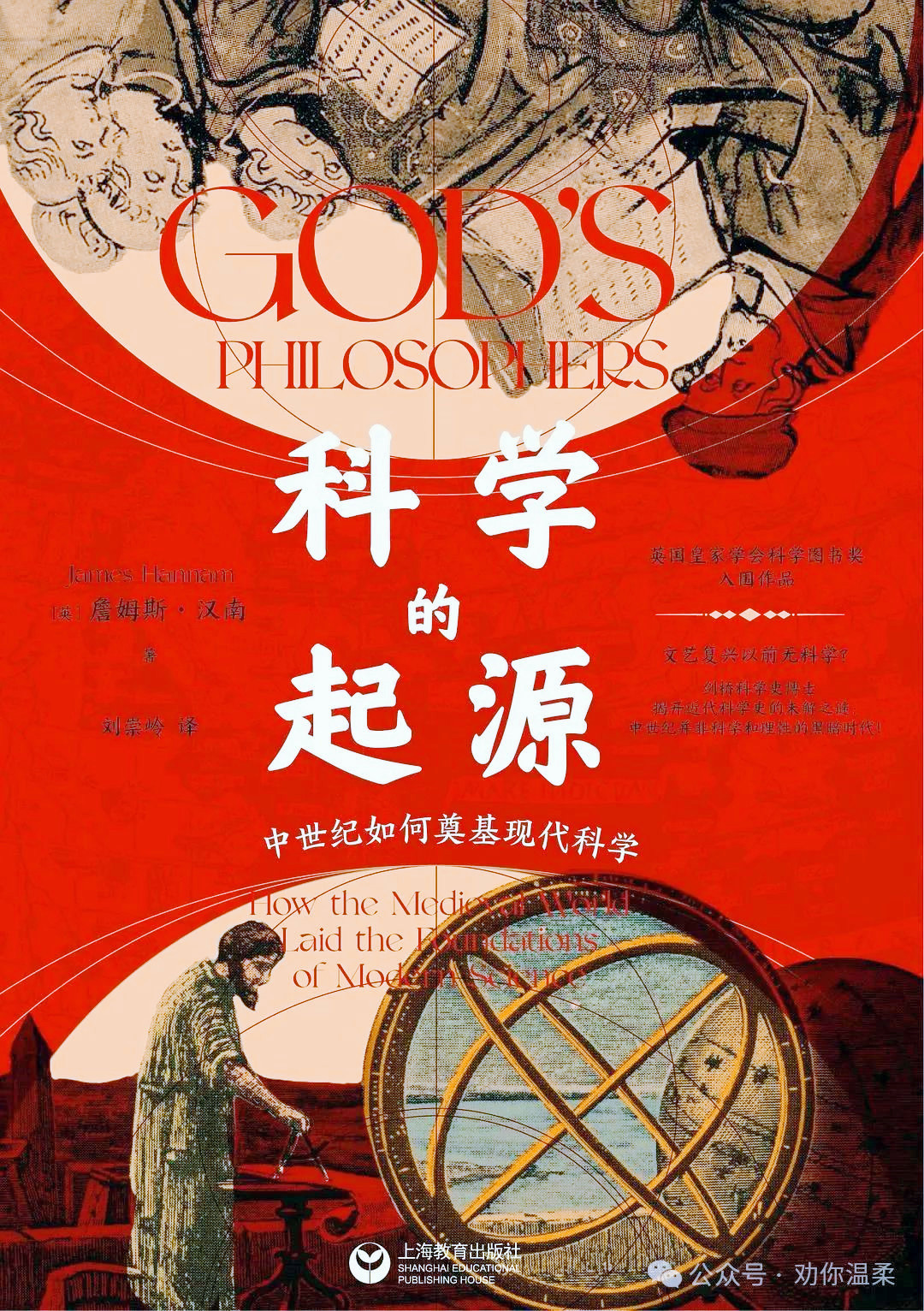
作者:[英]詹姆斯·汉南;出版:上海教育出版社
原作名:God's Philosophers:How the Medieval World Laid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Science
由英国科学史学者詹姆斯·汉南写作、刘崇岭翻译的《科学的起源:中世纪如何奠基现代科学》,2022-12-31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作者基于剑桥大学科学史研究背景,针对“中世纪科学停滞”的流行观点进行系统性反驳,旨在重新评估中世纪科学的历史地位。
该书以6世纪至16世纪为时间跨度,梳理中世纪欧洲与伊斯兰世界的科学遗产,分析眼镜、机械钟、风车等技术发明及光学、数学等领域的理论进展。通过考证中世纪学者对地球形状的认知、教会对科学研究的资助等史实,论证基督教神学与伊斯兰文化在推动理性思维发展中的作用,并指出宗教裁判所审判伽利略事件的政治属性。全书以科学革命关键人物为线索,阐释中世纪在方法论与技术积累层面对近代科学革命的延续性影响。
内容简介
“中世纪是智力停滞、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这是被现代学术界完全否定的神话,如果没有中世纪学者的贡献,伽利略、牛顿、科学革命都不会出现。很多关于中世纪的说法并非事实,比如,中世纪的人并不认为地球是平的,而哥伦布也没有“证明”它是一个球体;宗教法庭并未因任何人的科学思想或发现而将其烧死,事实上教会是科学研究的主要赞助者,甚至若干位教皇以对科学的了解而闻名;哥白尼不惧迫害;教皇也没有试图禁止人体解剖;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的著名审判是关于政治,而非关于科学。中世纪是个在智识上高歌猛进的时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促成了科学进步,带来的成就远超古典世界,在技术上也取得了很多成果。欧洲人独立发明了眼镜、机械钟、风车和高炉,工匠和科学家将东方传来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改进到了超越其发明者想象的水平。透镜与相机,以及几乎所有类型的机器以及工业革命本身,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被遗忘的发明家。
本书集中描述一段跨越六个世纪的史诗之旅,回顾了让·布里丹、尼科尔·奥雷姆、托马斯·布拉德沃丁等被忽视的天才们的发现,并将罗吉尔·培根、奥卡姆的威廉、托马斯·阿奎那等更为人熟知的人物的贡献带入历史语境。
中世纪是一个不乏发明和创新的时代。现代科学技术与所谓“黑暗”中世纪的关系,比我们所知的更有渊源。
作者简介
詹姆斯·汉南(James Hannam),牛津大学物理学学士、伦敦伯克贝克学院历史学硕士、剑桥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博士。曾为会计师,在伦敦金融城小有成就,主要从事电影制片,对科学史满怀热情,为各种报刊如《观察家》《今日历史》《立场》《新科学家》撰稿。《科学的起源》是他为大众写的作品,2010年入围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图书奖。
刘崇岭(译者),辽宁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硕士,现为英语和俄语自由译者。
图书目录
引言 中世纪科学的真相
第一章 罗马陷落之后:中世纪早期的科学进展
第二章 数学教皇
第三章 理性的崛起
第四章 12世纪文艺复兴
第五章 异端与理性
第六章 异教科学如何被基督教化
第七章 惨败:中世纪的魔法和医学
第八章 炼金与占星的秘术
第九章 罗吉尔·培根与光学
第十章 钟匠:沃灵福德的理查德
第十一章 默顿计算者
第十二章 中世纪科学的巅峰
第十三章 新视野
第十四章 人文主义与宗教改革
第十五章 16世纪的博学者
第十六章 人体的运转:医学与解剖学
第十七章 人文主义天文学与尼古拉·哥白尼
第十八章 天文学改革
第十九章 伽利略与乔尔丹诺·布鲁诺
第二十章 伽利略与新天文学
第二十一章 伽利略的审判与功绩
结语 一场科学革命?
进阶阅读建议
大事年表
重要人物表
注释
致谢
海德格尔(网名):如何用一千年培育出科学精神?
艾萨克·牛顿爵士不会横空出世,他有句名言广为人知:“如果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非凡的成就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科学是一代代科学家接力、传递而成,它需要一个科学家网络,它不是某一个人的杰作,而是跨越数个世纪的思想接力和启迪。
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了几何学证明、对天体的畅想,天文学虽说不够正确,却也是蓬勃发展。从托勒密到伽利略,相隔千年之久,古希腊学说是如何穿越漫长的时空抵达近代科学发力的17世纪?一种落后的观点认为整个中世纪的智性创造是停滞的,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希腊哲学重见天日,科学创造才起步。这种庸俗版解释蛊惑了大多数人,稍微用点思辨力就会发现这种观点站不住脚。难道中世纪没有任何值得肯定的智性创造?难道历史并不是延续的?
炮制出庸俗版观点的是启蒙运动思想的那些作家们,为了反对宗教,他们不仅忽略了中世纪的成就,而且还用自己的偏见写作误导后人。这些作品在人类走向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得到推崇,传播甚广,久而久之便成了人们所以为的“常识”。
《科学的起源》是詹姆斯·汉南(James Hannam)为大众写的作品。作为牛津大学物理学学士、伦敦伯克贝克学院历史学硕士、剑桥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博士,詹姆斯·汉南对科学史满怀热情,并且为各种报刊撰稿。《科学的起源》把读者带入到罗马沦陷以后的早期中世纪,一路观察欧洲的理性崛起,直到伽利略的时代。聚焦这段历史就是为了填补大众所欠缺的那一块——对中世纪的无知。当代学界早已抛弃了启蒙思想那套庸俗版的解释,可是从学术到日常有着巨大的隔阂。《科学的起源》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没有很高的阅读门槛,任何一位热爱思考科学起源的人不应该错过它。
阅读这本书之前,我们得带着一些问题的意识。首先,科学的诞生是一件孤立的事吗?从简单的东西方范畴来讲,现代科学的诞生是西方独有的事件。换言之,地球其他地区就压根没有诞生科学。有人或许批评,这样的论述是武断的,中国也有技术发明。中国主流学界喜欢把科学技术混为一谈,认为技术也代表了科学。这实际上是一种粗糙的矫饰,技术当然是科学的一部分,但技术等同于科学吗?吴国盛教授说,中国有的只是技术史,而不是科学史。这里需要澄明,究竟什么才能被视为科学?
举个例子,医学都是从巫术演变而来的。中国自古以来有说法,医就是巫。人类对疾病引起的症状感到恐惧,一个人为什么会呕吐?为什么会抽搐?这些可怕的表现和常人太不一样了。人类对这种反常最原始的认知是认为,这种痛苦来自神灵或大自然的惩罚。要解救那个处于抽搐的人,就需要和神秘的大自然或神灵沟通。所以最古老的巫术也是某种医术。不用怀疑,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都是从巫术过度到医术的。在救治的长期实践中,人类会积累起有效的经验。经验的总结和归纳上升到一定的理论,就构成了东西方的传统医学。但是,人类认识疾病的客观因果关系也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医学的诞生是很晚近的事。关于这一点可以去了解一下“西班牙大流行”的历史,发现病毒、细菌、抗体、抗原、备制疫苗、治疗药物等都处于那次“大流行”后对医学实验室投入研究的历程中。
现代医学作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典型事件,它在西方诞生,被称之为西医。为什么中国的传统医术不是现代医学呢?因为中医并不是用科学的方法探索的,它仍旧处于传统的经验总结的习惯中。医学的事例可以表明,和其他技术一样,它们都必须在一个讲究科学精神的文化里产生。中国的炼丹没有像西方炼金术那样诞生化学,中国的天文知识只有历法和时辰的技术应用,没有诞生真正的天文学。甚至到了大清,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而古希腊人在托勒密的时代就普遍知道地球是圆的。西方中世纪人没有一个会认为地球是平面的,他们早就有了天体的概念和认识。有了这个认知前提,西方人才会设想打通大西洋航海,因为他们认为地球是圆的,最后总能回到原点。这样我们便看出,认知前提和科学精神有关,大量事实的对比之下,科学精神作为一种群体的气质,是西方独有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代科学只诞生在西方。那么,科学精神只是希腊哲学的副产品吗?换言之,科学精神是文艺复兴后才具备的吗?詹姆斯·汉南用大量的史蹈嫠叨琳撸惺兰褪强蒲Ь衽嘤囊±海惺兰团嘤鹆死硇院椭鞘叮皇峭ǔK档奈拗陀廾痢�
思考现代科学诞生的另一个纬度是历史上的科学家们。17世纪之所以被推举为现代科学诞生的时代,乃是因为这个历史阶段天文、物理、化学的发现是爆发式增长的。这些科学家们的名字以及他们建立起的公理出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他们所发现的物理单位。自17世纪伊始到20世纪中旬是科学家群星璀璨的四个世纪,这些人都集中在西方欧洲。这四个世纪绝不是简单的科学发展的过程,最好是被看作科学精神成熟的结果。
著有《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托马斯·库恩就曾说,科学家通常都是独立地研究并发现科学真相,然而这种独立研究无法脱离整个科学家的网络。从横向来说,科学家之间会有跨学科的交流,这使得单独一门学科在别的学科帮助下突破瓶颈。从纵向来说,某一科学家可以和前时代的科学家“交流”,通过钻研前人的学说修正或推翻错误的结论,得出一个正确或可被证实的结果。比如伽利略就是基于托勒密建构的体系、布鲁诺观测的数据修正天文学。这种接力和研究的传统是在一个纵横向、跨时代的科学家网络中进行的。而这种智性的、追求真理的传统源于某种巨大的激情,这激情是对探索世界、认识God引起的。这激情源自于宗教信仰,人们在中世纪认为通过自然之书和Bible都可以认识God。也只有在这一信仰的氛围内,探索自然被视为正当的、急迫要紧的事。
如果没有科学家群体的出现,如果没有如此众多的科学观点汇聚,现代科学的成就无从谈起。这并不是人的问题,并不是选择对了什么人,就能出现科学。这是精神的培育,必须深入到这个思考上——科学家群体是怎么出现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中国可能最有价值。我们在100年前以为西学中用行得通,别人现有的成果拿来用就好。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认为拿得到最前沿技术的就是科学大国,对科学精神的培育并不重视。科学精神是西方的家传,通过《科学的起源》回顾早中期的中世纪历史,看到17世纪以前的一千年,欧洲的知识分子阶层和科学家群体逐步形成。
希腊哲学经典由于穆斯林的侵占而被保存,这让曾经的伊斯兰教世界的科学突飞猛进。穆斯林雇佣的Christians勤勤恳恳地翻译着这些著作,不少著作通过西班牙地区、与拜占庭交往密切的威尼斯地区流入到欧洲腹地。最早一批接触到希腊哲学的是修道院的神职人员,为了反驳异端,他们也需要专注于古典著作的研究。修道院擅长手抄本,随着大翻译运动和书籍数量的增长,古典著作已成为知识阶层的重要知识来源。
此时,欧洲的教育领域一项新的发展便开始起步,这就是大学的诞生。这些知识机构比修道院更自由,处于独立状态。当时的大学就是学生的自治联合体,由学生组织成的公会雇佣教师、学者。中世纪大学的重要课程依然是神学,相对于修道院,可以自由地传授“七艺”——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数、几何、天文、音乐。从第一所欧洲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到巴黎大学、牛津、剑桥,这些自治联合体形成了有效网络,各个学科的知识人通过游学、教书、通信、发表书籍、公开辩论等方式参与到智性生活当中。要知道,这样的智性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信仰的生活,他们的研究和话题无一不关涉到神学问题。罗马教廷并没有强制干预知识团体,也没有禁止古典学说。当时的主流认为,认识自然、发现真理也是对认识God的重要补充。当时的氛围和环境是比较自由的,只要不是公开提出与信理相悖的学说和观点,都是被默默允许存在的。“日心说”还是“地心说”,在神职人员当中都各有拥趸。的确,伽利略受到了的审查,然而整个事件的缘由却并不是他所提出的日心说。要知道当时的教宗十分欣赏他的观点,并与之通信鼓励他继续研究。无疑,伽利略事件之复杂囿于参杂了政治,后世的启蒙思想作家显然没有把历史真相告知与众,采取了掩盖的态度。
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科学家群体的出现与欧洲知识分子自治联合体有关。众多修道院、大学机构形成一张紧密联系的网络。如果说罗马教廷曾经在历史上是独断专行的,阻碍了思想自由、科学探索,那么一批又一批的科学者是如何在时代中接力、传承知识的?一个被绝对专断的社会还是否有可能出现自治的知识分子团体?其实我们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很多反例,知识分子不是沦为权力的附庸就是作为多余的人被铲除。关于科学精神的培育,教育该如何做,也许中世纪的氛围告诉了我们一切。在信仰与异端、信仰与理性的争辩中,现代科学作为一个意外的产物诞生了。它起初并不是普遍的东西,在人类历史上的发生如此独特。唯有回溯中世纪,在信仰的视野下才能理解这个意外不过是必然。
https://wap.sciencenet.cn/blog-279293-1491788.html
上一篇:《科学的起源》简介
下一篇:[转载]基于患者队列的随机对照试验设计:队列内试验(TwiCs)的方法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