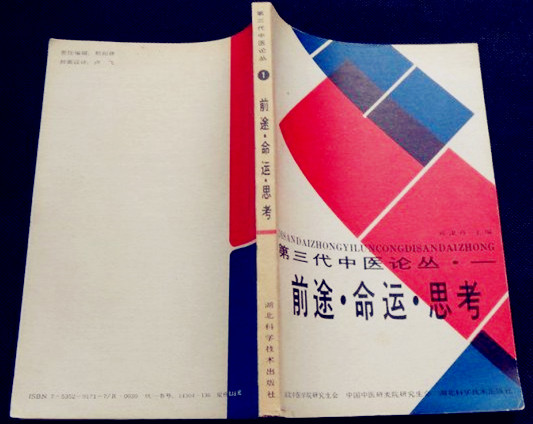博文
昙华林往事:“第三代中医”和《第三代中医论丛》
|||
2010年10月3日,我在“科学网博客”发过一篇《“第三代中医”和《第三代中医论丛》的往事》,这里根据日记补充部分细节,参加到师妹的这个系列中来。
1987年9月,我们与湖北科技出版社合作,出版了这本《前途命运思考——第三代中医论丛(一)》,主编是出版社社长郑津舟先生,编委是卜平、王华、王进、陈新、闻集普、施吉、聂广、谭德纯、熊波、鄢良。
记得2006年底,我到北京开会碰到鄢良(当时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的研究生会主席,国内培养的第一位医学史博士),谈到《前途命运思考——第三代中医论丛》出版即将20年,他提议搞个学术纪念会,大家再聚一聚弄个20年后的“再思考”。我也联络了赵洪钧、何裕民等,后来因为大家忙,兴趣不大就拖延过去了。
那是34年前,我这个自命不凡的冒失鬼恃着在本科期间发了几篇文章(共6篇,后来研究生期间每年发表20篇以上,赚了不少稿费),还没有入学就经常跑到湖北中医学院研究生宿舍,和那些师兄、师姐们攀谈。那时候,一代天骄的大学生豪情万丈,乘改革开放的东风而来,备受社会各阶层恩宠。自然而然地,怀揣“时间开始了”的壮志,做“天将降大任于己身”的梦想。
进校不久,我就率先提出“第三代中医”的概念,加入到“振兴中医”的呼号中。1986年春,各地中医院校相继成立了研究生会,我和闻集普在湖北科技出版社(他的同学那拓祺本科毕业分配在此)的支持下,打着湖北中医学院研究生会的招牌,联系中国中医研究院、上海中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等多家兄弟院校的研究生会,开始征集稿件。
什么是“第三代中医”?当时是这样划分的:中医高等教育诞生以前者为第一代中医,诞生以后者为第二代中医,而恢复高考以后者为第三代中医。我们坚信,第三代中医肩负着继往开来的重大使命,中医振兴必将在这一代完成。刚才,我从1985年11月1日凌晨的日记里找出当年的“征稿启事”:
本书取名为《第三代中医:前途与命运思考》。因为第三代中医最关切中医的前途和命运。
对于第一代中医,尽管他们也考虑(甚至当今把握着)中医的前途和命运,尽管他们也忧心忡忡,疾“乏人乏术”之苦。但他们毕竟可以坦然地说:我们这一代已经走过来了,这接力棒应该而且必须交下去!
对于第二代中医,尽管他们也渴望中兴、渴望开拓,但他们毕竟也可以说,我们最宝贵的年华却处在最艰难的时期,现实中承上启下的担子已经够重了。
那么第三代中医呢?我们意味着来日方长,意味着未来中医。中医的前途是我们的命运,我们不想,谁想?!我们不干,谁干?!什么是“历史责任感”?只有充分认识这几个字的份量,才能肩负我们的使命。
悠久的传统科学正向我们手中移交。然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第三代中医面临着巨大的信念危机!
信念的建立和巩固,不在于空洞的说教,不在于一时的热情和冲动,不在于美好善良的愿望和遐想,而基于可供信服的事实,在于实事求是的理性分析。坚定的信念得助于基本事实客观分析的升华——清晰的方向和目标。坚定的信念是所有科学巨匠成功的前提,如果我们蹉跎岁月,如果我们碌碌无为,中医的未来就会黯淡无光。
《第三代中医:前途与命运思考》是我们自己的思考,旨在聚全国青年中医精英的智慧和理性,思考我们的学科结构、发展潜力、理论惯性、突破方向......。相信,观念的进步能够改变学科的格局,我们的思考将集聚巨大的能量,产生深远的影响。中老年专家已经有了《中医学2000年展望》,他们正看着我们,新一代与老一代中医的见解有什么不同?但无论如何,我们的思考将直接影响我们的行为,并且决定未来的中医。
《第三代中医:前途与命运思考》要求来稿密切联系实际,以现实为参照,以历史为借鉴,以理性为原则,进行客观、冷静地思考。观点不拘,形式不限,更希望将多学科知识、方法和精髓与中医学的具体问题融为一炉,切忌“贴标签”式生搬硬套。来稿限8000字以内,请寄“湖北中医学院研究生会”,截止时间1986年6月30日。根据来稿情况,考虑是否分册发行。
之后,湖北科技出版社将其作为丛书立项,很快得到全国各中医院校研究生的大力支持,一份份散发着青年中医人热情的稿件纷沓而至。于是,编辑出版了第一辑《第三代中医论丛:前途与命运思考》(1987年9月)。当然,年轻人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进入专业实习和论文准备阶段的伙伴们各忙各的,再也没有一年前的激情。因为“历史责任感”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它最终一点点消逝在岁月的冲刷下。
本书的“编后记”有这样几段话:
……1985年,我们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部分青年编辑同志(责任编辑那拓祺校友早已是湖北出版集团副总裁——今注)在社领导的热情支持下决定在全国组织一批以研究生毕业论文为主体的当代青年优秀科技论文,并分学科汇编成册,暂时定名为“未来学者丛书”。但由于当时各方面的条件尚不成熟,故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湖北中医学院发现该院有些研究生正就有关“第三代中医”涵义的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于是我们便产生了以湖北中医学院研究生会为基地,面向全国征稿,首先在中医这一当前面临许多问题有待探索和发展的领域内出一套观点新、思想深、质量好、水平高的当代青年中医论丛的想法(那拓祺1984年毕业后分配在湖北科技出版社,而他的几个同学又是我的研究生同学,当我有了一个初步想法后就和闻集普一起主动找到那拓祺,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计划,但最终也只出版了一本。今天拿起手中的这本小册子,我发现主要作者基本上是我们85级的,说明第一年课程学习期间才让大家有机会在一起思考和讨论一些前途命运的公共话题——今注)。于是我们热情鼓励、支持了“第三代中医”问题的讨论,决定与湖北中医学院研究生会和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会(那时候,鄢良是该院研究生会主席,也是那拓祺的同学——今注)一起联合编辑出版这套论丛,并将其定名为《第三代中医论丛》。
鉴于目前中医面临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西医的强烈冲击而处于将被淘汰的危机,我们首先列选了十二个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征稿,决定论丛第一辑一专门讨论有关中医发展战略问题为主,取名为《前途·命运·思考》。自1986年元月征稿以来,我们陆续收到300多篇来稿,这些来稿从分析现状,剖析问题,客观评价中医现有学术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发展战略等方面入手,涉猎哲学、史学、文化学、社会学、比较医学、分子生物学、中医未来学等多个领域,透过各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一颗颗热爱中医事业、愿为振兴中医事业而奋斗终身的赤子之心,体察到了一代中医新人勇于探索、刻意创新的激奋之情。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中医未来的希望。
……今天,科学事业的发展正处在一个大协作、大联合的时代,像中医过去那样独承师技,各自为事的活动方式恐怕永远成为历史的遗迹了。《第三代中医论丛》的出版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的潮流……
20世纪80年代,是自五四以来思想解放的一个高峰(那时候的国家百废待兴,犹如建国初期的生产力解放),那些恢复高考后入学的大学生、研究生颇有“以天下为己任”豪情,很多人的血液里沸腾着“历史使命感”,正如我们在本书“前言”所描述的:
古老的中医在渡过了20世纪初的世界性传统医学大倒退后,又出现了一次空前的危机。现代科学正呈加速度迅猛向前发展,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冲击着人们的意识结构,传统的中医学向何处去?!——历史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面对这一严峻现实,牢骚满腹、悲观丧气者有之,麻木不仁坐视观望者有之,热血沸腾锐意进取者有之,正视现实左右求索者有之,封闭僵化抱残守缺者有之,……这一历史的图景,展现了一场新与旧、扬与弃的搏斗。
在这当中,我们是第三代人(我当时的想法是未经历过解放后中医大学教育的人是第一代中医,从开办中医大学教育到恢复高考前的业医者为第二代中医,恢复高考后入学的为第三代中医,这个划分突出了我们自己的历史地位,但难以概括没有经历过大学教育的“自学成才者”)。第三代中医最关切中医的前途和命运。对于老一代中医,尽管他们疾“乏人”、“乏术”之难,但他们毕竟可以坦然地说: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这接力棒必须交下去;对于第二代中医,尽管他们渴望振兴,渴望开拓,但他们毕竟也可以说:中医事业青黄不接,当务之急是承上启下!那么第三代中医呢?悠久的传统医学正向我们手中移交。我们意味着来日方长,意味着未来中医。中医的前途是我们的命运。如果我们不努力为古老的中医探索一条迅速发展的道路,中医将面临自然淘汰的危机;如果我们客观地分析局势,尽快找到切实可行的方向、途径和措施,中医药有可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列于未来医学之林。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历史的重任落在我们肩上。我们深深理解“历史责任感”这个词的深刻含义。
……
我们正沿着前人走过的路向前走着,同时我们正走着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第三代中医论丛》凝结着我们的探索和追求,带着我们的热情和期望,散发着第三代中医的体温,桴应着第三代中医的脉搏与大家见面了。在这里,我们为当代青年中医开辟了一个学术争鸣的园地。虽然它还显得有些稚嫩和不乏偏激之情,但我们相信青绿的嫩芽最终是会长成参天大树的。重要的是,通过它的出版,我们希望在当代青年中医中造成一个敞开胸怀、畅所欲言的环境和气氛,更加激励起他们为振兴中医事业而勇于献身、开拓进取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造就出新时代的张仲景、李时珍,创造出新的学科奇迹,中医这门古老的传统医学就一定能以崭新的面貌争艳于世。
今天,当我重新录入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激情再一次被自己过去的豪言壮语所煽动,也许我生来就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幻想的人。如果我的情绪能够影响更多的人,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正能量”,或者说是理想主义,尽管它常常显得不切实际。
顺便说一下,当年的编委会曾经打算出版社社长做主编,卜平、鄢良两位研究生会主席做副主编的,因为我和闻集普是发起人、组织者和实施者,一时难以接受,于是就形成了前面提到的编委会成员名单。
2010年,在写出《“第三代中医”和《第三代中医论丛》的往事》博文的时候,我在网上搜索,发现有人将《第三代中医论丛》扫描上传于网上,我代表作者之一进行了特别致谢!但是,那时候还可以查到全文,现在再也找不到了。当时转发的“目录”为:
序/陈可冀
前 言/第三代中医论丛》编委会
现代中医学研究状况的宏观思考/关 前(1)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医学――中医发展方向的文化学思考/陈 新(15)
中医学,神奇的工具——对中医理论的实质前途与当代中医学历史使命的思考/鄢 良(27)
论我国中医发展中的定向错误/王律修(47)
从脏腑学说的缺陷看中医发展方向/周 捷 张 秋(63)
中医学,哲学与经验的融合与分离/聂 广(72)
中西医结合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许树强(92)
新技术革命与中医发展战略/何裕民 章 芝(100)
现代西医对中医的挑战及中医发展对策/王 敬 陈能进(116)
从国外医学之沉浮看我国中医的发展方向/卜 平(124)
近代中日废止中医泛论/赵洪钧(137)
论中医理论的现代研究方式/王 键(148)
论中医科研的社会劳动结构/闻集谱(157)
怀疑方法在中医发展中的作用/王旭东(169)
中医学的技艺及其前景/许懋容(177)
中医临床医学的危机与出路/陈齐鸣(157)
从分于生物学的进步看中医的发展/汪 建(193)
中医学发展缓慢原因之专题笔谈/卓同年、陈放中等(200)
一、学术范式的弊端(200)
二、研究对象的异化(203)
三、尊古崇古的民族心理(208)
四、儒家思想的消极影响(209)
五、理学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阻碍(212)
六、整体科学水平的落后(219)
七、形式逻辑研究的薄弱(220)
八、政策失误和极左思潮的历史性影响(222)
九、传统观念的束缚(223)
十、人际关系冷漠带来的学术传导阻滞(225)
十一、管理环节的薄弱(226)
十二、医药失序的危机(227)
十三、“醋劲”、“惰性”与“浮性”(230)
十四、未来20年的惯性预测(232)
编后记(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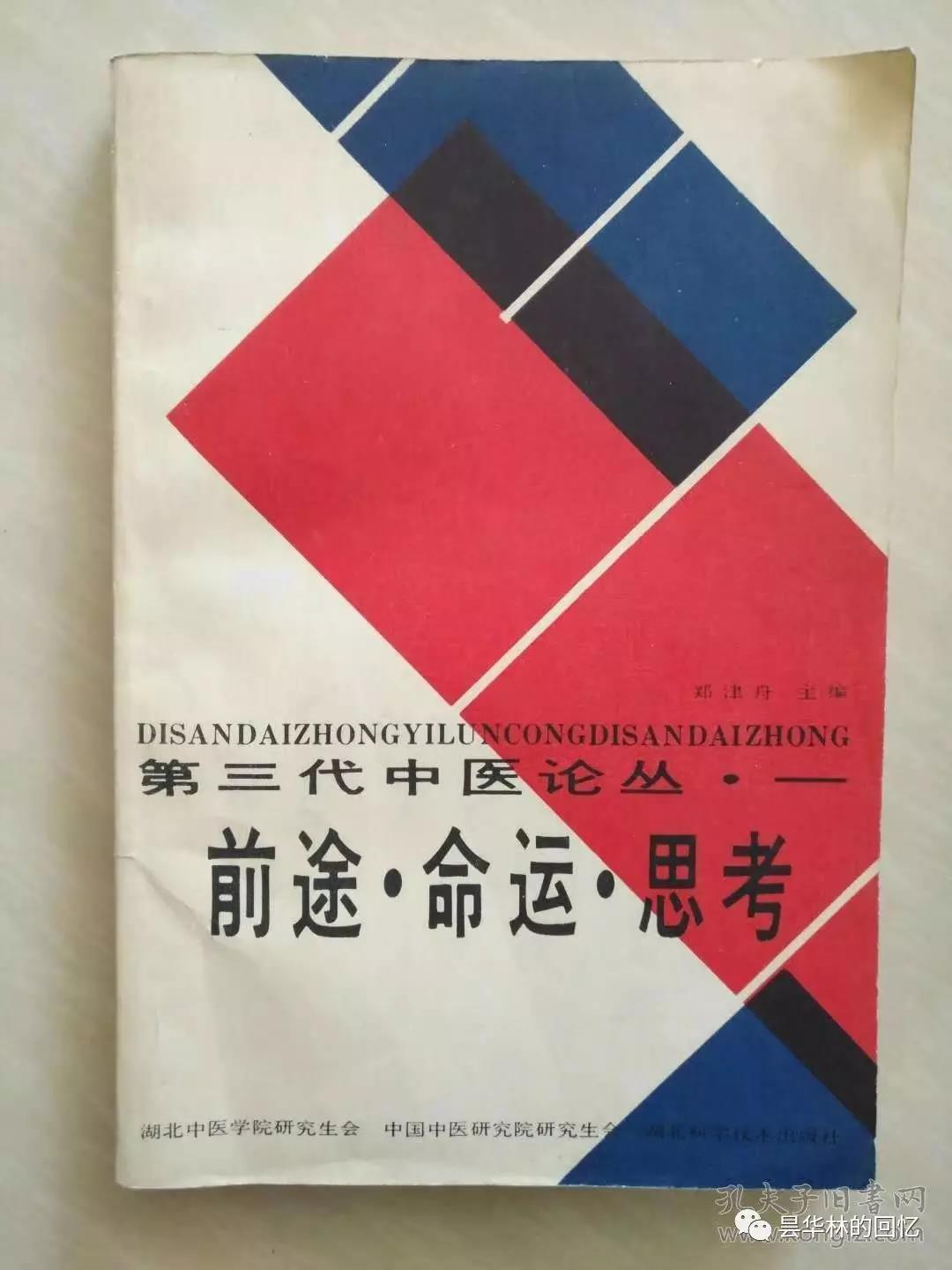
下面,是天津大学杨正瓴教授贴在我2010年博文上的李荫远院士(1919-06-23~2016-08-22)的“科学网博文”——《杂忆和杂写(一)从选上学部委员到耄耋之年 》 ,刚好是那个时期国家大环境的缩影之一,也附在这里(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08115-520141.html)。
附李荫远:从选上学部委员到耄耋之年
按:有好长一段时间不发博客了。我仍然头脑清晰,今天拉杂写下一些,让网友们知道我还健在。
“文革”后1979年,有不少人说中国科技工作者有断档的危机,必须尽快地采取措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于是决计先将学部委员的聘任制改为选举制,并扩大其名额。主持科学院的方毅同志,热心科学十分尽职,马上着手进行:由当时还在世的,原五、六十年代聘任的学部委员作选举人,各单位酝酿后提出候选人,对外并不公开,只通知拟定的候选人,自己提交一份学业资历、科研成果和论文目录,我所在的研究所有五位同事被要求提交材料,我们各自都还在纳闷,有点提心吊胆,不知是为了什么事情。后来得到院里通知才知道自己当选了新学部委员(我单位五位交过材料的有三位当选)。不久收到一个进出院部的证件,其实很少用到它。更不记得学部委员有什么特权。1981年召开了学部会议,开了几天会,是讨论学部的章程和其他议题,最后选举了主席团,再由主席团选举院长。当选人是卢嘉锡,卢先生是位知名人物。二战时在美工作,还得过奖章。1945年归国,1954年入党,并创办福州物质结构所担任所长,他祖籍台湾,1915年生于厦门。从专业水平和政治条件来说,他的当选没问题,一时让我感到新鲜的气氛。方毅卸去原院长兼党委书记,调国务院任副总理。卢院长和新来的院党委书记就任后不久,最高当局却又颁发了一个将中国科学院划归国务院领导,任命卢某为院长的红头文件。
我当选学部委员的事完全出乎意外,我想原因是那一次新增的名额颇多,其次是“文革”前十七年在政治运动不断的情况下还能坚持工作,有一点儿成就,就殊可嘉许罢,可以说当选的门槛不高。这也不怪,那十七年有一部分同事在缺乏设备和避免被批为工作脱离实际,就干脆在上班时以读毛选四卷、看专业书和参考消息度日。“文革”后还有少数与我差不多同时回国颇有能力的海归申请离境,上级明智地发给护照,还由院里设宴送行。我在学部第一次会上,除听报告外,在分组座谈会上按照20多年来吸取的教训“言多必失”;听得不少,说得不多,也没有被推选入数理学部的常务组。记得开完会后也没有大任务。在80年代我担任过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两届审查非核物理项目申请书的工作。审查组由八人组成。我们是否滥用了权力呢?绝对没有。科学基金会事先有一位抽调来过滤申请书的副教授,也照顾我们开会。当时基金会很穷,我们差不多全部申请都批给了钱。款数少得可怜;还从原被过滤掉的申请中找出尚可考虑的也给一点钱。记得其中一届是在杭州的原杭州大学开的(时在暑假)。为了节省开支,住吃和开会的日数都事先规定,只留了一天作为市内游览后,如期返回。
1978年,全国首次招收授予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我被列入我们研究所中的导师之一。那一次的考生十分优秀,我收了四人,推荐了二人给其他导师。最多只收四人,不是上级的规定,而是我所的几位将当导师的人一起商定的,可谓极为谨慎和郑重。学生在研究生院念一年书后,到研究所作论文,要保证在两年之内完成任务,选题煞费苦心,可是一到毕业(甚至还未毕业)就被留美的奖学金吸引走了。后来有了授予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但考生与第一届比一年不如一年,原因之一是北大、清华……等名校自己将本科毕业生中优秀的免考,保送为研究生而且第一届考生不少是十年浩劫中暗中走白专道路的有识之士。1989年我年满70岁,送走了最后一位研究生去美之后,决定关门不再招生,而且逐渐退出一线的研究工作。我自知已过了科研出成果的大好年华不必强求。我一直没有个研究团队,收摊子不成问题。
此后,我继续担任物理学报执行副主编,这件事由来已久,物理学会主办的物理学报编辑部原归清华大学代管,解放后清华北大重组,物理学报编辑部由全国科协委托物理研究所代管。学报的主编是王竹溪老师,副主编是钱临照前辈。创办中国科技大学时,物理所领导以支援科大的名义,将钱先生的编制并未事先征求本人意见就转给科大。钱先生找到我说:他以后不到所里来了,请我代替他作副主编,我在昆明就认识他,未加思索就答应了,后来一想真是很孟浪。他大约先已把这一决定征得周培源先生和王老师的同意。周先生原是中国物理学会的会长。解放后各个学会都归全国科协领导。他从那时起就不要求学会搞什么活动,也不照章改选会长,一直在开了科学大会之后才恢复学会的活动,开会改选会长。他是一位政治上十分明白而学术上有大成就的长者。我在昆明时并没有听过他的课,不曾有往还。那次差不多休眠了三十年后才开会时,周先生一见到我,就连声说:他感谢我这几年为物理学报出了力,这许多年只有这份学报还是活着的。当时王老师的肝病已到晚期(在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染上血吸虫病的后果),周先生就和我商量学报主编由谁接任的事,我说,学报编辑部“挂靠“在物理所还是由所外的人任主编更好一些,周先生点头并亲自去病房请王老师推荐人选,王提名周光召,周先生说光召太忙,于是王另荐黄祖洽,就定下来了。一晃就过了许多年,物理学报早已扩大了篇幅,并出了与中文的物理学报内容迥异的英文期刊Chinese Physics B(刊载非核物理的论文)。又有了Chinese Physics C(刊载与核物理相关的论文),编辑部设在高能物理所。当初的计划还没完全实现,至今尚缺Chinese Physics A(计划刊载理论物理的论文),因为始终未能争取到有关方面的同意。
我曾连续担任过两届物理学会的常务理事,分管出版事务。并在1984年为物理学会创办了Chinese Physics Letters(中国物理快报),邀请北大甘子钊任主编,编辑部仍设在物理所。1995年左右,我辞去物理学报执行主编的职务,编辑部把我的名字作为顾问留在封面内页。到现在主编已经换了三届。
1995年我虽然已逐渐退出一线的研究工作,我的兴趣转移到碳60和相关的新生事物上。我为科技导报写过这方面的综述,并随时关注着这方面的新进展。然而就在这时由于十年浩劫的后遗症,我的三代六口之家散架了。“文革”前期,表面上对我夫妇的冲击不大;作为革命的对象,我有写不完的检讨,每天上班要先向毛主席请罪,接待外调时受尽斥责,都是形势所当然的。同时我的老伴胡镜容作为一个工科学院的教基础数学的讲师,因职位低人缘好仅只紧跟革命群众天天开会,可谓意外的轻松。不幸的是,她原有轻微的心脏病却得不到起码的医疗(那时是护士主管医院的期间,心电图仪器被打上了封条),她的病日渐严重。1980年我们的二女儿以上山下乡再回家的知青,因超龄得不到上高中的机会。她突然背叛了读书无用论,决心利用从来不肯让人知道的海外关系出国念书,我们只好听之任之。她很快地办好了出国签证,竟然在美从社区学院读了一年半转入州立大学,两年后本科毕业,再受雇于IBM。以计算机专业获得衣食无忧,成家育儿的日子。1990年她接她妈妈去美养病,在她家长住下来,拿了绿卡。从那年起,我每年有三个月或稍长去美国看望老妻,但每年一次的院士会我还都出席。1991年第二次增选学部委员(从来没人问过为什么1980年第一次选举后要等十年才举行第二次增选)。这一次才是先有章程,要求本人申请和两位选举人推荐……等规定,以后每单数年增选一次。1993年学部委员改称院士,直到我1999年“资深”之后才不再参加增选会。我从来没有申请过科学基金,也没有当过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有过一点小麻烦,即是那些年有两、三位友人找我推荐其作为候选人。此种事还好办,我先请对方写个草稿,我加以删削,在评语上我字斟句酌,然后密封寄出,选上与否与我关系很小。我只主动地推荐过一位改革开放后出国,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又在大公司工作一年,即便回国的某位海归。
我的大女儿1964年考入北大化学系,读完二年级,“文革”降临,上山下乡。回城后,考入一工科学院读完硕士,留校任教,她的美语十分流利(幼儿时期养成的)也就成为学院接待来访外宾的陪同者,因此,她后来得到作为交换学者或访问学者的好处。九十年代中期,她在罗马作访问学者,突然得知学院将让她接替将要退休的教授当教研室主任,并提升为副教授。这应该说是好事,她却张皇不安。她的推想是,如再遭逢政治运动教授们便是反动学术权威。她在罗马工作期满之后,以探望妹妹的名义取得访美的签证。在那里很快就有华裔学人主办的科技开发公司雇用她作助理,替主办人管理这个不过十多个雇员的知识产业。接着她的小家庭也移民纽约。2004年老妻心脏病已到晚期,我接她回京打算试以中医和针灸拖延残年,熟料不到半年,她竟以脑梗塞在海淀医院去世。
从1995年以来,我已不再专心探究科学。2006年起一直在京安度余年。行动不太方便,每天看科学时报和中国青年报网上消息,我明白世道已经大变,在功利主义的驱动下,谈不上公平和清正。当今出现的社会危机绝对绝对不是个人的问题。八十年代的新启蒙和理想早已随风而逝,但我国的科技水平确有极大的进步,特别在系统工程方面成绩更大。
我以青少年时代的根底,每天读读写写,以文史自娱。空巢老人并不一定就会十分寂寞,试看我们这一代的海归和高知,有多少人不是空巢?我是其中的幸运者,有了一位尽心照顾我的人,应该满足了。
写于北大物理学院即将召开的王竹溪先生百年冥寿纪念会之前。
https://wap.sciencenet.cn/blog-279293-1206580.html
上一篇:昙华林往事:“现代中医研究会”与《现代中医》
下一篇:星言星语与星月(114):小姐俩